今天是著名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诞辰150周年。1869年1月12日(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在1936年去世前,章太炎的最后一项事业是主持于此前一年9月16日成立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并亲自授课。在讲坛上,太炎先生结束了自己特立独行又寄托遥深的一生。而他的讲学生涯,也正是以其近三十年前在东京首度讲授《说文解字》开始的。

章太炎
太炎先生一生讲学,稍成规模者,计有十余次。而声名卓著者,则有1906至1911年间的东京讲学、1913至1914年间的北京讲学、1922年的上海讲学与1934至1936年间的苏州讲学四次。其中,若论影响之大,首推东京讲学。
1906年6月,身陷“苏报案”的章太炎刑满释放,当即前往东京,与革命同人会合。7月15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与“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所谓“宗教”,指的不是孔教或者基督教,而是佛教。在章太炎看来,“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至于“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即其“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与“人物事迹”。这篇演说可谓章太炎的“政治宣言”。其中关于“国粹”的部分,则是其历次讲学的“思想纲领”。
东京时期正值章太炎革命生涯的巅峰。通过主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他一方面与反对排满的各方展开激烈论战,笔锋及处,所向披靡;另一方面还积极从事理论建设,日后的国号“中华民国”便出自他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与此同时,他“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成为了弟子眼中与史家笔下一道永恒的风景。
有感于世人只知章太炎为“国学大师”,鲁迅曾抱病完成《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指出“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不过,与“革命元勋”相比,后人更为熟悉的,显然还是作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
1906年9月,章太炎在东京成立了国学讲习会,“科目分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地点设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内”。(宋教仁《我之历史》)不过,在1906与1907两年,章太炎只是就相关专题做过个别演讲,直到1908年4月,才正式系统开课。当时,“听讲的人以浙人、川人为多,浙人中有沈士远、兼士兄弟,马裕藻、马叔平、朱希祖、钱玄同、龚未生等;川人中有曾通一、童显汉、陈嗣煌、邓胥功、钟正楙、贺孝齐、李雨田”(任鸿隽《记章太炎先生》),此外还有任鸿隽、任鸿年兄弟等。
同年7月,应龚未生的邀请,章太炎在其《民报》社的寓所中另外开设了一小班,听讲者八人。除在大成中学转来的龚未生、钱玄同、朱希祖与朱宗莱外,还有新加入的鲁迅、周作人、许寿裳与钱家治。章太炎先后为他们开设过《说文解字》《尔雅》《庄子》《楚辞》与《广雅疏证》等课程。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日后,根据朱希祖、钱玄同与鲁迅的笔记,整理出版了《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一书。所谓“教学相长”,章太炎的若干重要著述——例如《新方言》《文始》《齐物论释》与《国故论衡》,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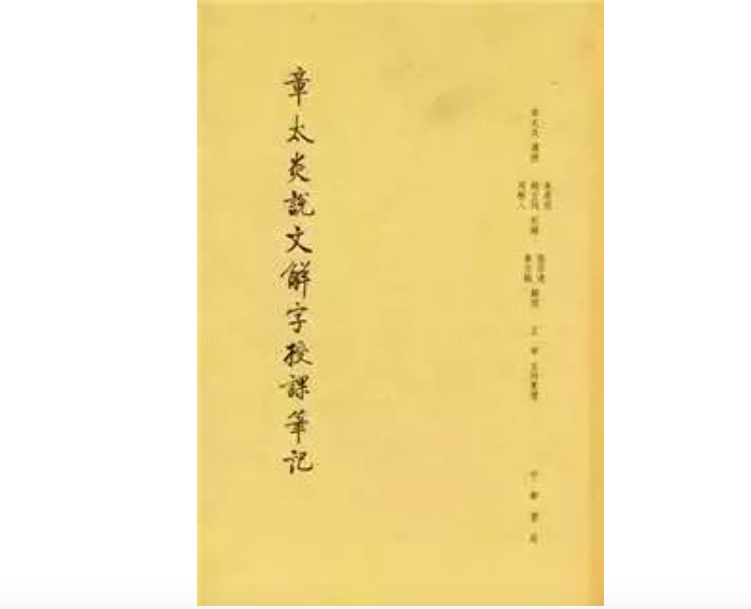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讲授:章太炎,记录: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主持整理:王宁,版本:中华书局,2010年
民国初年的章太炎,多为国是奔走。待到1913年12月,他才在北京重新开始讲学。顾颉刚与毛子水是当时班上的学生。根据顾颉刚的回忆,他的“讲学次序,星期一至三讲文科的小学,星期四讲文科的文学,星期五讲史科,星期六讲玄科”。(《〈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但未及一月,即遭袁世凯软禁,讲学被迫中止。
北京时期的章太炎曾经“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时任司法部佥事的吴承仕,对于此举十分敬佩,时常前往章太炎的软禁地探望,不畏险阻,事师如亲。此时的章太炎,“多言玄理”;而此时的吴承仕,也正“好说内典”。于是师徒二人一拍即合,相谈甚欢。章太炎以佛教唯识论为主线,旁及老庄与孔孟诸家,每发新意,吴承仕便秉笔录下。后来二人的谈话范围越来越广,囊括典籍、医学、历算、数学、音乐、文学、音韵与史事等诸多领域,异彩纷呈。1916年,笔录告一段落,共得一百六十七则,是为《菿汉微言》。全书最后一则为章太炎自述其“思想变迁之迹”,大有“托命”之意。章太炎自称此书“虽多言玄理,亦有讽时之言”,只是“身在幽囚,不可直遂,以为览者自能知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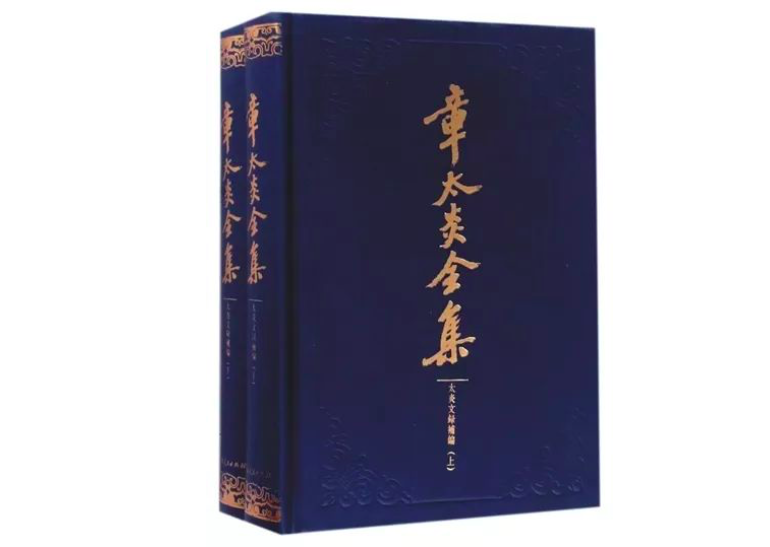
《章太炎全集》,整理:虞云国 / 马勇,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尽管不如东京讲学意义深远,章太炎的北京讲学同样在现代中国的学术史与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当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于1922年4至6月间在上海再度讲演“国学”时,却已时过境迁。这一系列讲演共计十场,分为“概论”、“国学之派别(一)——经学之派别”、“国学之派别(二)——哲学之派别”、“国学之派别(三)——文学之派别”与“结论——国学之进步”五章。曹聚仁全程听讲,并以白话文记录了讲演的全部内容,结集为《国学概论》一书。此书“上海泰东版、重庆文化服务版、香港创垦版,先后发行了三十二版,日本也有过两种译本”(曹聚仁《从一件小事谈起》),至今风行不衰。
在章太炎的全部著述中,《国学概论》可谓最为知名与普及的一种。时人与后世对于“国学”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书的论述框架。不过,上海讲学却成为了章太炎讲学生涯的转折点。讲学声势“始盛终衰”,开讲时盛况空前,人数最多的一回,足有千余;但随着演讲不断推进,听众逐渐减少,最后一讲,仅剩不及百人。不仅公众日趋冷漠,学界对于此次演讲,也多有批评。章太炎的昔日弟子周作人认为其“只适于专科的教授而不适于公众的讲演”,“否则容易变为复古运动的本营”,导致“国粹主义勃兴”。(《思想界的倾向》)而新一代的知识界领袖胡适不仅支持周作人的主张,更将章太炎的上海讲学视为其“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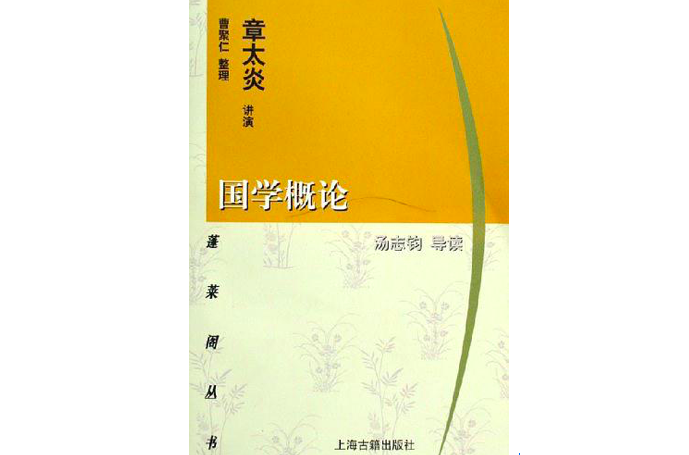
《国学概论》,作者:章太炎,版本:中华书局,2000年9月
上海讲学最终以争议与寂寥收场,说明章太炎的时代已经悄然远去。同样讲授“国学”,在清末民初乃是一种革命力量,孕育与促成了中国学术、思想、文化与教育的“古今之变”;待到“新文化运动”兴起并蔚为大观,一如既往的讲授则在时代潮流中黯然出局,“国学”站到了历史前行的对立面上。
章太炎讲学,在苏州“曲终奏雅”。其课堂记录,日后整理为《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一书。在其去世次日,《申报》率先在显著位置发布消息——“朴学大师章太炎氏在苏逝世”。1936年6月16日,又续载“治丧”报道,称其为“国学大师”。7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葬章太炎令》,表彰“硕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强调其一生“以讲学为事,岿然儒宗,士林推重”。
10月9日,有感于世人只知章太炎为“国学大师”,鲁迅抱病完成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指出“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称赞其为“有学问的革命家”。17日,意犹未尽的他又起笔写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再申此意。不想未及完稿而病情急转直下,于19日去世,此文遂成鲁迅“绝笔”。留学日本期间,鲁迅曾在东京向章太炎问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奋起而为先师“辩诬”,既属“私谊”,亦出“公心”。无独有偶,当年在东京与鲁迅同班的许寿裳,也认为“先师章太炎是革命大家,同时是国学大师”(《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将“革命者”的身份与贡献置于“学问家”之前。不过,与“革命元勋”相比,后人更为熟悉的,显然还是作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
从晚清末年到“抗战”前夕,章太炎的讲学生涯历经近三十年,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历史阶段。其四次讲学的内容与策略,虽有调整,但基本姿态与主要追求,却大致未变。而由此产生的不同反响与回应,尽管也指向章太炎的学术本身,但更为凸显与呈现的,还是各自历史情境中的时运更替,以及彼时知识界的内在焦虑与紧张。如何谈论章太炎,以及怎样理解“国学”的利弊得失,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不同观念与立场进行对话与互动的思想场域——从中激荡起与映照出的是章太炎的升降浮沉,也是现代中国在转折时代的步履与身影。
作者:李浴洋
编辑:徐悦东
原标题:只称他为“国学大师”,是低看了他 | 章太炎诞辰15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