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尔赫斯和玛丽亚·儿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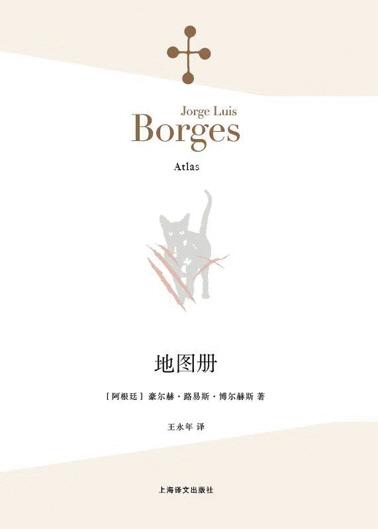
《地图册》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译者:王永年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博尔赫斯的作品最早译介到中国大陆是在1979年。当年《外国文艺》第1期刊登了王央乐翻译的四篇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南方》《马可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1980年代后期,博尔赫斯在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艺术观念以及叙事方式的实践,直接影响到当时一批先锋作家的创作。
2019年,是博尔赫斯诞辰120周年。近日,“博尔赫斯的地图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玛丽亚·儿玉旅行摄影巡回展”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开幕。作为本次展览主题的作品《地图册》,是博尔赫斯创作于1984年的诗集,作者将他与玛丽亚·儿玉共同游览各地的所见所感写成了诗,每个题目独立成章,趣味盎然。
这次展览将展出130多张首次在中国面世的精彩照片,参观者能以只有博尔赫斯才能看到的全新方式来环游世界和大大小小的城市。这些照片呈现出了这位杰出作家的丰富性:他活跃、放松、充满反思、令人尊重,同时也是一位怡人的伴侣。
在开幕仪式上,玛丽亚·儿玉谈到了丈夫和这本《地图册》对自己的意义:“博尔赫斯的《地图册》从他和我的记忆中生出,好似一张被反复使用的草稿纸,由讲稿、笔记、亲身经历和一种微妙的情感组成。它之所以具有原创性,不在于描绘了一对周游世界的伴侣,而在于这两人的年岁相差甚远,并且其中一个失去了视力,于是他们所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现实:在她的眼中,他是自少年时代起的探险伴侣,与她一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通过学习外语,打开了通往秘密世界的大门;而他,则透过她惊讶的双眼,重新发现了这个世界,重拾了青年时代的理想。与她在一起,文字——生命——化作了一面棱镜,折射出独特而非凡的生活体验。”
1
新京报:作为此次展览主题的《地图册》记录了你和博尔赫斯游历美洲、欧洲、埃及、土耳其、冰岛、日本等地的经历,能否谈谈这个展览的缘起?
儿玉:博尔赫斯的一位后辈作家是我们的朋友,当时他看到这些照片建议说,为何不将这些照片出版?可以给照片写一些文字。博尔赫斯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所以就有了《地图册》。《地图册》摘取了文字内容,于是我们就安排了照片展,在世界不同城市巡回展览。
新京报:《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入门》和《地图册》你也有参与创作,包括与博尔赫斯一同翻译18世纪冰岛诗人斯诺里·斯图鲁松的诗歌。可否分享一些合作过程中的故事?
儿玉:《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入门》的写作是他口述我记录,早先是他母亲记录,记录人员还包括许多其他人,陪在他身边的任何人都会被他叫来做记录。一旦他有什么想法了,他会说,“打扰一下,能帮我做个记录吗?”等坐到书桌边,一切准备就绪,他会说,“我是这么想的……”他还会经常做修改,一会儿改一下这里,一会儿改一下那里,有时候改到出版商说,来不及了,已经出版了。
我们会有所交集也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听了一场讲座,那场讲座很有趣,人很多,地上都坐满了人。我当时很害羞,讲话音量也很小,我的问题在于:如果我都没办法在几个人面前讲话,又如何能够给很多人讲课?当我看到博尔赫斯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比我还害羞,他讲话音量也很低。我对自己说,如果他能做到,我也可以。
后来再见到他是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差点把他撞倒。我连连道歉,对不起,我没有看见你,我小的时候听过你的讲座。他问我,你工作了吗?我说,没有,我在读中学。他说,你想学古英语吗?我问,莎士比亚?他说,不是,更古老一点,六七世纪,盎格鲁-撒克逊。我说,那太难了,我学不会。他说,不是,不是,我是想问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学,我也不会。我说,那好啊。之后我们会在咖啡馆见面,有一天他突然说,母亲说你还是个青少年,我不能一直这样带着你在外面,我应该带着你去我们家学习。就这样,我开始成为他家的常客。
2
新京报:博尔赫斯很喜爱口头文学,不少作品采用了口头讲述的方式,后来才结集成册,这类作品非常流畅,书面和口头的语言融合堪称完美,他平时讲话时是否就以这样的方式娓娓道来,还是说只有口述作品时才会采用?
儿玉:他平时讲话也是这样,娓娓道来,与他讲话就像是在阅读,是一种享受。和他待在一起,就是与他分享对文学的热爱,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兴趣所在。平时读书给他听一般会念英文,有时会给他读希腊文,一边读一边翻译。他特别羡慕我会希腊文,因为他自己学的是拉丁文。
新京报: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瑞士日内瓦因肺癌去世。为何没有选择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待在了日内瓦?在这个“特殊时期”,有什么小故事可以分享吗?
儿玉:日内瓦对他而言就是他的青年时光,是幸福的代名词。他年轻时在这里自学德语,翻着词典读诗歌,觉得很快乐。在最后的“特殊时期”,他是在学习阿拉伯语。
那时,博尔赫斯已经病重,他知道“那一天”很快会到来,决定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和医生商量,医生也是博尔赫斯的朋友,他让医生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已经病重且不久于人世。在出发前,我问医生,如果博尔赫斯的状况恶化了,想回来阿根廷还可能吗?医生说,当然,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安排救助直升机。我说,请将这个事情告知博尔赫斯。之后博尔赫斯问我,为什么要问医生这种问题,你知道我不打算回来的,我不想面对那些,不想将自己的情况暴露在聚光灯下。我说,我只是希望你有选择的余地,希望你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一起去了意大利,逛遍了整个意大利,之后去了日内瓦,他决定最后就留在这里。我们去了以前经常住的酒店,我们和酒店的工作人员也是朋友。日内瓦的老区特别漂亮,博尔赫斯说,我们为何不在老区找一处公寓住下?我说,这不太可能,老区那边都是本地人,他们不喜欢外国人来来往往。他说,你能做到的。最终我们在那附近找到了一处公寓,距离酒店也很近。等一切安顿妥当,博尔赫斯说,我们继续学日语吧。我们联系了日语老师,日语老师却说不能私下授课,所以日语学不成了。那我们能学什么语言?阿拉伯语,我们可以学阿拉伯语。
我于是开始找阿拉伯语老师,翻阅报纸时找到了一位阿拉伯语教师。我很急切,晚上九点就直接联系了那位老师,这个时间在日内瓦是非常晚了。我给他打电话,那位老师问,你为什么想学阿拉伯语?我说,我学习了好几门语言,阿拉伯语就是下一个,有什么问题呢?他又问了一遍,为什么,你到底为什么想学阿拉伯语?我说,我很急,你真的要帮我,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真的得教我。说完我就停下了,他听完也很久都没有说话,漫长的沉默之后,他说,好,我教你,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都可以,你是老师。我们定在了周末。
他说,好的,我去你家上课吗?我说,不是,不是,我住酒店,我们去酒店上课。说完我就觉得好笑,邀请一个陌生人去酒店,他会不会觉得我有所企图。更好笑的是,那天他过来了,问我,我们是在客厅上课吧?我说,不不,我们去卧室上课。可以想象他的表情吧。卧室里,博尔赫斯已经坐在书桌前,准备好开始上课了。当我打开卧室的门,那位老师看到博尔赫斯在里面,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眼疾手快地关上门,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你不知道,我读过博尔赫斯所有译成阿拉伯语的作品,如果你告诉我是给他上课,我一定不会犹豫。我说,不,这才是“命运”(destiny)的选择,由命运来决定他在离开前是否能够学得上阿拉伯语,所以不能告诉你。
新京报:自博尔赫斯离世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努力奔走,为保护和推广博尔赫斯作品努力着,你心中有关博尔赫斯最深刻的记忆或者想法是什么?
儿玉:我知道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对我来说,他一直都在。能让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完全奉献自己去努力、去争取,一定是因为爱,绝对的爱(absolute love)。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感觉他一直都陪在身边,他在和我一起看这个世界。
新京报:除了对书的热爱这一特点,博尔赫斯奉之为人生哲学的是什么?
儿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To be an ethical person)。
采写/新京报记者 余雅琴 实习生 陆茉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