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姚斌
无处不在的复杂性问题
世界的复杂性无处不在,比如,有的汽车在行驶过程中会因为故障突然“擅自”加速,这种意外很可能导致伤亡。如果分析这种事故,大体会归结为驾驶员操作失误、垫毡顶住了油门加速踏板、油门加速踏板黏滞未能及时复原,等等。但是,这些原因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意外加速事故。实际上,对意外加速事故的发生,发动机软件系统的庞杂和糟糕的设计,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系统的极度复杂性,让我们很难理解其中相互作用的部件的深层问题和缺陷。
类似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系统中,以空中交通预警系统为例,人们创建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飞机在空中相撞。这个系统会提醒飞机驾驶员注意潜在危险,并告知如何根据规则作出应对。每当有人提出一项新的系统规则时,有关方面就会通过模拟试验来测试其效果。在若干次测试中,如果表现均能达到预期,新规则就会被批准投入使用。但是,几十年来这个系统的规则已经变得极其复杂,甚至复杂到全世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不但一般人无法理解,即使是专家,有时也会对系统在某种情况下所作出的反应感到困惑。
最有意思的是,在一个家庭中,总会有一个人会因为计算机或某种机器无法正常运行而受到指责,在其他人看来,他/她只是用手碰了一下,就把事情搞砸了;有时甚至只要某人在场,人们就会认定他是导致某种技术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原因。例如,一个学生暑假回到家中,偏巧打印机坏了;一个亲戚来访,刚好电脑鼠标就失灵了。将这些故障的设备交给他人维修,一到他们手上,故障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当把设备带回家后,却发现它仍然无法使用。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即使是功能平庸的家用台式电脑也是非常复杂的,复杂到地球上任何人都不知道它在做什么、怎么做。
因此,有人声称,我们生活在一个“纠缠时代”。在这个纠缠时代里,人类的线性思维无法应对其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如果仅仅是日常生活那也还好,但如果高度的复杂性作用于金融市场,就会遭遇重大的损失。在当今的金融市场上,参与者并不仅仅是人,大量以各种信息为基础的计算机程序也参与交易,而且速度比人类手动执行要快无数倍。这些计算机程序以异常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并通过巨大的交易网络对决策进行级联式放大和传播。

系统的极度复杂性,让我们很难理解其中相互作用的部件的深层问题和缺陷。图/视觉中国。
2010年5月6日,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闪电崩盘,证券市场出现了大规模的、非常迅速的巨幅震荡。许多上市公司的市值都因此遭受重创,不过不久之后又都基本重回原位。这次闪电崩盘涉及一系列交易算法和实施细则,而这些算法和法则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交互”,也就是复杂性科学经常提到的“涌现”,在短时间内便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金融系统异常复杂,它们是更高层级的技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个技术生态系统决定了每种证券或商品的交易时段。可以说,地球上没有人能完全理解金融世界中相互关联的所有系统,甚至没有人能完全理解其中任何一个系统。
造成复杂系统形成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只要举出其中的一个,就知道有多么复杂。“吸积”这个词来自天文学,是指行星系由一团旋转的尘埃和气体凝聚而成,这种星星点点的累积过程就是“吸积”。将这个词运用到复杂系统中,可以解释复杂形成的原因。比如,在法律体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条文总会被修订,由于法律体系不断地吸积,最终形成了一个拼凑起来的系统。
系统越来越复杂,有人就尝试解耦某些系统,将它们拆解为更小的单位,以保证其相对简单性和可管理性。这就好比,如果某家公司的规模已经变得过于庞大,且预期其失败会造成级联式冲击,那么就必须对它进行拆分或缩小规模。然而,这种做法往往事与愿违,在大多数其他类型的技术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互联通常只会继续猛增。无论多么努力,我们的大脑和社会在面对这些复杂系统时的表现,都可能力不从心。
在国际象棋比赛中,计算机比人类强大得多:计算机能够想到人类棋手不可能想到的走法,并取得最终的胜利。那些极具计算机特色的走法被称为“计算机走法”,人类棋手几乎从来不会用,那种走法看上去似乎是错的,但其实很有效。在最高级别的对弈中,对人类来说,国际象棋显然太复杂了,因为交互的部分太多,即使是像卡斯帕罗夫这样的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也无法完全理解。许多时候,我们甚至无从分辨哪个决定是错的,哪个决定是对的。

纪录片《阿尔法狗 AlphaGo》海报。这部电影全方位展示了人机大战的过程,更尽可能多地揭示了人类思维的工作方式和人工智能未来的工作方式。
以生物学思维应对复杂世界
那么,如何解决复杂的技术系统问题?在《为什么需要生物学思维》这本书中,复杂性科学家塞缪尔·阿贝斯曼提出,应该以生物学思维来解决问题。
原因有三:一是生物系统通常比物理系统更复杂,而我们的技术系统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像生物系统;二是生物系统是有历史的,生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容易受到进化的影响,之所以会呈现复杂的结构,是因为系统中存在极为复杂的历史路径;三是生物系统可以通过高度最优化容限模型来进行分析。与生物系统相似,技术系统可能会因为一些很小的干扰就出现灾难性的故障。因为生物系统与技术系统存在着深远的“亲缘”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生物学思维中学到很多东西。注重细节、强调多样性的生物学思维,将会为理解杂乱的进化系统提供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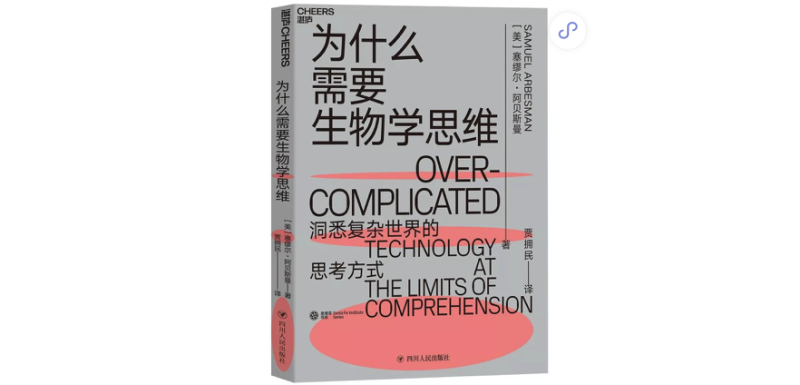
《为什么需要生物学思维》,塞缪尔·阿贝斯曼著,贾拥民译,湛庐文化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
生物学家,特别是野生生物学家,在研究生命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时,都会考虑它们的进化轨迹。这种方法特别适合用来理解复杂的技术系统。他们很清楚,一次只能研究生态系统的一小部分,而且即使是针对某一部分的研究,也未必会完美无缺。他们只研究少数物种之间的作用,很少考察某个地区完整的物种网络。野生生物学家对自己的判断非常坚定,而且明白,在任何时刻,都只能观察周遭复杂情况的一个片段。
生物学思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我们如果借鉴生物学家对癌症的观点,那么就是,在某些细胞长成肿瘤后,不能简单地说这是某件事情出了问题。癌症其实是诸多因素和多种生活反应累积所致,而且在这些因素和环境之间还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癌症是身体出现了大规模故障,而这种故障足以致命。
如果说,生物学思维是理解复杂世界的一把金钥匙,那么,这些生物学思维可以被表述为:不要被表象所迷惑;以欣慰感看待不理解的事物;谦卑之心加上迭代的生物学思维。我们必须努力维持两种相互对立的状态:第一种状态要求我们努力克服自己的无知,绝不能沉迷其中;第二种状态意味着一旦理解了某个事物,就不要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科学的思维,也是生物学思维,是我们学习新事物和解决难题的必备能力和先决条件。
虽然,阿贝斯曼认为,这本书未能呈现出他本人的全部思考,但是他所阐述的思想已经非常广泛。在巨大的技术复杂性面前,普通人作出剧烈的反应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对技术所导致的复杂世界要么深怀恐惧,要么过度崇敬。这两个都属于极端反应。那么,阿贝斯曼在破解极端反应的道路上,显然为我们提出一个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撰文 | 姚斌
编辑 | 徐学勤 榕小崧 喻子豪 李永博
校对 |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