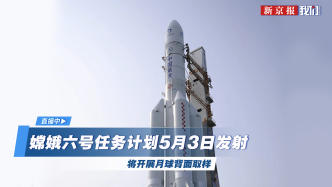长久以来,“安史之乱”是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而被国人广泛接受的。但是,研究中央欧亚大陆史的森安孝夫教授却不那么看,他认为“安史之乱”可以被视为征服王朝的先驱,是中央欧亚大陆骑马民族试图将中原纳入势力范围的一种历史趋势。森安孝夫之所以那么看,是因为他的视角与传统研究中国史的视角不一样,他拒绝西方中心史观和华夏中心史观,采取了一种开放的全球史视野。由此,他“发现”了粟特人,并在历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粟特文化的热潮。
这种全球史的视野对我们看待中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贸易线路吗?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对中国的影响又有多大?在《丝绸之路与唐帝国》里,通晓多门古语的森安孝夫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蒙古高原的古代突厥语碑文以及相关汉籍的史料,从另一个视角给读者讲述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在《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的新书发布之际,我们采访了此书的译者、日本姬路独协大学人间社会学群教授石晓军,与他谈了谈森安孝夫的这本书里的观点。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日]森安孝夫著,石晓军译,理想国丨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1月版
“安史之乱”不是“乱”,是一个过早的征服王朝
新京报:在《丝绸之路与唐帝国》里,森安孝夫提出一个比较惊人的观点,他认为“安史之乱”不是“乱”,是可以被视为征服王朝的先驱,是中央欧亚大陆骑马民族通过结合游牧社会军事力量与丝路贸易经济力量,试图将中原纳入势力范围的一种历史趋势,所以“安史之乱”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安史之乱”是欧亚大陆变动的先兆,是一个过早的征服王朝。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石晓军:这是一个很新鲜的观点。从中国内部往外看,我们可以把“安史之乱”视为“乱”。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更大的视野中来看,就可能会得出像森安孝夫的结论。
“征服王朝说”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这个学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人提出来了。欧亚大陆上有很多征服王朝。在欧亚大陆东部,就有辽、金以及后来的元和清。但是,人们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安史之乱”。大部分人都把“安史之乱”视作唐史的一部分。
森安孝夫不是研究唐史的。用森安孝夫的表述,他是研究“中央欧亚史”的学者。他把欧亚大陆分成西部、中央和东部。因此,森安孝夫的视点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的视点是很不一样的,也跟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的视点有所不同。当然,他们得出的结论就很不一样。把“安史之乱”看作一个比较早的征服王朝,也是一种思考“安史之乱”的新思路。
基于多元性的唐文化而形成的“汉民族”,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称为“唐民族”
新京报:森安孝夫特别强调,唐帝国不是狭义的汉族国家,而是“拓跋国家”,是五胡和汉人合二为一的结果,这是前期唐帝国具有世界主义、开放性、国际性、尚武等特征的原因。森安孝夫还认为,这种汉民族和异民族混血、文化融合所产生的能量创建的国家,和现代的美国也是相通的。这样的看法,对我们看待历史和世界有什么样的意义?
石晓军:我们现在讲汉族,往往会在无意识中陷入“汉族是不变的”的看法里。实际上,汉族本身就像滚雪球一样,是不断动态发展的集体。汉代的汉族、唐代的汉族和现在的汉族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族群。
在唐代,唐政权的中枢核心是由“北族”——拓跋和鲜卑与南边的农耕的汉族的混合——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唐帝国是中国史上首次出现的具有开放性的、国际性的大帝国。不是所有的王朝都能称为“帝国”,宋朝就不是一个帝国。因为帝国本身是多元的、世界性的。基于多元性的唐文化而形成的“汉民族”,其实早已不是汉代的那个“汉民族”,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称为“唐民族”。森安孝夫在书里也讲到了这一点。这样的视角对我们看待一些习以为常的问题会产生很好的启示,我们要历史性地看待历史问题。

石晓军
重新审视粟特文化,对我们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有积极作用
新京报:在推荐序中,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孔令伟认为,本书似乎有意无意地陷入了“粟特中心史观”。当然这也是因为在森安孝夫之前,日本人对粟特文明在中央欧亚大陆扮演的角色认知有限导致的。所以,孔令伟认为,这本书似乎其名为“粟特人与唐帝国”更好,因为作者在里面对吐蕃、于阗和龟兹少有提及。你怎么看待这个评论?对粟特人的强调,对我们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有什么新的意义?
石晓军:在森安孝夫的研究之前,很多人对粟特文明都是缺乏认知的。正因为大家的知识空白,森安孝夫在这本书里,重点地描述了粟特人在欧亚史中的地位,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在最近几年粟特人成为一个话题。因为近几年中国北方地区出土了很多粟特人的墓葬。这些墓葬颠覆了我们的很多看法,人们开始关注粟特人。森安孝夫研究中亚史,而中亚正是粟特人的故乡。欧亚的区域文化可以分为几大块:以游牧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以农耕民族为代表农业文化和大家比较忽视的介乎游牧和农耕之间的半农半牧地区文化。半农半牧区域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在10世纪之前,这个区域最活跃的族群就是粟特人。而森安孝夫通晓很多中亚地区的古语,他利用了古语言文字的资料去做研究。而中国的学者做这个地区的研究,用得比较多的是古汉语的资料。
森安孝夫对粟特人的确非常强调,但还不至于陷入“粟特中心史观”。这跟讲谈社这套书的性质也有关系——这套书不是要四平八稳地写教科书,而是要让各个领域的顶级日本学者,畅所欲言地写自己研究中最有心得的地方。强调粟特人也是由于长期以来陷入了以中国为中心、或以汉族为中心的史观。森安孝夫对汉族中心史观有一种反思。至于书里,对吐蕃、于阗跟龟兹提及较少,这是因为过去学者的注意比较多,资料发掘的也比较全,所以森安孝夫在这方面的笔墨就少一些。

唐代的粟特人武官像
在森安孝夫看来,粟特人是中世纪欧亚大陆最活跃的一股力量:粟特人不光经商,还参与政治和军事行动。唐帝国的武将里有很多粟特人,其中包括安禄山。粟特人不仅对唐帝国很重要,他们还是沟通欧亚大陆中部和东部的纽带。现在研究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个时期的史学界的中心话题之一,就是粟特文化。大家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历史学家们通过粟特文化,解释了很多过去不好解释的东西。从人种学上来讲,粟特人是白种人,它的文化渊源跟东亚各个民族都是不太一样的。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有着积极作用,也让我们跳出从内部看内部的视角。
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贸易路线,而是一个网络
新京报:森安孝夫似乎不只是视丝绸之路为贸易线,而是一个世界史的舞台。丝绸之路在从游牧骑马民族登场,到中央欧亚型国家优势时代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对我们现代重新看待和挖掘丝绸之路的遗产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石晓军:丝绸之路不是一根线,而是一个面。过去有人以为,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贸易路,像高速公路一样,从长安一直通往西方。但实际上,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网络。这个误解是受了近代以后德国地理学家的命名的影响。
在丝绸之路这个舞台上,活跃着游牧民族。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游牧民族仅仅活跃在这一舞台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国史上的“征服王朝说”,就和这个连锁反应有关。
在中央欧亚型国家的优势时代,丝绸之路平台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的网络节点都是城邦。然而,在十四五世纪以后,人们开始走海路运输,陆上丝绸之路就慢慢失去它的地位。因为无论用马车、驴还还是骆驼,跟船相比,运输的效率都是很低的,成本却是很高的。现在有些人认为,丝绸之路上大家都用骆驼运货,这是一种误解。因为骆驼很贵,大部分商人都用驴来运货。
陆上丝绸之路,从宋代后失去原有的地位。宋朝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造船技术。不久,欧洲的航海技术就有了飞跃的发展,后来就到了大航海时代。这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使命就已经终结了。在元明清,陆上丝绸之路就已经没什么动静了。清朝和俄罗斯之间有一些小规模的交流,但这交流的规模完全比不上海洋上的交流。

新京报:森安孝夫在重新构建世界史的时候提出了“中央欧亚视角”,这种以内亚视角来看待世界史似乎在学界已经很流行了,但是似乎在大众层面上,这个视角没有那么为人所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在学术界和大众之间历史视角上的分裂?这样的视角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内亚地区会有什么样的启示?
石晓军:这说明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专家没有做好普及工作。日本讲谈社这一套书就是写给大众的,但每一卷都是由各个领域的权威学者来写。中国缺少这样的书,很少有专家学者去写这方面的普及性著作。
今天我们急需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理解内亚地区。现在,全球史、区域史的视角在中国历史学界方兴未艾。但在近代、在全球一体化之前,我们需要从一个大区域的视角理解历史。我们看待欧亚中部、东部的问题,就应该以一种区域史的视角来考虑。
从全球史、区域史的视点看待历史,是国内学界相对比较缺乏的视点
新京报:本书一开篇森安孝夫就在序章就开宗明义地批判日本的“自虐史观”,他反对西欧中心史观,也反对中华中心主义,因为它们都是民族主义的。他用全球史视野,来考察活跃于中央欧亚大陆的突厥、回鹘与粟特人的历史。你觉得,森安孝夫为何会选择这样的视角来叙述唐朝的历史?
石晓军:森安的出发点不只是为了叙述唐史,唐史只是他叙述体系中一个部分,因为唐帝国在7-9世纪的欧亚大陆中扮演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森安孝夫反对西方中心论,也反对中华中心论。这两种思潮不光在中国存在,在日本也存在。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基本上都以西方为中心,“脱亚入欧”是日本的基本思潮之一。整个日本社会一直认为,西方的就是好的,这甚至包括了战后日本引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由于日本的思想界、学术界对二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这可能和国内对日本的认知有些距离——这种“西方的就是好的”思维更加加剧了。实际上,日本战后的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是进步史学流派。
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后,日本社会慢慢出现了一种反弹思潮,即认为过去的反省做得太过了,把日本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自虐”——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编写的研究著作和教科书等,几乎都是把日本说得一无是处。有些学者提出,日本人应该抛弃这种“自虐史观”,堂堂正正地恢复日本本来的历史。这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种思潮,他们还成立了研究会,要从日本的视角来研究、重写日本史。“自虐史观”就是这些学者提出来的。
森安孝夫实际上批判了这些学者。森安孝夫认为,他们批评的“自虐史观”不是真正的“自虐史观”。正视历史,把日本的阴暗面写出来并不是一种“自虐史观”。真正的自虐史观是不正视历史,什么都以西方为中心。他在书里举了很多反例,提到在很多地方东洋比西洋先进得多,如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达到的水平比欧洲领先了几百年。但同时,森安孝夫也提到,不能凡事都以中华为中心。因为日本过去一直处于中国文化圈里边,所以有着以中华为中心、日本为边缘的历史观的也大有人在。
新京报:你觉得这跟森安孝夫日本人的身份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在这本书的前面也提到,他所研究的时代,也是日本民族意识产生的时期。你觉得他这种历史叙述会跟他身处的战后日本的处境,想要重建某种日本的亚洲论述有关系吗?
石晓军:这恐怕没有什么关系。森安孝夫只是出于纯学术的角度,提出了他对世界史的一些看法,并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这和战后日本,以及日本在亚洲的位置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迄今为止,国内的中国史学者大多还在从内部看自己,因为搞中国史的学者和搞外国史的学者各自井水不犯河水,画地为牢。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我们的学术界缺乏森安孝夫这样的视角。
在中国,全球史这几年处于兴起的状态,其实日本很早就开始了对全球史的研究,比方说西嵨定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提出了东亚史观,这就是一种全球史、区域史的视点,因为它把日本放在东亚的区域内考虑问题。现在,近代之前的历史都放到了欧亚大陆里进行考虑。这样的视点是国内学界相对比较缺乏的。
作者丨徐悦东
编辑丨罗东
校对丨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