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郝春鹏(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读过《乌托邦》的朋友都知道,托马斯·莫尔借笔下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介绍了一个闻所未闻的乌托邦新岛。在这个国度里,人们轻现实重理想,轻物质重精神。他们衣着简朴实用,一年到头也只有两件:一件干活穿的粗皮衣,一件平日的毛外套;既无缤纷的色彩,也没有奢华的装饰;他们的生活节制有序,从不铺张浪费,避免一切奢华无用的器物。令人惊奇的是,鲜花这种既有颜色又不实用的东西却被乌托邦人所推崇,花园位于城市的中心,是他们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连“乌托邦”的故事也是希斯拉德在莫尔家中的花园里讲述的。
这些描述其实不只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花园的偏爱,在更广的历史时段上,它还体现了人类对花园这个非自然之自然的需要和期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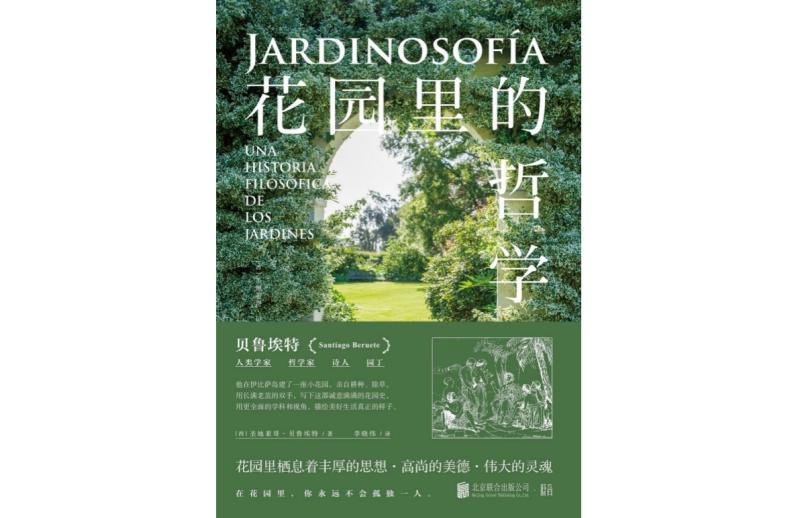
《花园里的哲学》,(西班牙)圣地亚哥·贝鲁埃特 著,李晓伟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10月
“花园”这个词译自西语,英文的garden、西班牙语的jardín、意大利语的giardino皆来自法语jardin,都本自jart这个古老的单词,意思是“菜园”“果园”。而这个词又来源于法兰克语的gard,意指“树篱”“围栏”。如果追溯其更早的来源,或许出自于原始印欧语系的“gher-”词根,指“掌握,包围”。
无论怎样,以上各种“花园”都离不了一个中心,即“封闭”“围墙”,其基本的含义就是:“一个被围起来的园子”,指的是一块人为的、同野生环境分开,由土坯、石头或者篱笆围筑起来的空间。
如果对花园的历史还有兴趣,读者朋友可以翻开圣地亚哥·贝鲁埃特的这本《花园里的哲学》,书里还有很多关于花园的奇闻异事。《花园里的哲学》不单介绍了古往今来花园在哲学生活中的地位,文末的附录也颇值得一读。
据说贝鲁埃特自己就建了一座小花园,亲自除草、铲土、修枝、耕耙,之后用这粗造变硬的双手写下了此书。“掌握园丁这个职业的工具的使用方法”帮他温习了作家这个职业的写作方法,他说:“如果我没有亲手建造一座花园,这本书会与现在大不相同”,故而本书就是贝鲁埃特自己的“精神花园”。
诚然,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学术作品,而更像是带着你漫步他花园的向导,随手指点园中的花儿和果实给你看。这里面没有艰涩的理论与厚重的概念,因为揭示花园的秘密并不是向导的使命,所有的秘密都要读者们自己去发现。而在这座花园中,那些注释就是花园里的各色花朵果实的详意,细心的读者必能在其中发现更多的惊喜。
希腊罗马人的花园:那些“花园派”哲学家
希腊人用“paradeisos”称呼花园,其实这个词来自波斯,最早由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学生色诺芬引入雅典,用来指称“充满土地所能提供的所有美好东西的地方”。古希腊人非常推崇波斯国王和贵族那天堂般的花园,就连埃及与巴比伦也是他们向往的对象。所以在希腊的故事中也布满了各色代表异域福地的花园,例如为赫拉克勒斯取得的金苹果就在赫斯佩里德斯(Hesperides)的花园中;荷马的作品《奥德赛》里出现了多个花园:神女卡吕普索的花园、国王阿尔克诺俄斯的花园,还有奥德修斯的父亲在伊萨卡的花园等。
希腊人对花园的静谧情有独钟,其中哲学家尤甚。最初的哲学流派几乎都发生在花园一类的场所,因为它是进行哲学实践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思想与知识传播的载体。
柏拉图的教学始于阿卡德米(Academy)学园,其影响深远,以致这个词至今仍是“学术”的代名词。学园中有绿树成阴的小路,花草也自不能少,门廊上还写有“不懂几何学者禁止入内”的标语。柏拉图去世后,其高徒亚里士多德虽未继承柏拉图的学园,但他自己在雅典卫城东北部开辟了一块新的教学场地,名为吕克昂(Luceion),今天法语的“lycée”(中学)就来源于此。据说,由于他和学生们习惯在学园的回廊里边走路边讨论哲学问题,因而又被人称为“漫步学派”。

伊壁鸠鲁和他的“菜园”。
更有名的“花园派”哲学家则是伊壁鸠鲁,他又被称为“菜园哲人”。其实花园的起源与农业本是合在一起的,目前已知的第一座花园可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在其后的几百年,花园与菜园并无明显区别。约公元前306年,伊壁鸠鲁从萨摩斯岛搬到雅典,在一个叫“花园”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学园。据说之前那里本是一座私人花园,老普林尼曾写道:“伊壁鸠鲁是一位通晓休闲生活的大师,他是在雅典发现休闲这种用途的第一人;在他之前,人们还没有在城市中体验乡村生活的习惯”。我们常说,哲学研究源于“闲暇”,今天school这个词的本意就是“闲暇”。
相较于“花园”,罗马人似乎更偏爱“菜园”。维吉尔在《农事诗》中对花园避而不谈,却歌颂了田园的美好、简朴的农村生活以及农民的劳作。当然,罗马人的花园也绝非各种蔬菜的汇集。鲜花、灌木与雕塑是花园的基本元素,受东方文化的影响,罗马的花园也充满了几何建筑的特点及修剪整齐的树林与灌木。希腊花园中的神像在罗马逐渐变为娱乐和装饰,同时也是权势与文化修养的表现。贵族们逃离城市的忙碌,在这里举行露天宴会,与朋友共同享乐,即便是一个人也可以享受阅读和写作的喜悦。
花园与皈依:基督教和文艺复兴时期
《圣经》创世记中也有关于花园的最早记载,上帝为亚当和夏娃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园中有两棵特别的树,由于人类的始祖偷吃了其中一棵智慧之树的果实,他们就被永远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人间再无这样永恒的乐园。带着这种原罪以及对尘世苦难的批评,加之中世纪基督教强烈的禁欲色彩,形成了地上的花园再美丽也不及天上乐园的看法。不仅如此,世俗的花园还常被视为欲望与诱惑的代名词,过多沉溺于此就会忘记自己的原罪和死后的救赎,因而不少修士为避免花朵的魅力、树叶的柔和及潺潺流水的“引诱”,特意远离了花园。但这一时期的花园也并非全无发展,植物迷宫的建造就是其中最有独特性的贡献,当然,它也是对古希腊克诺索斯迷宫的模仿。

亚当与夏娃
随着中世纪那种面无表情、干瘪枯燥的面相逐渐被文艺复兴时期的鲜活生动所代替,花园也再次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
除《乌托邦》外,在彼得拉克那里,花园也早被视为一种代表艺术与自然的和谐、丰饶与调和的场所。据说,在成为人文主义者之前,彼得拉克崇尚的是自然和乡村山林。在一次欣赏了山峰的景色,坐下休息时,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随手翻看了朋友送给他的礼物,那正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书上的一段话如醍醐灌顶一般忽然令他惊醒了:“人们赞美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汹涌,河流的浩荡,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己置于脑后。”
更值一提的是,奥古斯丁的皈依也和花园息息相关。这个故事同样记载在《忏悔录》中:那时奥古斯丁还是个纨绔子弟,一次同朋友待在加西齐亚根的花园时,他临时走开,一人躺在无花果树下思考过去的人生,忽然听见邻近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拿着,读吧!拿着,读吧”,于是他跌跌撞撞跑回朋友身边,那里放着他留下的《使徒书信》,翻开来,默默读着最先看到的一章:“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13:13-14)他顿觉一道光射入心田,溃散了过去所有的阴霾疑虑。
所以,如果说教堂是尘世连接天国的船舶,那么花园就是现实世界通达幸福理想的“乌托邦”。
第三自然:人为何建造花园?
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巴尔托洛梅奥·塔尔吉奥(Bartolomeo Taegio)根据花园的特质,将其称为“第三自然”。他在1541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自然与艺术融为一体时,就被提升到了一种创造性的级别,达到等同于艺术本身的高度,而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第三自然。”
与花园相对的所谓第一自然,是指人类未曾涉足的、纯净的、保持原有形态的地域,例如山川、海洋、沙漠等;第二自然则是指景观、田地、原野、耕地等,也就是被人类所干预改造的地方。
同第一自然的粗糙和为改造自然的单纯实用追求(第二自然)不同,花园反映的是一种对美与和谐的追求。它超脱出了前两者的单一,并提升为一种唯有人类才具有的审美特质。第一自然所具有的只有真,而不是美,唯通过艺术之加工才能使自然在人眼中变得美丽。花园的意义是要让期待更美好世界的理想保持生机,它既表现了人类对曾实现过的事物的怀念,也表达了人对尚未实现之物的渴望。虽然花园并不那么自然,到处充满了人为的痕迹,但它又无疑满足了植根于人性之中的最深需要,即传播、沟通以及为后代留下某些思想和感受的需要,花园的建造是进行文化表达的最精致手段之一(《花园里的哲学》,第11页),它是人们在视觉层面上对“幸福”的比喻,是更美好世界的预兆(同上书,第109页)。

哈德良别墅,古罗马的大型皇家花园。
另一方面,人在改造第一自然、建筑花园的同时,也被花园所“改造”和“建筑”。花园里有鲜花也有罂粟,有绿叶也有大麻。一方面花园是我们的理想和乌托邦,另一方面它也能把我们塑造成一个逃避现实的瘾君子。人在欣赏花园的同时也被花园诱惑着,迷醉于花园的人可能会因此逃避现实,这一点尤其需要花园欣赏者的注意。
建造花园的人更了解花园,他们正是认清了花园的两面,或更准确地说是认清了欣赏者的两面,才敢于继续为人们建造花园,因为纵然花园有两面,但善用它则会令人幸福,如古波斯谚语所云:“建造花园的人会与光明为友,没有任何一座花园在黑暗中诞生。”
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上,人为什么喜欢并建造花园?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有很多,但最简单的一个是:因为花园让人感到幸福和舒适,“人类总是执着于将一方土地变成伊甸园,这一现象反映了人类对宁静、祥和以及平衡的需要,因为人类总是处于死亡的命运与对永生的渴望的永恒矛盾之中”(同上书,第5页)。在现实的艰涩和困苦中,花园就是一个短暂安抚和告慰我们精神生活的乌托邦。在《乌托邦》中,花园代表着美好生活,是理想城邦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在现代反乌托邦的故事里,花园的缺席也格外显眼。而反乌托邦的批评本身是另一种乌托邦,反乌托邦中花园的缺席恰恰彰显了它与幸福生活直接相关。
其实贝鲁埃特写这本书的用意十分明显:他想要揭示,花园不仅代表了一种世界观和社会构想,同时还表达了一种对生活理想和道德模式的追求:(同上书,第398页以下)
首先,花园是极好的、美丽的、幸福的现实理想空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所有乌托邦和乐园的原型;
其次,园艺培养了许多同美好生活相关的美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从来不是现成的,而是靠劳作实现出来的;
第三,园艺和哲学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恢复了人们对世界的信息,使人由内而外焕发新生,自身也为其获得能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身体就是花园,而我们的意志担当了花园里的园丁(《奥赛罗》,第一幕第三场);
最后,在花园中可以学到重要的一课就是学会等待。明白要收获就必须先播种;要开花就必须先发芽。花园能让我们摆脱现在的市场逻辑,不再贪求过多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清楚知道什么才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回到自己曾经遗忘的乐园。而这,也就是重新找回那个所有人都遗忘的苏格拉底问题:“人应如何在世生活?”
——特别是当我们再一次为现下的疾病甚至死亡所逼迫时,如何珍惜和把握今生就显得尤为重要。
撰文丨郝春鹏
编辑丨董牧孜,校对丨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