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米亚·科托的《梦游之地》《耶稣撒冷》《母狮的忏悔》在中国出版中译本。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他曾经这样说起自己的这三部小说:
《梦游之地》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写这本书是在1992年,当时战争(莫桑比克内战)还在继续,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情绪是非常痛苦的。在那场战争里有大约一百万人丧生,而且战争持续了整整十六年。这是唯一一本我在写的时候非常痛苦的书。
而《耶稣撒冷》这本书里有一个主角“我”。你读过的话就会明白,这个“我”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因为我在这本书里讲述的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我写这本书,是想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来了解自己。
至于《母狮的忏悔》,写这本书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项蛮大的挑战,因为这本书基于一个真实事件。对我来说,得找到一个办法把现实转化成虚构,把事件转化成小说。

米亚·科托(Mia Couto),1955年7月5日生于莫桑比克第二大城市贝拉港。当今葡萄牙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米亚·科托的小说,“没有典型现代主义小说的晦涩、多义、含混的风格;但在词汇、句法、修辞上,却又如同诗歌一样具有丰富的意象和强烈陌生化效果。”那么,可以称之为“诗意小说”、“诗化小说”、“诗性小说”或“以小说形式所写的诗歌”吗?本文作者提出,我们需要暂且放下这些标签的束缚,去理解他的诗艺,去理解他身后的非洲。
米亚·科托的写作风格,经常被认为受到拉美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他本人对“魔幻现实”的提法并不认同。“他的确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他所书写的就是现实,现实就是他的诗艺的源泉。”
这算是小说还是诗歌呢?
对于现代文学,我们执着于强调文本的体裁已经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很久以前,小说旨在讲清楚一个故事,是富有戏剧性和鲜明人物特征的叙事文本;诗歌则因为对意象、修辞和韵律的使用,相对而言比小说要复杂难解得多。后来,小说和诗歌似乎掉换了位置,晦涩难解、含混多义的小说越来越多,诸如卡夫卡、乔伊斯、罗伯格里耶、巴塞尔姆等等;诗歌反而不乏越来越通晓明白,甚至故意使用大白话的作品。所以,小说与诗歌在体裁上尽管截然不同,细究起来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去年底我读完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的三部小说,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算是小说还是诗歌呢?
因为,这三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和作者意图都十分鲜明,并没有典型现代主义小说的晦涩、多义、含混的风格;但在词汇、句法、修辞上,却又如同诗歌一样具有丰富的意象和强烈陌生化效果。
那么,能否使用“诗意小说”、“诗化小说”、“诗性小说”等标签,或是“以小说形式所写的诗歌”等来描述米亚·科托的这一整体风格?似乎意义不大。在当代,一个小说里稍微有一点“超现实”的描述,或是“陌生化”的笔法,或是安排一个不合世俗逻辑的情节,轻易就会被冠以“诗意”或“诗性”的头衔。而且,在了解西方文学传统的读者看来,“诗”本身的内涵从古希腊戏剧时代起就日益精深,轻率地使用“诗”这个字眼的确容易滋生误解。
于是,当我阅读米亚·科托之后,如何处理对他的“第一印象”,如何安放我作为一个汉语读者的“阅读视域”,都显得十分困难。我决意不再去固执地定义他小说的性质,而是不妨谈论一下他那鲜明的诗艺。
他一直位于政治光谱里,弱势的、人道的、自由的、人文的一边
谙熟文学理论的读者一定知道,倘若一个文学文本的“中心思想”非常清楚,作者的“创作意图”昭然若揭,那么脑海里很多跃跃欲试等待“庖丁解牛”的文学理论就会显得很落寞。
对米亚·科托的小说,我没法使用“后殖民”、“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等批评术语。这主要是米亚·科托在小说中已经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盘托出,毫不神秘。关于莫桑比克摆脱殖民统治的反抗,关于赢得民族独立后在冷战背景下的内战,关于内战后和平年代里的社会问题,米亚·科托不仅在小说中进行了明确的书写,更在诸如作品的前言后记以及一些演讲和文章中予以干脆的指出。即使读者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在今天的条件下,只要稍微动一下手指,就能查阅到莫桑比克的历史——包括对米亚·科托本身作为殖民者后代的心路历程。
米亚·科托是一个笔名,他是葡萄牙殖民者的后代。葡萄牙的殖民活动从15世纪开始,到17世纪臻于极盛,“二战”后才被迫放弃殖民,持续了将近500年。所以,米亚·科托之于莫桑比克固然可以视为殖民者后代,但在如此漫长接近明清两个朝代时段的殖民史中,我们可以想象米亚·科托与莫桑比克的渊源之深,究竟哪个是故乡?
当莫桑比克的民族自决运动兴起时,米亚·科托不仅“反殖”,还“反专制”,这里指的是葡萄牙本国的独裁政府。在莫桑比克赢得独立后,他又挺身捍卫莫桑比克的土著传统、土著语言,反对当时的政权对传统的清算,总之,米亚·科托一直位于政治光谱里那个弱势的、人道的、自由的、人文的一边,始终未变。
这就很容易探知他小说的主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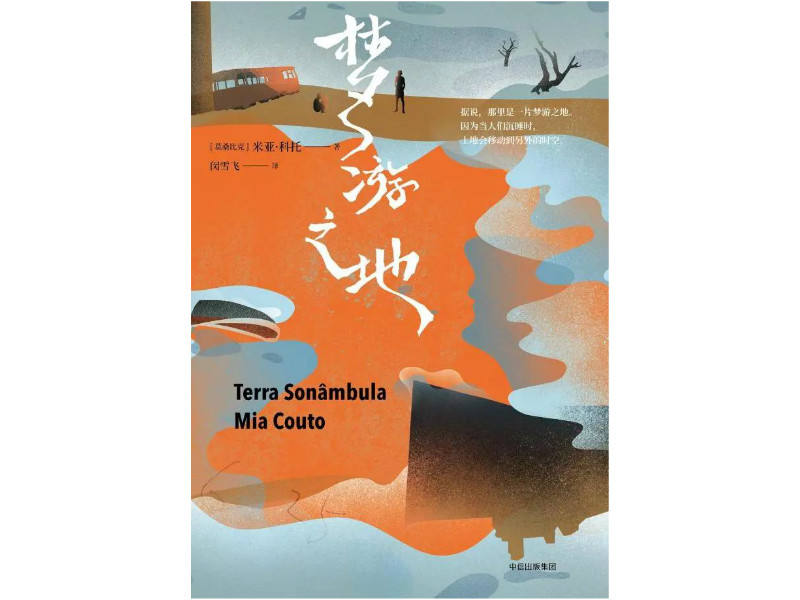
《梦游之地》 作者:米亚·科托 译者:闵雪飞 版本:中信·大方 |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8月
以我阅读的三部中译本小说为例,1992年出版的《梦游之地》挥之不去的是内战,毕竟1992年该国内战才刚刚结束,这意味着米亚·科托是在内战进行之时撰写这部小说,其性质宛如战争实录,至少也是战争的“影子书写”。《梦游之地》第一句话就摆明了要对内战进行控诉:“在那个地方,战争杀死了道路。”毫不掩饰,毫不留情。《梦游之地》借助内战中一老一少的生活和对一个捡到的日记本的阅读,一面逐渐揭开这一老一少在战争中的命运,一面反复申说梦游与现实的关系。个中隐喻不难猜测:内战的根源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梦”与维系传统的“梦”之间的游移与冲突,换言之,也就是一个刚刚摆脱殖民的民族,其意欲塑造的自我与其内在的冲突。此外,因为《梦游之地》是作者的长篇处女作,所以比后来的作品更具一种猛烈、阔大、繁复的阅读体验,这恰恰体现了米亚·科托的野心和才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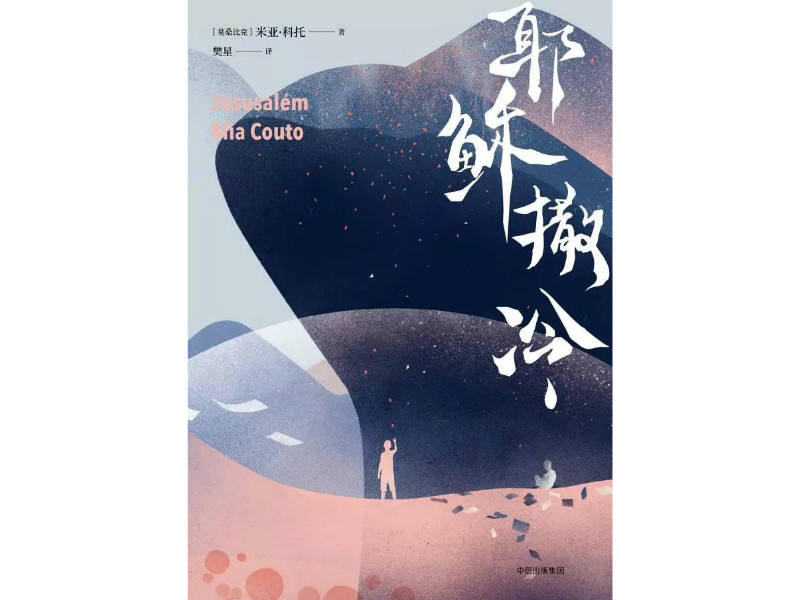 《耶稣撒冷》 作者:米亚·科托 译者:樊星 版本:中信·大方 |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8月
《耶稣撒冷》 作者:米亚·科托 译者:樊星 版本:中信·大方 |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8月
2009年出版的《耶稣撒冷》是一部各方面都恰到好处的成熟之作,它的主题更加清晰可辨,叙事更加简练优美,诗句迭出又不晦涩。米亚·科托关于这部作品曾主动交代:“我最关心的主题之一,是我们与时间之间关系的困境。”《耶稣撒冷》描写了一个男人在妻子去世后,带领家人远遁都市,在荒野里建立了一个叫做“耶稣撒冷”的乌托邦,但他并非开辟新宗教,而是旨在遗忘。所力求遗忘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莫桑比克的内战创伤和对信仰的不再信任,但遗忘于情于理均无法做到,这就是米亚·科托所说的“莫桑比克人与时间关系的困境”。在小说中,米亚·科托“安排”了一个白人女性来到耶稣撒冷,打破了困境,戳穿了遗忘的无法遗忘,最终耶稣撒冷解体,那些无法遗忘的种种成为了建构未来的材料。在处理这一主题时,米亚·科托还格外凸显了“白人女性”这一意象的意义,再加上每一章节开头引用的女性诗人的诗歌段落,使得作者“以女性救赎遗忘”的意图更加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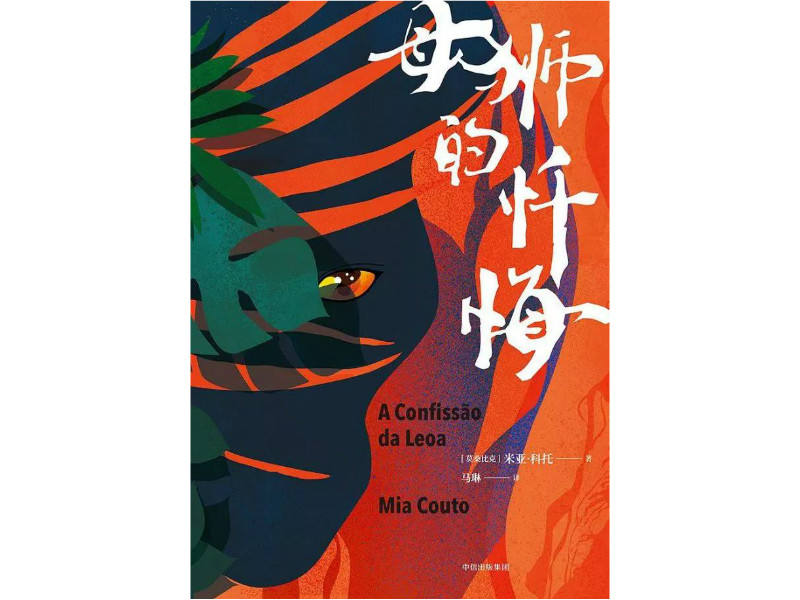
《母狮的忏悔》 作者:米亚·科托 译者:马琳 版本:中信·大方 |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5月
但这一意图最明显的当数2012年出版的《母狮的忏悔》。这个故事迫不及待地向读者宣告了伸张女性主义的主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莫桑比克乃至非洲贫困村落的底层女性伸张爱、性、婚姻的权利。坦率地说,这个故事比前面两个作品逊色,这不仅体现在主题演绎上的粗陋,还体现在情节与叙事的毛糙,缺乏《梦游之地》的委婉与奇妙,也没有《耶稣撒冷》的圆润与清晰。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部作品源于米亚·科托担任记者时所接触的真实事件,这应是《母狮的忏悔》在技巧上不够出色的根本原因。
他的叙事,几乎是用诗歌式的语言连缀而成
透过这三部拥有中译本的作品,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米亚·科托的创作从早期主要书写内战,到中期主要反思内战并关注到性别、父权等社会问题,再到近期主要以社会问题为主,其主题变化有着可追溯的演变。
那么,用何种方式来表达这些主题就成了至为重要的问题。要知道,战争、女性、信仰、传统等等,都是基本的文学母题。莫桑比克的内战再激烈,女性再备受压迫,信仰再徘徊无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再剧烈,对于大多数异域读者来说是不陌生的,读得多了还觉得乏味呢。假如遇上一些持“阴谋论”的读者,甚至还会揣测作者专写这类主题,是不是冲着讲究政治正确的文学奖去的?等等。
米亚·科托不惧于此,正在于他的作品的魅力本不在“中心思想”,而是任何读者阅读后都会感到奇妙、会迅速被吸引、会不知不觉拿起笔勾画警句的语言。我思索良久,认为只能用“诗艺”来概括他的语言技巧。
他的诗艺首先体现在叙事的遣词造句。与那些偶尔来一段诗歌式、超现实描写,或是在开头结尾来一些诗意抒情的小说不同,他的叙事几乎是用诗歌式的语言连缀而成。词与词通过各种拟人、通感、比喻等修辞来组成句子;句子与句子之间像两个陌生人在自说自话;而段落与段落之间则像蒙太奇。总之,读者很不容易捕捉其叙事的逻辑,却很容易陷入修辞和韵律的美妙,因此,恰恰是靠着对作品“中心思想”已经了然于胸的前提下,以阅读诗歌的方式阅读,才能继续前进,不至于陷入迷惘。
我们随便翻开他的小说的某一页,把其中的某一段话按照诗歌的形式排列,上述特点就更加清楚,如《梦游之地》的第五章(第99页):
那深深的河床里必须有一条河流淌
直至汇入无尽的大海
河水将安慰无数的干渴
滋养游鱼与大地
希望与未竟的梦想会沿河而行
这将是大地的分娩 从这里
人们再次守候生命
毋庸置疑,尽管有翻译的“屏障”,但我们依然能从中感受到强烈的诗意,小说主要就是依靠此类句子来完成叙事,充满着意象的驱遣、情感的贯通、修辞的运用,令人难忘。
这里不免要谈到翻译的问题,根据中译本几位译者的陈说,我们了解米亚·科托在葡萄牙语文学里的魅力,恐怕只有通过葡萄牙语的阅读才能真正体会。但毕竟大多数中国读者无法阅读葡萄牙文,而且这也是任何翻译都无法克服的内在本质,翻译之所以有好有坏,也恰恰在于此。上述三本米亚·科托的中译足以使我们认知米亚·科托的诗艺。
他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他所书写的就是现实
显然,语言并不仅仅是米亚·科托诗艺的唯一体现,还包括小说整体上具有的诗意氛围。这来自于作者把一个拥有现实背景或现实诉求的故事装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叙事框架里。
在《梦游之地》里,这个框架是一个做梦之人的“闭环”经历,在《耶稣撒冷》里,这个框架是一个家庭离群索居建立遗忘的圣地,在《母狮的忏悔中》,这个框架是母狮与女人从肉体到灵魂到身份上的叠加。
在这些大的叙事框架下,充满着许许多多离奇的情节,每个故事都是由各类匪夷所思的情节所推动。例如,《耶稣撒冷》里扎卡里亚讲了一个小故事,“士兵永远受着伤,战争甚至会伤到那些从未投身战役的人。这名小战士每当咳嗽,都会从嘴里吐出大量子弹。”(p85);再比如,《梦游之地》里,肯祖抄起砍刀挥砍一棵树,树中有一个声音说:“我是最后一棵树,砍到我的人,如果是个男人,将会成为女人,如果是个女人,将会变成男人。”(p219)等等。
这些微观的奇妙情节会令读者欲罢不能,也是米亚·科托诗艺的另一个体现。那么,这些情节从何处而来?或者更确切地说,米亚·科托如何构思出这些情节?

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1927年3月6日-2014年4月17日),哥伦比亚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等。马尔克斯被认为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最不负责任的猜想是“魔幻现实主义”。自从马尔克斯之后,魔幻现实主义似乎成了无数读者的懒惰托词,每当面对通过丰富的想象力、通过超越现实和科学逻辑的叙事反映现实社会的文学作品,大家似乎找不出第二个词来描述。于是,一方面这对很多作品是误读的,另一方面也使得魔幻现实主义被常态化、庸俗化,失去了描述的力量。我记得莫言获奖时,很多读者也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他,至于诺贝尔官方给出的描述“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却不怎么流行。
米亚·科托也是如此,我已经见到了不少读者用这个词来描述他,豆瓣上还有读者用这个词来贬低他。米亚·科托旨在书写现实,这一点并无不妥,但他作品里情节的“超现实”、语言的“陌生化”真的是一种“魔幻”吗?或者说,米亚·科托的诗艺是对半个世纪前的模仿吗?
非也。这种印象恰恰暴露了读者对于非洲文学的无知。作为文学版图里经常被遗忘,仅仅在政治需要时才被提起的非洲大陆,除了人类学家,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对非洲的巫术、传统、民间信仰等真正保有兴趣,即使有兴趣也未必能获得货真价实的相关知识。
米亚·科托书中的许多奇异的情节和富有新意的语言,脱胎于非洲本土、土著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文化观念以及日常语言等,换言之,这些外邦读者认为是“魔幻”的情节,并非作者对莫桑比克现实的“隐喻”或“虚拟”,而就是当地的“现实”。米亚·科托夏天来华时,在一次专访中说:
“我认为魔幻和现实这两个东西就是一体的,现实就是魔幻,不存在什么魔幻现实主义。”
——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年8月17日。
在《梦游之地》所附米亚·科托的一次演讲中,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一群瑞典科学家到莫桑比克开展环保工作,到了村子里,科学家说:“我们是科学家”。但土著语言里没这个词,于是翻译只好近似地翻译道:“我们是男巫”。科学家说:“我们到这里搞环境”,土著语言里同样没这个词,翻译只好又用了一个最接近的词,但这个词在土著语言里意义丰富,包括了诸如宇宙起源、人类诞生等意思。后来科学家问:“最困扰你们的环境问题是什么?”土著很迷惑,想了想说:“野猪”,因为野猪在当地还指病死之人变成的幽灵。科学家当然会说,“好办,把野猪赶走!”土著则陷入了迷惑:“怎么能把幽灵赶走?”
这不仅仅是翻译和沟通的问题,而是两种思维。列维·施特劳斯在《神话思维和科学思维》里,亦已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不过他举的例子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在他的故事里,一个印第安男子走到一处岔路口时,他的身体分裂成两个,各自走在不同的岔路上,等岔路再度合一,分裂的身体也再度合一。列维·施特劳斯惊异地发现,在土著的语言中,这个男人的名字形式上是“复数”,但意思却表达“单一个体”。用科学思维来看当然矛盾,但印第安人习以为常。施特劳斯借此指出,诗人会通过原创、生造的语言来创造诗艺,而神话“通过各式各样经常矛盾的意象,让人能够感知一个无法被直接描述的结构”。
无独有偶,这恰恰是米亚·科托诗艺的另一个面相,他的确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他所书写的就是现实,现实就是他的诗艺的源泉。只是我们太不了解莫桑比克,不了解非洲,所以才会忽略这一点。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对自己传统和民间社会中的“现实”的理解,又能深刻到哪里呢?
作者:张向荣
编辑:西西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