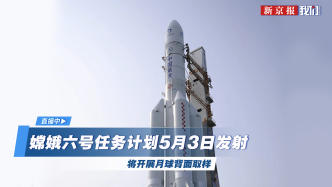21世纪信息大爆炸时代的来临,对史学研究的方式、方法造成了巨大冲击。数据库的出现与普及更是引发了不小的震动。诸如四库全书、历代笔记、朱批奏折、近代报刊、内阁档案,等等一系列文献数据库如雨后春笋般纷涌而出。新一代的历史学者赶上了技术革命带来的原始红利。只需动动鼠标,登录界面,单击右键,就可以根据输入的关键词轻而易举地找到上千条相关史料。以数据检索为基础的“E考据”正越来越多地受到青年历史研究者的喜爱,老一代史学研究者埋首书案、皓首穷经的史料搜集法正在走向日暮黄昏。
信息时代对历史学科的冲击不仅于此,它更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在过去,史学作为一个专业研究领域,主要供同行之间讨论点评,是一个边界相对严格的“小圈子”。这个圈子对文献档案拥有近乎绝对的掌控权,并将其居为奇货,并不情愿对圈外人士分享开放。但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大量原先圈外人难得一见的文献档案得以开放,任何感兴趣的公众都能自由运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传统史学对史料的垄断被打破了,各式各样基于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媒体平台,也要求高居象牙塔里的历史学者走出塔外,面对公众发表自己的观点。历史写作不再是同行之间小圈子里的讨论点评,而是成为天下之公器,人人皆可加以议论指摘。史学越来越由一个学院里的专业学科迈向一个面对大众的公共事业。
当下的历史写作,当如何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强大的数据库在给予研究者以搜集史料的便捷同时,是否也培养出研究者过度依赖技术的惰性,从而消磨了传统史学中穷经尽牍的刻苦精神?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呼唤,历史学者是固守学院畛域之别,还是勇敢面对公共舆论的挑战?
本篇对青年历史学者仇鹿鸣的专访,将对上面提出的这些问题,以一位受过传统史学训练、又享受信息技术红利的亲历者身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2020年9月1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新史记: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的历史写作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读书时代
适逢学术写作的转型期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石刻文献等。著有《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等。
“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
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这一段话,常常被仇鹿鸣拿来引用。在他看来,历史学人既是职业读书人,也是知识的生产者。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当我们书写历史时,我们才能理清事件之间的关系,消除思想中的矛盾,并对可能面临的质疑提前做出解释和修订。
历史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说:“历史研究其实是在处理人类生活当中的戏剧,也就是人的不同个性,这其中包括自我意识、理智与自由。”优秀的历史学者和优秀的演讲家有着诸多共通之处,他们的目的都在于发现那种具有张力的戏剧性,并以此吸引读者-听众的耳目。一个优秀的演讲家所说的话可能存在前后矛盾、语义不清的地方,但仍能通过声音、语调和情绪左右听众的想法。而优秀的历史写作也总是要抓住读者最揪心,最张力的触点作为起笔。对于一名写作者来说,他们不仅要保证自己的论据是有效的,也要让观点具有逻辑性,经得起读者一遍又一遍地研究和推敲。因此,相比戏剧舞台上的表演家,或是公共舞台上的演讲者,作家往往需要扮演一位更加勇敢的角色。
作为学院派青年历史学者的代表人物,仇鹿鸣的历史写作生涯开始于研究生阶段,本科直博的经历让他接受了现代学术体系的磨炼,同时也深感学术评价体系对于写作者的制约。时下学术论文越写越长,大量材料反复堆砌的风气让他不以为然。无论史料和话题是否有趣,写作的首要目标是力求简洁而明炼。
仇鹿鸣说,自己在读书时代正好赶上了学术写作的转折期,既没有丢掉老先生教导的传统史料学训练,也享受了信息时代为历史学者带来的原始红利。数据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史料收集的范式,却也让不少年轻学人学会“偷懒”,忽略了文献学和目录学的训练,对于史料的重要性程度失去了基本的判断。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作者:仇鹿鸣,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8月。此书为仇鹿鸣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也是他的成名作。
对话仇鹿鸣
新京报:你曾在多个场合提及,历史研究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持续不断的写作习惯对历史研究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历史研究和写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仇鹿鸣:这个问题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研究生到成为大学老师的阶段,一个历史学人最基本的定位是职业读书人。我从研究生生涯到现在已经有17年的时间,我觉得人生最愉快的时光可能就是研究生的前几年,那个时候没有特别需要发表作品的压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漫无目的地阅读。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设置博士点,提供大学教师岗位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对学术有所推进。因此,研究生的训练,尤其博士生阶段的训练,是要培养专业的研究者,把你从一个美食家变成一个厨师,或者说,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知识的生产者。
有一些老先生说,十几年不写文章是为了足够的积累,这种看法我并不认同。现代的知识与民国时代大不相同,学科高度细分化,每个学者都进入一个特别细分的领域。所以,学者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写作时间,先解决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比较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积累起信心,然后再慢慢学会如何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专业的研究。随着阅读和研究的范围扩展,你可能可以解决稍微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我不太相信,一个人从未写过一篇好文章,或者几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表,能够突然在十几年之后发表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或著作。因为无论是收集材料,还是论文写作的技巧,如何让读者来接受,,其实都需要大量训练。

《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作者:仇鹿鸣,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
新京报:学术写作也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相比以前,学术评价体系对历史研究者的写作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外在压力是否会对研究和写作带来额外的负担?
仇鹿鸣:刚才我们说到历史研究者拥有知识生产者的身份,但回到中国的学术界的确存在着落差。很多青年教师存在着过劳的情况,就像现在网上常说的“学术圈的内卷”。我自觉一年能写出两篇比较像样的文章,要写出三篇就感觉比较吃力了。很多比我还年轻的同行或学生,为了应对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一年写五六篇甚至十来篇的论文,这让我对这些作品的学术质量感到担忧。当然,青年学者面临的压力是全球普遍的,在世界范围内对年轻的学者的压榨都很强烈。
新京报:作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你平时会看一些通俗历史读物吗?你怎么看待市面上常引发舆论关注的通俗历史读物和历史改编?
仇鹿鸣:前段时间出版的《显微镜下的大明》,就是作者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写出的很好的通俗作品。但是,这样的工作其实最好由历史学家自己来完成。通俗不等于简单,不等于迎合民众,《万历十五年》、《叫魂》这样的作品,虽然产生了超出学术圈的效应,但也不能说是通俗历史读物。而且,不同身份的读者阅读《万历十五年》的体验也是不同的。

畅销历史小说家撰写的通俗历史著作《显微镜下的大明》(博集天卷 |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一经推出,便风靡海内。这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全部建立在专业历史学者严谨的论文之上。马伯庸的这本书被认为是将专业历史研究通俗化和商业化的典范之作。
中国的学院派学者较少写出这类有“出圈”效应的作品,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制度使然。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学术评价体系没有彻底区分专著与论文,很多学者的专著只是他们的论文集,有一些会做些修改,但不懂得如何写出有设计感的专著。考核和评级的压力让多数学者专攻学术论文,也是很常见的情况。
如何提高写作技巧,我还没有想到特别好的办法。我的第一本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之所以受到历史圈外的关注,倒不是因为写作上的特殊技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三国题材在中国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对于纯粹的论文写作,首先就是简练而清楚。由于数据库的技术帮助,现在的学术论文的一个倾向越写越长,很多是大量的材料铺排。首先你需要让别人很清晰地明白你在谈论的问题,至于能不能写出有趣味的、让人觉得有吸引力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受到材料的限制。没有好的材料,再高明的写作技巧也是空想。
新京报:成长于信息时代的历史学者,在搜集史料方面与老一辈的历史学者有什么不同?新技术的变革如何影响历史写作?
仇鹿鸣:需要承认的是,数据库的出现,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我自己正好赶上这个转折的时代,当时《四库全书》的电子版正值上线,这么庞大的数据库,还可以让你进行全文检索。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数据库帮助我们可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写出比较多的、质量还不错的论文。与我们的老师相比,我们积累材料时间比较短。过去,很多老先生都是用手写的卡片来积累史料,其实是通过手抄的方式自己建立一个数据库。后来的学生就把相关材料抄下来,分门别类地放到自己的柜子里。在我们刚开始念书的时候,其实老师还是建议我们要做卡片的,这就是过去时代认可的积累材料的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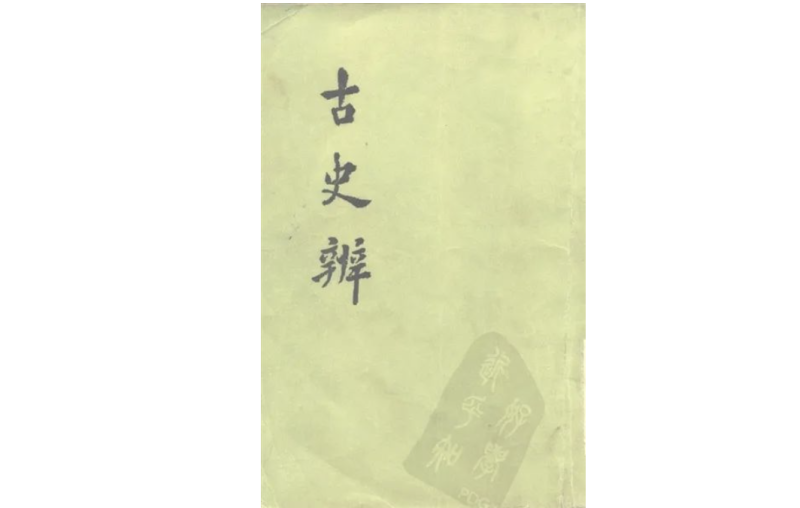
《古史辨》,编著:顾颉刚,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由历史学家顾颉刚等人共同撰写的论文结集《古史辨》,是现代中国“疑古学派”的代表作品。疑古学派的文章刊出后常常饱受争议。其中固然不乏闪光之处,但也颇多揣测过度的不经之论。但其对史料所秉持的怀疑辨析的治史态度,至今影响深远。
信息化带来的另一个直观感受是,我能够更快地确定哪些题目不能写。我们在研究中写出来的文章,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其实还有更多的题目已经被你自己否定掉了。这个过程对读者来说是看不到的。在过去,你可能花了好几个月收集材料,最后发现原来的设想是完全错的。数据库提供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就是可以让我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总结这样一个题目,少走了很多弯路。
数据库的出现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过去的学者收集材料就要花几个月甚至一年,有了数据库之后,这个工作相对来说变得比较简单,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你提出一个问题,发现前人已经证明过了,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取出更多的材料来强化这个观点。这种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但相对来讲,史料价值有了明显的下降,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换句话说,数据库在降低了学者收集材料的压力之后,对学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如何更好地分析、利用、解读和批判史料。从这点上来讲,我们还处在吸收数据库的原始红利的阶段,前面还有很长的路。
另外我也发现了一个随之而来的弊端,就是很多学生,特别是年轻的学生,由于有了这个辅助工具,忽视了传统意义上的目录学的学术训练。因为数据库是超链接形式的,它是不断跳跃的,是碎片化的,而且是目的性很强的。如果数据库代替了传统的目录、史料学的训练,代替了文本精读的话,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刺激学术生产数量的增加,但从长远来说可能会降低研究的品质。
采写|李永博
编辑|罗东 李阳
校对|张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