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在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新旧力量冲突最为激烈、社会矛盾和斗争最为复杂的时期来到中国,见证了当时中华大地的社会剧变和历史转型,并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中国待了两年多,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的思想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文化、政治、社会,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
杜威来华经过
超出预期的巨大影响
1919年2月,杜威携家人利用学术休假机会赴日本游历、讲学。此事被其中国学生们得知,立即协商请他来华。3月12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陶行知(时名“陶知行”)致信胡适,称如果能借便“请先生(杜威)到中国来玩玩”,并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则“再好不过了”。胡适接信后立即致函杜威,邀他旅华讲学。适逢北京大学陶履恭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正欲赴欧考察战后教育,顺道经过日本,二人受胡陶二人嘱托,到东京后立即拜访杜威。杜威愉快地接受了这次邀请。随后北大校长蔡元培致电哥伦比亚大学,从官方协助支持,落实了杜威在北大进行讲学一年的工作事宜。
1919年3月上旬,胡适以“实验主义”为题,在教育部进行了4次讲演,全面介绍了杜威的哲学思想,评介了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形成、渊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同时还对实在论、真理论和方法论等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解说。关于实用主义的方法,胡适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成为流传至今的名言。这些讲演内容,先后发表在《新青年》《新教育》《新中国》等刊物上,可以说,杜威还未到中国,教育界对他已有了基本了解。
4月28日《申报》发布消息说,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自西京来电,定于30日到沪。并称“博士为世界思想领袖,教育先导”。4月30日,杜威偕夫人爱丽丝·奇普曼(Alice Chipman)一行乘坐“熊野丸”轮抵达上海,胡适代表北京大学南下,与南京高师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等多家教育团体,一同在上海码头迎接杜威到来。

1920年5月10日,江苏省教育厅欢迎杜威夫妇(前排中立者)。
杜威原计划在中国待到当年夏天,然而到中国后的第4天,便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个古老的中国迸发出来的青春热情和生命力深深吸引了他,他在给哥伦比亚大学同事的信中说,“西方再也看不到同样的东西,这几乎是恢复青春……”他想留下看个究竟,便改变了回国计划,并两次续假延长时间。最后,他到1921年8月2日才离开中国,在华时间共计2年3月又3天。
他先到了上海、杭州和南京,参观了一些中小学和地方高校、工厂,然后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的演讲及在各地的巡回演讲。两年多时间里,他一共作了二百多次讲演,大部分是关于教育问题。抵达上海后的5月3日和4日,他在江苏教育会作了两场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由蒋梦麟口译,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座为之满,后来者咸环立两旁”。
此后,他先后在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等地作了十六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十六次教育哲学讲演,十五次伦理学讲演,八次思维类型讲演,三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系统地介绍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其足迹遍及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的热烈欢迎。
两年多时间里,胡适从各方协调安排杜威的行程,并陪同他在北京、太原、济南和天津等地讲演,担当翻译。陶行知、郭秉文、刘伯明等杜威的其他弟子也参与其中。对杜威这些艰深的哲学和教育思想,胡适生动地进行了中国式传达。在他和陶行知的帮助下,讲演内容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纸杂志上,其中《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和《伦理讲演纪略》被汇编成《杜威五大讲演》一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自1920年6月出版至1921年8月杜威离华前的一年时间内,重印了13次,每次印刷达万册,此后又多次印刷。杜威在当时中国产生的轰动效应,可见一斑。
可以说,杜威是五四时期受到中国知识界一致欢迎的思想家。陈独秀、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胡适、陶行知、冯友兰等等,无不受其影响并给予较高评价。梁启超把他与近两千年前龟兹国(今新疆库车)的鸠摩罗什相提并论,认为他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重大革命,并表示“中国人宜以杜威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瞿秋白认为:“中国的宗法社会……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就连孙中山总结革命教训,为了否定中国古人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佐证强化他的“知难行易说”,还专程去拜访杜威求以质证之,得到杜威的同样看法而信心大增。杜威的中国之行影响深远,大大超过了当初预期,以至胡适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甚至还断言:“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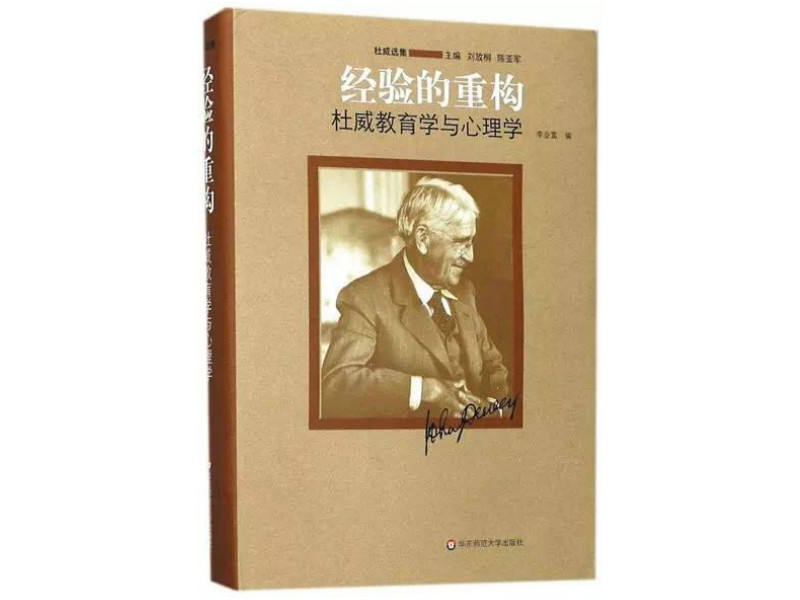
《经验的重构:杜威教育学与心理学》 作者:(美)约翰·杜威 编者:李业富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
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美好的期望和善意的批评
杜威一直对中国政治和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时刻关注中国的问题与时局命运,包括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用他女儿的话说,中国是杜威仅次于美国最爱的国家。杜威前后留下了几十万字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包括时论、论文、游记、来信答复、解密报告、家信和演讲等各种形式。他描述了当时中国发生的各种现象,除了评论和对策建议外,也包含着他对一些中国人与现象的批评。他的批评是善意的,是基于希望中国繁荣发展的美好期望。
他一踏进这块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国度,便爆发了五四运动。对国际时势的关注和此前对东方的无知,使他对这块土地充满了好奇。有人说他既是一名访客和旁观者,又是观察家,既是老师,又是有学问的学习者。1919年6月1日,他在给子女的家信中说道:“我们正好看到几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出发去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讲而入狱的男学生。要说我们在中国的日子过得既兴奋又多彩,的确是相当公平,我们正在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但通常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五四运动席卷了全中国,从北京到上海乃至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纷纷给予支持。最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杜威说:“你无法想象未签署《巴黎和约》对中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可说是属于公众舆论的胜利,也可说归功于这些男女学生的推动,当中国能独力做到这类的事情时,美国实在应该感到羞愧。”在《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他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
此前的十年里,西方数次宣称“中国正在觉醒”,杜威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当他看到高师工科部的学生动手建造三幢校舍,工科部受到鼓舞想办艺徒学校,来为工厂提供好的工人,而棉业行会非常热切和学校合作时,他敏锐地感受到,这是“商人和行会第一次真正受到鼓舞起来改进实业方法”,“这是一次真正的觉醒,并且是和学生一道”。在1919年7月4日的信件中,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有趣、在学识上获益最丰”的一次旅行。
对中国的热爱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事情的判断。尽管他被自由主义的学生和“新青年”们包围,但他并不完全同意他们对事情的看法。他认为,必须从中国自身的情况出发,去理解中国的历史,而不应该用近代西方的那些政治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历史状况。他认为,现代中国遇到了一个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自身不同的组织起来的世界,遇到了一种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人的力量,而是无法计算的物质力量——战舰、大炮、铁路、奇怪的机器和化学制品。中国必须改革,但因为有自己长期形成的政治传统和见解,变革将变得长期而艰难。
对于美国和远东、中国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在外交和政治上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家长式的”。在许多家庭中,当处于照料和保护下的青少年成长到足以宣誓独立时,就会有危机。在国家这个大家庭中也一样。“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们很可能需要许多耐心、宽容、理解和善良的愿望,把已经带上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赞助人色彩的传统家长式态度,转变成对于和我们平等的文化的尊重和珍视的态度。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作出这种转变,这个国家和整个远东的关系将决定性地变得更糟。”
杜威认为,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容易引起误解,他劝说美国不要干预中国内政,呼吁美国“要像国家对国家那样对待中国,而且要让其他国家寻求类似独立不依的道路”,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彼此互不干涉,而且给每个国家一个处理自己事务的机会”;美国应该取消所有的特权和单方面的关系,以便使中国人的注意力可以聚焦于改善他们自己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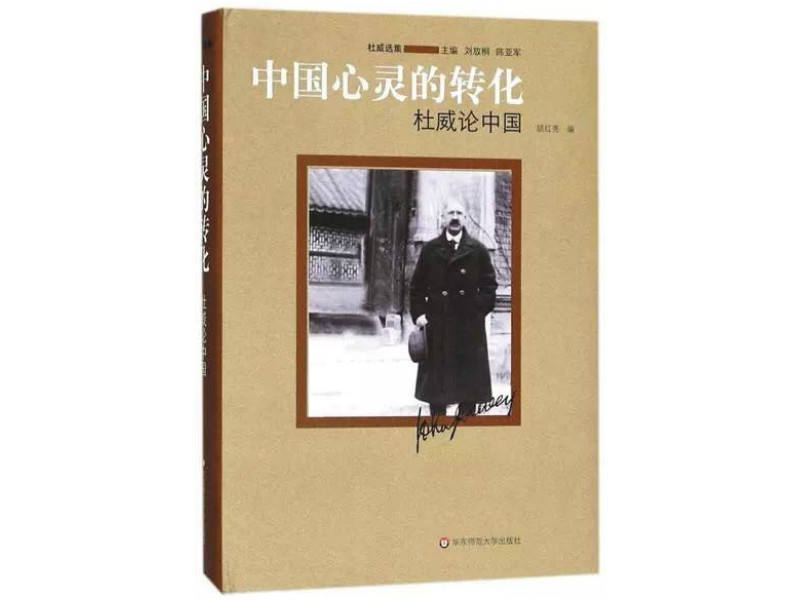
《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 作者:(美)约翰·杜威 编者:顾红亮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
杜威的中国弟子们
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
杜威思想在中国广泛的传播,除了其思想本身的魅力之外,还得益于他众多中国弟子的宣传推广。20世纪初,中国不少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杜威的有郭秉文、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张伯苓、刘伯明、郑晓沧、李建勋等人。这些人回国后大力宣传杜威思想,同时用杜威思想积极指导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从文化教育、思想学术等各方面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他们对杜威的思想也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杜威夫妇与学生参观申报馆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爱丽丝·奇普曼、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郭秉文(1880-1969)是最早接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中国学者,他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即参与南高师创办,先后任南高师教务主任、校长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他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被教育界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他直接将杜威的思想应用于改革实践。他邀请杜威来南高师做报告,聘请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来校任教,管理东南大学时,他延揽师资,崇尚实学,并将数百名中国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迁来南高师,使之成为南高师、东大师资的主要来源。他重视学生的个性培养,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兼顾个性发展的教育方针,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由选择学习科目或有一定限制地选课。他倡导民主治学,通过“三会制”将教授治校放在首位,在学生中实施“自动主义”,使东南大学成为实施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胡适是杜威最为知名的中国弟子,他于1910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被公认为接受和实践杜威社会和政治学说第一人。在阐释杜威的经验主义时,他说,“教育即是继续不断地重新组织经验。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人生四围的境地;即是改变所接触的不知所措,使有害的变为无害,使无害的变为有益……”经过胡适的解释,杜威的“经验”成为与“生活”相同的含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生活,便是增添经验,进行教育。这一解释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杜威生活教育观的基础。
胡适尖锐地批评当时的中国学校教育与社会严重脱节,认为这是亡国的教育。1922年领导新学制改革时,他将“注重生活教育”和“注重个性之发展”列入“七项标准”中。他强调教育与生活的一致性,强调要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为发展个性教育,还主张在学校采用选科制和学分制,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教育。可以说,胡适完全遵循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结论的假设。”蔡元培也曾说胡适“不但临时的介绍如此尽力,而且他平日关于哲学的著作,差不多全用杜威的方法”。
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曾于1912年赴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1917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担任北大校长及教育部长时,他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推广杜威思想,注意用杜威“生活教育”理论,去观察和分析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以历史教学为例,他指出教学应当以学生生活需要为主体,以平民生活为中心,注重历史与生活的有机结合,并以解决当前问题为要旨。他提倡注重自动、自治与训育,形成良好的民主素养,使个人健全活泼,并提倡个性教育,这些都与杜威的哲学理念一脉相承。
与胡适同龄的陶行知,1914年赴美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学市政半年后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等人。1917年秋回国,开始了他教育和改革实践的生涯。陶行知继承了杜威的教育理论。他强调教育对于社会改造的作用,说“改造了人便是改造了社会”。他认为国家兴亡系于教育,若能普及教育便能影响祖国变革趋向,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他们都重视教育与生活间的有机统一。他继承了杜威“教育存在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是教育的深化和延续”、“教育必须与生活紧密结合”的观点,主张“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生活即是教育,教育即是生活”,倡导民众于生活中寻找智慧,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教育,提升自我。
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国民教育水平落后,列强外来侵略和内战不断。如何开启民智,促进人们爱国觉醒,推动社会变革成为时代的呼唤。陶行知认为对3亿农民普及教育至关重要,1922年,在晓庄师范学校的实践基础上,陶行知结合中国农村实情,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主张,将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思想直接倒了个儿。他提倡的生活教育是一种在社会中、在生活中进行的教育,社会有多大,生活有多广,教育就有多少。他倡导青年应该投身于社会,将教育场所扩大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将人类的生活场所变成人类受教育场所,在社会中锤炼自己的意志品格,形成自己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他看到中国“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学生被动学习,缺乏主动创造性,在杜威“从做中学”的基础上,提出“教学做合一”:“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要根据做的法子”,强调了知行合一,更突出了教学做的有机统一,比杜威“从做中学”的理念更进一步。他的教育理论可以说是杜威思想在中国实践中的创造和发展。正如费正清评价说:“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
20世纪20年代,借着五四运动的兴起和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感召,中国教育改革进入风起云涌的时代。杜威的这批中国学生,在中国大力推动实用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大众教育、普及教育,开创了教育实验的先河,推动了新学制改革。他们将杜威思想引入到教育实验、教育政策的制定、课程教材改革与社会改造中,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受到了批判,他的中国学生们也纷纷受到影响,此后对杜威思想的研究一度陷入沉寂。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知识界开始了对杜威思想的重新反思和评价。时至今日,人们对杜威思想的现实价值、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及他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又重新给予了肯定,对他的研究也成为当下知识界的一大热点。值此杜威来华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在这里讨论杜威、再次认识杜威,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思我们自己,反思当下的教育,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
作者:周雪敏
编辑:徐学勤、李妍、沈河西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