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肯·福莱特
1949年7月5日出生于英国威尔士加的夫,先后在哈罗·威尔德语法学校和普尔工学院学习,1967年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哲学。1978年凭借小说《针眼》荣获埃德加·爱伦·坡最佳小说奖,开始专职写作。1989年出版的《圣殿春秋》,获得巨大成功,2003年BBC将此书列为英国最佳百部小说之一。2007年,他推出此书的续集《无尽世界》,再登各大畅销书榜首位。福莱特作品的最大特色是内容都有史实根据,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与小说中的虚构角色相融合。《圣殿春秋》和《无尽世界》于2009、201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圣殿春秋》
肯·福莱特著,胡允桓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7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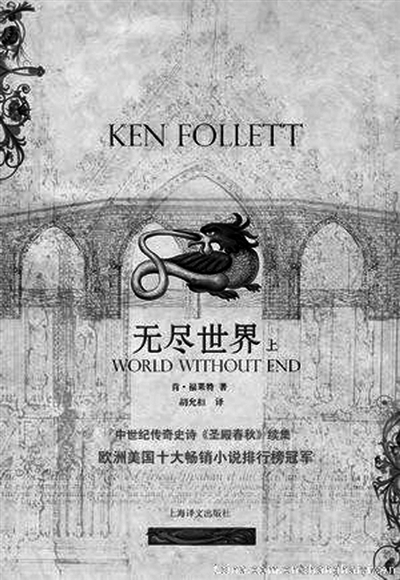
《无尽世界》
肯·福莱特著,胡允桓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2月版
肯·福莱特是畅销全球的惊悚小说家。1989年,福莱特出版《圣殿春秋》,这部以中世纪为背景的小说意外获得巨大成功,时隔十七年,他续写《圣殿春秋》传奇,续集《无尽世界》一出版又即登上《纽约时报》等多个畅销书排行榜。带着对那些中世纪故事的好奇,本报记者在伦敦对福莱特进行了专访。
艾柯的书让我想写中世纪题材
新京报:据说你决定写中世纪的故事和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有关系?
福莱特:出版人们一直说,最不受欢迎的、最没有人感兴趣的,就是中世纪题材的小说,但是艾柯出版的《玫瑰之名》,就是一本中世纪背景小说,却大获成功,证明了出版人们的看法是错的。尽管如此,但当我写《圣殿春秋》的时候,我的出版人还是非常担心书的销量,他依然认为大家还是不会对中世纪题材感兴趣。但是我认为,如果是一个好的故事,人们还是会喜欢的,这和是不是中世纪或者其他年代故事没有关系,真正重要的是故事本身。艾柯的成功,让出版这本书对我来说变得稍微容易了一点。
新京报:你喜欢艾柯的书吗?
福莱特:我不是很喜欢。《玫瑰之名》里有很多我喜欢的地方,但是中间有一部分特别冗长无趣,没有很多情绪的东西,是很多数字和密码,太抽象的东西,我不太喜欢,我是20或者25年前读的这本书,时间已经很长了。
去教堂让我的灵魂变得冷静
新京报:教堂建筑是你在《圣殿春秋》和《无尽世界》里反复提到的内容,怎么会对这个部分感兴趣?
福莱特:当我欣赏大教堂时最被深深震撼,当你站在任何一个大教堂面前,非常大,非常美,宏伟壮观。你问你自己:“为什么它在这里?”这并不像比如看到中国的宫殿的时候,你知道它的功能,谁住在那儿,但是大的教堂不是这样。既然没有人住,为什么要修这么大呢?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这是让人很产生兴趣的一个话题。所以我就开始寻找为什么他们会修这些教堂,以及他们是怎么修的,谁修的,是怎样的人修的。
新京报:在现在的英国好像并没有那么多人去教堂了。
福莱特:对,现在这个国家大概只有一半人说他们依然相信上帝,另外一半人则不,这些相信上帝的人也没有太多会去教堂。这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很多人去教堂,这个国家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依然很喜欢教堂,每个人都很喜欢,因为教堂本身很美,很平静,这和宗教已经不太相关了。对某些人来说确实教堂还有重要的宗教意义,但很多人热爱教堂,但是同时又不信仰上帝。我去教堂次数很多,但并不是为了祈祷,去教堂可以让我的灵魂变得冷静,可以舒缓我的情绪。
我会为读者修改情节
新京报:23年前,《圣殿春秋》出版时,美国很多媒体批评它,《纽约时报》说你用20世纪的语言讲了个12世纪的故事,你怎么看?
福莱特:中世纪和我们现在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他们说的英语是中古英语,要是我能说,我肯定会说的,但是我不能,所以我也不可能这样写一本书。那我就决定,写这本书和书中的对话都采用当代的英语。我认为读者会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情况。有的历史类型的小说,用的是一种奇怪的英语,所谓的一种方言,他们用的英语和莎士比亚的很像,人们觉得这是一种复古,但我不喜欢这样,我也不想这样做,因为看上去很做作,不自然。同时我的读者对我使用的方法感到很满意,有的时候,评论家会觉得太奇怪了,书里面的人物说的是现在的语言,但是读者们不介意啊,他们很快就适应了。
新京报:看过你的一个访问,你说你写的时候会考虑读者喜不喜欢,可你怎么知道读者喜不喜欢呢?
福莱特:其实我也不确定,但我本人就是个读者,我读自己作品也来来回回很多次,这也是我生命中最愉快的享受之一,所以我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也知道,当我不享受我的阅读经历时是怎样的,所有的事情都会非常糟糕。所以对读者的推测,大部分来自于我自己。这个问题我确实经常都在想,很多读者也不像我这样说这么多,他们只是享受他们阅读的乐趣。当我读书的时候,我会想为什么这么好,或者为什么不是很好呢,然后分析我的想法,当我写我自己的作品时,我也会借鉴我之前的想法。
新京报:那对你来说,读者是最重要的?
福莱特:是的,对我是这样。我喜欢大家在我的书还没出版的时候读我的书,如果有两个人说到同一处他们不喜欢,我就会修改那个部分。
新京报:真的?
福莱特:是啊,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可能是他的个人喜好,但是如果有两个人就不一样了,之后可能会有几百万的人读这个书,那就可能有过万的人不喜欢这个情节。
我不会选择生活在中世纪
新京报:中世纪时大家更暴力、更危险,但你却对那个时段如此感兴趣,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会选择生活在那个时代吗?
福莱特:绝不!我会恨那个时代的。中世纪是很有趣,对于写作是一个好年代,因为很危险,所以我们可以去大肆想象那种生活。比如那些谋杀,引诱,贪婪,有可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被杀了,我们读这些会发自内心觉得我们是多么幸运。老实说,我是很依赖舒适生活的,我喜欢美食、我也不喜欢冷,中世纪的房子都很冷吧,我喜欢暖暖和和的,穿着我的羊绒毛衣,诸如此类。而且中世纪的每个人肯定都会很臭,因为他们也不常洗澡,如果我们回到中世纪,会说:“这是什么味儿,难道是人味儿吗?”所以我会恨中世纪的。
新京报:有人说,你的书很好看,就是性爱描写太多了。
福莱特:我很喜欢写关于性的东西,我的大部分书都有爱情故事,有爱情故事就会有问题,总会发生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种的事情。所有的爱情故事都会有矛盾,不一定是和这个一样的,有可能其中一个结婚了,或者其中一个是黑人、另一个是白人,这些都是问题,爱情故事总会有这些问题。一本几百页的书,两个人相爱了,他们因为某些问题而不能在一起,读者就会觉得:“哦,天哪,太悲哀了。”到最后,他们可以在一起了,我认为读者是想看到他们在一起的,而且是很开心的,这也是性所要表达的。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做爱做的事,读者读的时候也会很高兴。
新京报:人们会说你是个畅销书作家,那你是否认为文学性在你的书里是重要的?
福莱特:我肯定是个畅销书作家。至于文学性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是我希望我的书能够让所有人喜欢。文学只是书写的一种,对我来说,故事是重要的事情,我首要的任务还是讲故事。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