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最后的纪念》 阎连科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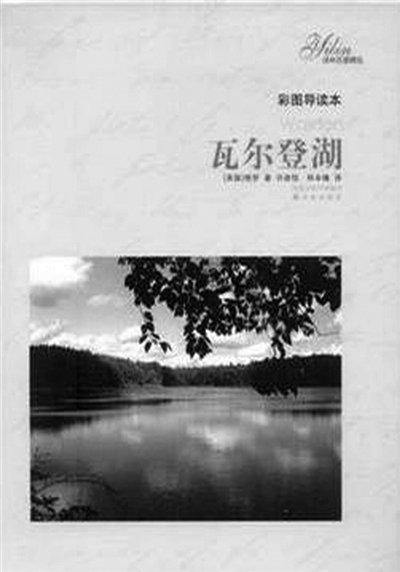
《瓦尔登湖》 梭罗著 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
【对话】
阎连科 河南嵩县人。代表作有《风雅颂》、《四书》、《我与父辈》等。2011年11月30日,阎连科在微博发出“一封告急信”,讲述自己所在小区当天开始正式被强拆。这就是新书里所讲述的711号园。
711号园是个世外桃源
新京报:看你的新书里写到,当你用你的试验方式证明了植物有感情和语言后,决定写一本植物的纪实文学?
阎连科:其实很早时候就想写,我对《瓦尔登湖》很敬仰,这是对《瓦尔登湖》致敬的一本书。我那时觉得已经到了可以写的时机,把手头要写的写完,就决定静心写这本。我很怀念当时711号园的那个环境,树木、花草、湖水……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新京报:你怎么比较这本书和《瓦尔登湖》呢?有向它学习的地方吗?
阎连科:后面写湖水的那部分已经向《瓦尔登湖》学习了,我也不相信我就比人家写得好,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过了这么多年,它还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我觉得也不要去比较这两本书,那是小巫见大巫,那样我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没有意义。具体的还需要读者来判断。
新京报:当时是什么机缘找到711号园的?
阎连科:有一个朋友和那里的开发商是朋友,起初他跟我说过几次,我说我坚决不去。后来有一天我和这个开发商在一个桌吃饭,他说让我去看一下。结果我发现真是我朋友说的那样,那么一大片地方,原生态都留下来了。开发商也跟我说了手续的问题,说得乱糟糟的,那时小区还没完成,说是搞完以后发房产证。我开始决定买下来,开发商也很够朋友的,说没钱可以晚交,别人都是交清了。
种菜是真正的富贵方式
新京报:你认为农具成为工艺品被摆在都市的商店,是人类文明的异化?
阎连科:这么大的城市,买农具却这么困难,我觉得是对祖先生活的遗忘。可能所有的孩子每天吃馒头,但是不到乡村去,都不知道小麦的样子,韭菜和小麦分不清,大学生真是这种情况,他们从城市到城市、从宾馆到宾馆。
新京报:你觉得这种状态是一种遗憾吗?
阎连科:一个超大的城市可能三五个月不见到一棵树木、花草。草和蔬菜需要到商场去看。这样的缺失从表面看是断了大自然的天然联系,实际上深层的是却失去了对一个世界的关心,我这样说可能别人觉得我有点酸溜溜的。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就是这样,除了我必须的之外,对其他的没有兴趣,只关心自己的前景。我写这样一本书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反馈,我把自己当成重度精神病患者,拥有这么多,喃喃自语,歌唱别人已经失去的东西。我自己也妒忌我自己,711号园去过的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失去也是必然的。
新京报:所以你说种菜是真正的富贵方式。
阎连科:今天谈到种菜、种花、种草是绝对奢侈的生活,有一个空间做这些事,确实很富贵。我对在711号园的那段生活是一种无法说的怀念,每天早上起床跑一跑兜两圈。之后给植物除草、浇水,那里是沙土,水两三天必须浇一次。那段时间不太敢让朋友去那里,害怕别人知道,有种偷来的感觉。那是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
神经质样地爱植物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你精心照料的芹菜反而不如随意种下的丝瓜长得好。
阎连科:真正让我最震撼的是另一件事,就是那个我种了两个月的葫芦只有灯泡那么大,之后我和朋友去了承德,两天两夜后,18个葫芦全部比人头大,我傻掉了!这个事情太神秘了,我觉得我对它们完全不了解。
之后我觉得就是应该让植物顺其自然地生长。我本来打算下一年再种葫芦好好研究一下,结果房子却消失了。
新京报:所以你后来也都不给树木修剪枝叶了。
阎连科:我家树最多的,恨不得种下各种花树,家里大约有50棵左右的树,乱糟糟一片,很多地方人都走不进去。有些荆类的植物就在空中地上随意长。
我那段时间有点神经质,离开那个地方也和大家一样说说笑笑,回去就是另一种状态。
新京报:但是这种神经质让你做了不少有趣的试验,比如“凡有情的人,都为它浇水吧!”放在黄花草旁的牌子,结果发现给它浇水的人太多了,它都要涝了。
阎连科:这样的东西,确实在那儿。挂了差不多一年,第二年后来没有挂。
新京报:还有你认为槐树和楝树有一场姐弟恋,你跑去跟其他邻居说,却没有人接你的这个话茬?
阎连科:今天离开解释那些举动,我觉得除了神经质没别的可以解释,别人会觉得我有点神经质。
新京报:但是到底是你有神经质,还是其他人集体不关心身边的植物花草呢?
阎连科:人都是从众的,巨大的城市里大家都对植物失去兴趣,结果让另一个感兴趣的人变得神经质。所有人如果都住在乡村,却有一个人不爱惜庄稼,那这个人才是异类。我写这本书就是从写作上,要背叛从众,是某种抵抗。
我想如果这个话题是另外一个人写,大家会觉得正常,但是我来写,可能大家会觉得和我之前写作有点儿相差甚远。
写作永远不能离开现实
新京报:虽然你在书里说自己并不那么关心社会,但是在这本书里随处可见你对社会的反思。
阎连科:这些都是我的随笔感想,还被编辑删了一部分。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大自然妥协,世界的主人翁是大自然,但是现在这个伦理关系弄颠倒了。我们变成了世界的主人,把主仆关系颠倒了。
新京报:在园子里的生活其实也影响到了你的写作,比如你会根据写作时听到的声音改变你文字的温度。除了这个部分,你觉得还影响到你写作的其他部分吗?
阎连科:现在看来,这本不算厚的书,实现了我希望写一本植物就是主人公的书。这本书的写作也伴随着这个园子的消失,我也很坚定一件事,就是我的写作永远不能离开现实,我说的是今天的现实不是昨天的现实。
我以前有的书还是写的昨天的现实,但是这个书很彻底。我之前有三四个故事,我很摇摆不知道接下来先写哪个,但是现在我很清楚了,下一本书就是要说今天的现实。认识昨天比认识今天要容易,昨天被过滤过,被记忆淘汰过,但今天很庞杂,要让今天的现实不能被后面的人忘记。无论怎样,我要写当下,这本书让我清楚了这一点。
新京报:书的结尾园子被拆掉了,你说觉得就像蚂蚁的行走路线,一只脚一阵风就被改变。
阎连科:确实这样觉得,心情很糟糕。事实上,每个人命运都是如此,每个人的命运几乎自己都不能掌握,或者说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非常少,更多的人是被别人掌握。吃什么不吃什么住在哪儿都由别人决定。这样想,也会变得豁达起来,更坦荡。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