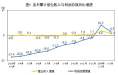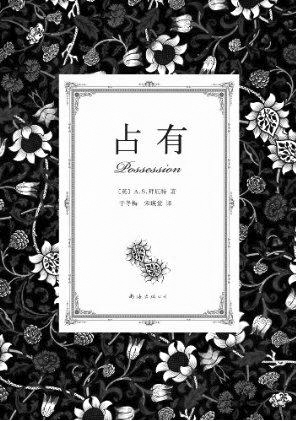
《占有》 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9月新版,拜厄特最早翻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

《诸神的黄昏》 重庆出版社2012年8月版,拜厄特参与“重述神话”项目写作的最新作品。

《天使与昆虫》 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9月出版,拜厄特早期小说之一,第一次引进出版。

A.S.拜厄特(1936- ),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先后毕业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1972年起在伦敦大学教授英语文学。1983年辞去教职专事写作,同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1990年,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1999年,获颁大英帝国女爵士勋章。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天使与昆虫》、《传记作家的故事》、《儿童书》等,以及《蜜糖》、《马蒂斯故事》等多部短篇小说集。拜厄特写作生涯中获奖无数,其最著名的作品《占有》(Possession)以侦探小说的方式钩沉出两位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之间隐秘而动人的爱情故事。《占有》获得了1990年的布克奖,也为拜厄特迎得了巨大的声誉。2008年拜厄特被《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来英国五十名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新京报摄影 孙纯霞
布克奖得主A.S.拜厄特最近来了中国,同行的还有她的三本书,《占有》、《天使与昆虫》、《诸神的黄昏》。一周之内,拜厄特在中国进行了两场对话,在北京是和学者陆建德、止庵,在上海是和王安忆,陆建德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王安忆是重要的作家,今年刚刚获得红楼梦奖。从级别而言,这样的对话组合已经足够有吸引力,但从内容而言,两场对话听下来,拜厄特的形象,依然是陌生的。这一点大概很像拜厄特的偶像乔治·艾略特,拜厄特对本报记者说,“我喜欢乔治·艾略特,她写得很好,热爱思考,而且她长得很丑。她是我的偶像。”今年英国人把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列为世界上必读的100本小说第一名,但在我们这儿,没什么人读乔治·艾略特。
如何走近并且理解一个作家,特别是这个作家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占据重要位置却又不为我们所熟知的时候?答案或许只能是作品。你必须去读作家的书,就像拜厄特本人所言,作品永远比作家重要。所以,我们的访谈,就从她获得布克奖的作品《占有》开始……
关于《占有》 生活迷失在另一个人身上
不知什么原因,如果你想写一本关于学院的小说,你必须把它写成一个喜剧。你不能让学院里的任何人真正地关心文学,他们必须都是愚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想写一本学院小说,其中文学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
新京报:我想这是作家访谈普遍会问到的一个问题——你写《占有》的动机是什么?
拜厄特:我想有两个动机,一大一小。小的动机就是“占有”这个词。我当时在大英图书馆研究诗人柯勒律治,有一个从加拿大来的非常有名的柯勒律治学者买了他的日记本。在图书馆的流通处,她在那里看一些书目,我看着她,想到了鬼魂附体、巫术这回事。我想是她附在了柯勒律治身上吗,还是柯勒律治附在了她身上,因为她的所有思想都是关于他的。我对这种一个人的生活迷失在另一个人身上的心理状态很感兴趣。这是一个起源。另外一个是,我当时在伦敦的一所大学教授英语课程,我觉得学者对于作家都是非常有占有欲的,而我是把我自己看成一个作家而不是学者,我对其中的张力很感兴趣。其实还有第三个原因。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英国学院小说的传统,像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戴维·洛奇等人写的小说,不知什么原因,如果你想写一本关于学院的小说,你必须把它写成一个喜剧。你不能让学院里的任何人真正地关心文学,他们必须都是愚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想写一本学院小说,其中文学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文学对他们来说高于一切。这些就是让我去写这本小说的原因。我当时想要把它写成一本法国式的实验小说,你会读到学院生活,但不会读到诗歌,诗歌会掩藏在学术研究的表面之下。然后有一天,我读到了翁贝托·艾柯的小说。我对自己说,不,不要用那种精致的法式写法,而是要用那种非常喜剧化的、侦探小说式的写法,因为那样会让它更有趣。然后我开始写各种侦探小说的戏仿,它进展得非常缓慢;其实我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的十二三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是因为我有四个孩子,此外还要教书,才一直没有写。
新京报:是不是也因为它是一本很难写的书?
拜厄特:更主要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思考它。我的所有书都是很难写的,而且我喜欢花很长时间去思考,我喜欢思考的过程。
新京报:这本书的标题Possession可以有不同的涵义。据我所知,在英语中,它至少有两个涵义:一是“着魔”(bewitched),一是“占有”。而中文只捕捉到了“占有”这一层意义。
拜厄特:当然那也是其中的一层涵义,人们去买下其他人的书籍和文章。其实在英语中还有第三层涵义,在《圣经》中,possession 的意思是“性”,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性占有。我是在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我想这其中可以有爱人之间的占有,可以有两个死去的爱人之间的占有,还有两个活着的爱人“占有”那两个死去的爱人。因为这其中有三层涵义,所以译者基本不可能把这三层涵义都表达出来。
新京报:所以他们必须做一个选择。
拜厄特:是的。
关于“爱” 他们小心经营着爱,但不再谈论
我的三个女儿都是很小心地经营爱情而没有用“爱”这个字眼。我想这之后的一代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之间有了分化,人们在报纸上看到名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金钱和浪漫的爱情,他们很糟糕。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关于名人的文化。我有一个外孙女,在她非常小的时候我们问她你以后要干什么,她说我要去纽约当一个名人。
新京报:在《占有》中有这样一段话,你说罗兰·米歇尔和莫德·贝利“出生在一个不信任爱情的时代与文化氛围中”,“恋爱、浪漫爱情、完全浪漫,却反过来产生了一套性爱语言、语言学情欲、分析、解剖、解构、暴露”。以至于罗兰和莫德之间的感情进展缓慢,似有若无,疑虑重重。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在不信任爱情的时代与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是你为什么去写一本关于激烈的、维多利亚式的浪漫爱情小说的原因吗?
拜厄特:是的,我想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那种爱情几乎是消失了。我想当许多事情是被禁止的时候,爱是可能的。当你去爱一个不是你的丈夫或妻子的人是错误的之时。爱变得可能,因为它是有趣的。
经常,有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开学一星期就和同学住在了一起,开始居家生活,他们没有和其他人在一起的经验。我有点可怜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浪漫的爱情。我的大女儿——她比那些学生稍微年长一些——对我说,我们从不用“爱”这个字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我想这非常好,她就是在大学里碰到了她后来的丈夫,到现在他们的婚姻都很幸福。
新京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会不会听起来有点愚蠢:我们这种不再轻易言爱的文化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我们不再说爱这个字眼了呢?
拜厄特:再一次地,我会想到我的女儿,现在她已经50岁了,但在我写《占有》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学生。我想她的情形实际上是非常好的,我想当她拒绝“爱”这个字眼的时候,她是在拒绝许多关于爱的蠢话,那些想像出来的东西,那种强调“你必须是身在爱情中的要不然你就不是一个人”的胡话。实际上你可以做各种事情并且是“一个人”,当然如果你确实是在爱情中,那很好。我想她那一代人很小心地处理了爱情,正是因为她们没有用“爱”这个字。她很小心地挑选丈夫,有了三个出色的孩子,而且他们当然是相爱的。很有意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丈夫都拒绝结婚,因为他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我们会离婚,但他们没有离婚。事实上,我的三个女儿都是很小心地经营爱情而没有用“爱”这个字眼。我想这之后的一代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之间有了分化,人们在报纸上看到名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金钱和浪漫的爱情,他们很糟糕。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关于名人的文化。我有一个外孙女,在她非常小的时候我们问她你以后要干什么,她说我要去纽约当一个名人。然后我们问,你要“做”什么呢?她说,我要“做一个名人”。她根本没有想到你当一个名人也是要“做”点什么的。
新京报:我想人们还是会想去写爱情小说。我想到了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和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它们都是很好的爱情小说,但作者都在故事中设立了战争的背景,也就是说你必须在其中设置障碍。
拜厄特:你说得很对,必须要有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爱情小说中的人物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因为那个时代有障碍。我都忘了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想男性作家比女性作家更多地考虑爱这个主题,他们还是会写爱情小说。这些男性小说家对爱情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想不起有哪一个好的女性小说家对爱不是持有怀疑或是嘲讽的态度的。当然,也有可能她们的策略是“虽然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但最好不要去提它”。
十九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权主义者曾说过,“生活一定不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学习怎样做帽子”——那个时候她们总是在一起一边给帽子插花一边讨论爱情——于是她拒绝了这种生活,开始思考。
关于女权 英国有女性写作的传统
在英国文学史上,好的女性作家一直都是和男性作家一样多的,我们没有美国和法国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学院从他们那里进口了女性主义的理论,或者说它们的理论主张。然后,我们开始有了一代学者,专门去寻找那种“弱势女性”。对这一点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强烈。
新京报:我想你可以算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你似乎对于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非常怀疑,在《占有》和其他书中,你常常对女性主义研究者大加嘲讽。
拜厄特:是的,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我是一个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者。我对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是非常怀疑的。虽然其中有些研究是很好的,但我不满的是,在她们开始去研究一个问题之前其实就已经找到答案了,因为你必须找到一个女性主义的“信息”。这就意味着你根本不用去读书,而我认为你必须先去读书再去看它说了什么,但女性主义者只是去书中摘取信息,在不同的选项上打勾。
我想说的另一点是,在美国和法国,女性写作的传统是要比男性写作弱的。美国文学是极端地男性主导的,虽然美国也有像艾米莉·狄金森这样伟大的女诗人,但如果你去看美国小说,从整体上看,所有伟大的美国小说几乎都是关于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的,以及一个偶然碰到的女性。在法国,作家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等级,总的来说,最好的作家中没有女性。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是从美国和法国起源的,它的主旨是我们要战斗,人们不承认伟大的女性作家,我们必须为她们伸张权益。但事实上,在英国文学史上,好的女性作家一直都是和男性作家一样多的,我们没有美国和法国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学院从他们那里进口了女性主义的理论,或者说它们的理论主张。然后,我们开始有了一代学者,专门去寻找那种“弱势女性”。对这一点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强烈。在我之前的那一代女性作家可能是比男性作家更强的,而且人们都知道她们要更好。我们有艾丽丝·默多克、缪丽尔·斯帕克、多丽丝·莱辛,以及后来才开始写作的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在男性那边我们有威廉·戈尔丁、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金斯利·艾米斯、安东尼·伯吉斯。如果你去看在有了女性主义之前的英国报纸,你会发现,评论家——不管男评论家还是女评论家——都会说:“这是一位重要的小说家,她的名字叫艾丽丝·默多克”,性别不是一个问题。然后,大学里的评论家将它制造成了一个问题,接着发生了什么呢?女性作家开始写那种关于女性的小说,写得非常小心,格局很小,着眼于爱情,对其他事情几乎一概不关心。我认为那真的是一个悲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安吉拉·卡特。安吉拉是不一样的。她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但是以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她重写了许多童话故事,在她的版本中女性是非常强大的。但很不幸她在一个错误的年纪去世了,在她只有52岁的时候。在她之后就没有人那样做过。当然,现在我们有了新一代的女性小说家,她们也是女性主义者,但是一种不同的女性主义者,她们不觉得自己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反她们非常的有趣。像阿莉·史密斯这样的作家,她写的很多故事都像是寓言,她的故事十分难以形容,但写得极其奇妙。比如说,她有一个故事,是写一个女人走到街上爱上了一棵树,然后她把那棵树带回家种到了地窖里,她爱它,她有一个情人,他们两个都很爱它。她就可以这么写。她写的完全不是那种英国的社会小说,不像上一代的女作家一样关注女性和家庭,写一些悲惨的家庭主妇怎样被困在家庭生活陷阱中的小说。
新京报:感觉她找到了小说的新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新的看世界的方式。
拜厄特:是的,我想是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方式。你去讲不真实的故事,以改变人们看待真实世界的方式。
新京报:听起来有点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我热爱他的所有小说,特别是《看不见的城市》。
拜厄特:是的!我热爱那本书。我们四月份的时候去了威尼斯,那几个星期感觉就像在“看不见的城市”中一样。你读过他的《意大利童话》吗?我觉得那本书也非常棒!
新京报:是的。我想起了卡尔维诺,因为他的书都很怪,但却不是和真实的世界脱节的,你在其中几乎可以找到人类全部的情感和经验。
拜厄特:是的,他的故事不只是奇幻故事,你不会想用奇幻这个词。我想阿莉·史密斯从卡尔维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很好的东西。
新京报:回到刚刚女性主义的话题。在我看来,女性主义学者似乎对性的问题(sexuality)过份着迷。比如《占有》中就有一个女学者将一切都从性的角度解读。我非常不理解这一点。
拜厄特:你是指性取向,比如同性恋或是异性恋,还是笼统的性问题。
新京报:笼统来说。
拜厄特:我想我们身处一个对性过分着迷的社会,我不喜欢这一点。如果你去看英国报纸,你会发现,每份报纸里面会有六到八篇谈性的文章,以及无数的穿着暴露的女性的照片。我们有那种专门教人提高性技巧的专栏——我觉得在中国应该没有这个——我们有这种专栏。它们真的是非常恶劣。这还是在非常值得尊敬的报纸,比如《卫报》里面,一周三次你会读到这样的文章。可能它们也会帮到很多人,但与此同时,它会让这个社会显得没那么严肃……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够复杂。
关于批评 在不懂一件事情的时候去写评论
如果你不保持大量阅读,你的风格会永远一成不变。不读书的那些人彼此写得是很像的。只有一点,尤其是对于那些学习英语文学的人来说,你有可能读得太多以至于永远都不可能开始写作。
新京报:你的博士导师确实曾对你说“所有从一流学校毕业的女生都希望自己能够写一本好小说,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吗?
拜厄特:她确实说过这句话。她也说过“所有学者都必须生活得像修女一样”,我要结婚的时候她对我非常生气。我当时想,这很不好。然后她很好,对我说她不能用法语读普鲁斯特,我想,我可以读,于是我就去书店买下了普鲁斯特的所有书,我开始读普鲁斯特,并变成了一个小说家,停止了当一名学者。我想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帮助了我。我的这位老师是一个十七世纪(文学)的学者,在那个年代非常有名;我有一个好朋友在荷兰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他对我说她做的所有研究都是错的。她的研究是错的,她也不应该刺激我。
新京报:很显然,写作对你来说比学术研究更重要。但你在英语系的训练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
拜厄特:是的。我只是单纯地认为,阅读对写作有很大帮助。如果你去参加年轻作家的聚会或是文学节,你会发现,有些天真的作家会说我不读太多书,因为那会损害我的风格。对此我非常生气。我说,如果你不保持大量阅读,你的风格会永远一成不变。不读书的那些人彼此写得是很像的。只有一点,尤其是对于那些学习英语文学的人来说,你有可能读得太多以至于永远都不可能开始写作。我想我是自己闯出了一条路,因为我需要阅读,我一直不停地读,直到我可以写作。但我不建议所有人都这么做。我们这一代在剑桥的学生当年是很认真地学习文学,我们相信它很重要,将会改变世界。我想我是其中唯一一个变成小说家的。我的同学有几个去了大学,更多人变成了很好的中学老师,教书取代了对文学的信仰。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对写作确实并没有什么帮助。
新京报:在《占有》的结尾,罗兰突然发现,“他准备好做一名诗人”了。我觉得这是全书中极具超越性的一个时刻。看起来有点像你的自身经历。
拜厄特:嗯……《占有》的整个主旨是写作比批评更重要,同时,我认为,写作要比写作者更重要。我认为诗歌要比诗人更重要。罗兰是出于对诗歌的爱才变成一个诗歌评论者的,当他发现他可以成为一个诗人的时候,那确实是一个超越性的时刻。我是在学院里面写这本小说的,总体来说,那些教授认为他们可以评判诗人、评判诗歌,他们认为他们说的是更重要的。这是我为什么要去写那些诗的原因,诗歌必须在场,因为诗歌比评论家更重要。这很难,但我必须这么做。
新京报:你写的很好。
拜厄特:我的经历是很像书中罗兰的经历,我想这是为什么我可以写出那个超越性的时刻。我的编辑是一个诗人,我对他说,我会在书中写一些不知名的诗人,然后他说,你要自己去写那些诗。我从来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过。我确实当天晚上就回家写了维多利亚式的诗歌。我不会写英语现代诗,我只会写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不过在我的下一本书中,会有一战时期风格的诗歌。很有趣,我一直被逼着去写诗,我觉得我应该为这本书去写一些超现实主义诗歌。
新京报:很有意思,听起来好像如果你想去写,你就可以写。
拜厄特:这叫“腹语术”。
新京报:你也写过很多的批评文章。你曾经对一个《巴黎评论》的采访者说你写的评论是“作家评论”,那么你怎样定义“作家评论”?你怎么比较你写的评论和一些其他作家的评论,比如说J.M.库切,约翰·厄普代克,或者米兰·昆德拉?
拜厄特:我想我和他们的评论都可以归为“作家评论”。嗯……我通常会在不懂一件事情的时候去写评论。我写评论是为了去理解。比如我去写关于艾丽丝·默多克的评论,是因为我不懂她的小说,所以我开始去写,直到我确实弄懂了为止。有一些人的工作是专业为报纸写评论,他们行使权力,创造品位,我认为这两件事情都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不想这么做。如果有人给我寄了一本我不喜欢的书让我写评论,我不会写,我会把书退回去。当然我也会去评论一些年轻作者的书,当我看到一些非常好的东西并且希望把它们介绍给读者的时候。但最主要的,我的评论是写我不懂的东西,这样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可以学到东西,有所收获。
采写 新京报记者 吴永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