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很多人闻游戏色变。我一直属于玩游戏的亚文化群体,我们被看作是失败者、孤独者,是心理有问题、逃避现实生活、面色苍白、身体不健康的肥宅。但是,其实我们能开飞机,我们还能经营一个国家,甚至能拯救人类。”严锋的话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引发阵阵笑声和掌声。
游戏在人类的文化和生活中越来越重要,渐渐成为了90后及00后的主流文化,从去年电竞俱乐部IG夺冠刷屏就可见一斑。随着VR、AR等技术的发展,本是虚拟的游戏变得越来越真实,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历史的重现也重叠在一起,这一切对90后及后代的认知与价值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电竞俱乐部IG获得S8世界冠军
对于资深玩家严锋来说,游戏不仅是游戏,它包罗万象,更是一个有机的、完整的世界。游戏中蕴含着乌托邦精神,可以弥补人生缺陷,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庸。作为国内第一个研究游戏与文化的学者,严锋说,他对游戏“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思想界”感到欣喜。
游戏到底有什么文化魅力和思想内涵呢?4月25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出席“第五届思勉人文思想节”,在“游戏:90后文化与人类乌托邦世界”的讲座上,从“游戏与我”的母题出发,结合他个人的游戏史以及黑格尔、瓦格纳、托尔斯泰等名家的理论,阐释了游戏与文化的关系。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科学杂志《新发现》主编严锋
《荒野大镖客》实现了人的终极欲望
严锋首先梳理了自己的游戏史,通过个人的体验,大致介绍了电子游戏的发展脉络。他从1987年开始玩任天堂游戏,玩过《银河飞将》《沙丘》《毁灭战士》《荒野大镖客》等等。
《银河飞将》的主线是拯救地球,其第三代游戏开交互性先河,而交互正在成为游戏文化的最重要特征。它的交互性体现在,游戏会根据玩家的格斗、行为等设置之后的情节。《毁灭战士》是FPS(First-person shooting game),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当下热门的“吃鸡”游戏也是从此发展而来。
《沙丘》则同时是划时代的游戏和科幻小说,其第二代开RTS(Real-Time Strategy Game,即时战略游戏)先河,包含了互动性、策略、建造世界等元素,在游戏里可以经营战场乃至一个国家。这种游戏可以模拟现实,如模拟城市、模拟经营、模拟大学等等,一切都可以模拟,它网罗了社会历史、文化、知识、思维、决策、博弈等等。90年代后期RTS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红警》《魔兽世界》等游戏。

游戏《沙丘》
《荒野大镖客》是让严锋最感到震撼的游戏,这个游戏用精细的建模构建了栩栩如生的有机世界,包含了策略、动作、冒险、解谜等多种元素,另一个游戏GTA(Grand Theft Auto,侠盗飞车)也类似地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些游戏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梦想——掌控世界,这是人最大的欲望。严锋说,以前皇帝才能主宰天下,但现在任意一个《三国》的游戏玩家就可以统一中国。

游戏《荒野大镖客》
严锋现在非常喜欢玩模拟飞行的游戏,他喜欢吃完晚饭“飞去”瑞士、大峡谷、朝鲜等地方。在游戏里,玩家可以抓取谷歌卫星地图,制作自己的3D地图。“我喜欢开着飞机去我走过的路、住过的地方,这也是一种泪流满面的体验。”严锋认为游戏开启了很多可能性,带给他宽广的思考空间,让人足不出户就可以游遍天下。
在游戏之前:音乐、文学与电影
严锋认为虽然黑格尔的哲学大厦已经轰然倒塌,但他的思路仍然可以带给我们许多启发。黑格尔将精神与历史的发展过程相联系,更是以超前的眼光,从媒介去理解艺术和艺术史。
黑格尔梳理了媒介/艺术的发展历程,从象征型艺术(建筑)到古典型艺术(雕塑),再到浪漫型艺术(绘画、音乐、诗/文学)。每种艺术都是一种精神形式,黑格尔根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划分了这些艺术的层次:建筑是物质压倒精神的形式,雕塑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统一,绘画的物质性进一步被形式所压倒,而音乐连形体也没有了,比音乐更高级的形式是诗/文学。黑格尔认为诗已经完全冲破形式和物质,诗是艺术的终结形式。
黑格尔在《美学》中写道:“尽管诗用语言的表达方式,诗却最不受其他各门艺术所必受的特殊材料所带来的局限与约束,所以诗具有最广泛的可能去尽量运用各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却不带任何一门其他艺术的片面性”。钱锺书在《读<拉奥孔>》中也表达了诗无所不能的观点。
文学获得最高艺术的地位是因为它不受形象的局限,严锋举了《三体》电影难产的例子,来说明电影媒介的局限性,《三体》小说中智子的展开等情节很难视觉化,而文学能够展示“不可视”的“可视性”。
黑格尔的思想在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引起回响,浪漫主义追求一种无所不包、吞吐天地的艺术。《尼贝龙根的指环》的作者、音乐家瓦格纳就提出了“总体艺术”的思想,他认为以往的艺术因对应单一感官而将人局限化,应该将人的各个感官打通,因此他创造了“乐剧”的艺术形式,包含了音乐、诗歌、绘画(舞美)、舞蹈、建筑和哲学,追求视觉和特效的最大化。严锋指出,这种视觉特效其实就相当于今天的IMAX效果。
瓦格纳知道艺术应走向艺术纵合,但乐剧没有实现他的理想,而今天的技术实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诞生了。托尔斯泰在当时就看到了电影对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他认为从此以后一切将改变,电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革命,会对旧有的文学进行直接打击,文学必须适应充满光影的冰冷荧幕,新形式的写作不可避免。如今,托尔斯泰的预言似乎已经成为现实,有人笑称:“中国文学界沦为替张艺谋打工”,而《流浪地球》的火爆也是因为它的电影化,是电影让科幻文学走进了千家万户。
交互性——我们时代的关键词
然而艺术史永远在流转,严锋已经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新气息,那就是交互性。“电影的好日子也要到头了”,严锋说。在这个众口难调、众声喧哗的年代,人的主体性空前活跃,原来的单线程艺术不再合时宜,交互小说、交互电影、交互戏剧,交互电视、交互文化等交互艺术才能满足人们对多种生活、多种世界的需求。
浸入式戏剧《不眠之夜》(Sleep No More)的巨大成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不眠之夜》是英国Punchdrunk基于莎士比亚经典戏剧《麦克白》的一次重新解构,打破了表演区和观众席之间的藩篱,观众可以自由地行走、探索和体验。自《不眠之夜》2016年来到中国,在上海麦金侬酒店开演以来,就一直维持着高热度、高人气和高口碑。

观众戴着白色面具观看《不眠之夜》
“讲到交互性,电影就哭了。”严锋说,电影很难实现高度的交互性,因为它的线性非常强,而交互性的特点就是非线性,即可以在多线中自由穿梭。
其实交互性的历史非常久远,它一直潜在或显在于人类的各种艺术中,比如《雪山飞狐》就是一种交互文学,它的开放性结尾“胡斐到底能不能平安归来和她相会,他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将情节走向的选择权交给了读者。小说的交互性还可以由各种“续”来实现,如果《红楼梦》把林妹妹写死了,别人还可以写续、写补,甚至做批注和评点,把林妹妹写活,写不同的情节和结局,让读者自由选择。“批注发展到今天就是B站的弹幕,而B站用户就是今天的脂砚斋。”严锋总结道。
在一切当中看到游戏,在游戏当中看到一切
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说:“游戏是这样一种行为,它在时空的界限之内,以某种可见的秩序,按照自由接受的规则进行,并且在必需品或物质实用的范围之外,游戏的基调是狂喜与热情。”因此他把一切看作游戏,例如法庭也是一种游戏,它满足特定的空间和人物、需要遵循的规则、有目标以及能分出胜负、有奖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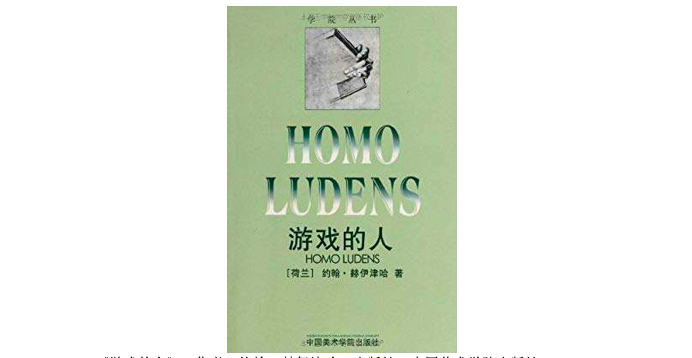
《游戏的人》,作者:约翰·赫伊津哈,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10月
严锋认为这种思路很夸张但很有意思,“如果它说的是实情,那么我们的文化是不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是不是有利的?我们是不是要加入并促进这个进程?”他提出了一系列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对游戏作出评价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游戏。游戏的要素主要包括目标、规则、反馈系统和自愿参与等。所有游戏都有目标,即使是《俄罗斯方块》,它和大部分游戏一样,目标就是“活着”。而反馈系统是最迷人也是最可怕的,玩家可以马上看到行动产生的结果,产生心流,即分泌多巴胺和肾上腺素,这是游戏吸引人的最重要原因。最后,玩游戏就是自愿参与,尝试克服种种不必要的障碍,在游戏中我们自愿受苦,那么如果将游戏原理移植到工作中,我们会不会自愿996呢?

游戏《俄罗斯方块》
游戏的好玩之处就在于其带给我们的成功感、成长感、掌控感、角色感、沉浸感和安全的挑战性。黑格尔认为战争和暴力是人类进步的根源,即人生要经受挑战才能磨练人的意志,而游戏就可以安全地磨练人的意志。严锋总结了游戏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交互性、沉浸感、创造力、自由度、社会化和综合性,综合性的例子是游戏里虚拟的房子可以赚到真的钱。
至此,严锋已经得出结论——游戏是艺术,但他进一步向观众问道:“我们能创造一个如《红楼梦》那样伟大的游戏吗?游戏可以成为经典、伟大的艺术吗?”这就涉及评判标准的问题,严锋给出了一些可以衡量的指标,如精神性、形象性、情感性、思想性和风格性,他认为即便游戏无法成为《红楼梦》,也可以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比如《底特律:变人》将人对成为他者的渴望实现了,我们可以不受物质的局限,过另一种生活。
另外,简纳特·穆雷在《俄罗斯方块》中也看到了高度的艺术性,他在《全息甲板上的哈姆雷特》中把一切游戏看作象征性戏剧,将《俄罗斯方块》游戏的不停息比作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过度辛劳的生活的完美象征,《俄罗斯方块》与生活一样,有永无止息的任务,需要我们高度集中注意力,把过度拥挤的日程清理掉一些,以腾出空间迎接下一波问题的袭来。

《全息甲板上的哈姆雷特》,作者:简纳特·穆雷,出版社: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8年08月
走向VR:艺术与游戏的未来
严锋指出,VR是游戏的下一个阶段,也是一个很可怕的阶段。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中提出了拟像三阶段,即仿造(前现代)、生产(现代)和仿真(后现代),而VR将带我们来到仿真的阶段。仿真是从DNA生命的复制层面、从物理规律去模拟的惊人世界,在仿真时代,我们甚至不知道符号的本体是什么,不知道模拟的对象是什么。

VR游戏
VR将提升维度,从2D到3D。其实如今的3D是假3D,因为是在2D上呈现的,而VR是直接走进去。《三体》第一部就是以VR游戏引入的,但刘慈欣是反VR派,他认为这会造成人类灭亡,人类沉浸在VR游戏里,就不会去探索太空了。在强VR的世界里,人们完全活在虚拟世界里,实现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可是完全精神化之后,人还是人吗?严锋说,这时人就变成了神,因为想变成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的虚拟世界和“黑客帝国”正在形成中,有诱人的地方,也有危险,我们都需要了解和思考。
艺术的未来也和游戏息息相关,康德和席勒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人也起源于游戏,人脱离野蛮的状态就是超越实用的功利而追求自由的表达。艺术的下一个阶段会是艺术2.0,即游戏2.0与各种艺术结合的泛艺术游戏,而艺术2.0的最大载体会是VR。严锋认为,最后会有一种游戏和艺术的融合,即艺术和游戏都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时间、另一个自我和另一种生活,艺术和游戏通过探索可能的世界,让我们更好地协调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作者: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实习生 李颖
编辑:徐悦东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