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摘自《辛格自选集》前言。
作者 | 陆建德
美国犹太裔意第绪语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04—1991)出生于华沙附近小镇莱翁钦,四岁时随家迁往华沙,后来又跟外祖父在卢布林省的比尔戈雷住过几年。波兰1918年年底恢复独立之前,这些地方都由沙俄帝国管辖。辛格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拉比,他自己虽受过传统的犹太教训练,却选择了与祖上不同的世俗生活,很早就使用意第绪语创作,心目中的受众是欧洲犹太读者。辛格1935年离开波兰移民美国后,这条独特的文学之路从未中断。在他小说家的生涯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波兰犹太社区的风土人情始终是他创作的动力和灵感。

辛格照片
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的辛格
1980年的中国读者带了久旱逢甘霖的兴奋和喜悦来阅读现当代外国文学,但是在举国一致的“现代化”语境下,很多欧美作家却是不折不扣的异类,辛格更是异类中的异类。重读辛格,这样的感受尤其深切。
辛格完全没有这种“科学的人生观”。《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中的主人公菲谢尔森博士服膺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展现的那种纯而又纯的理性的、逻辑的论证方式,他相信心灵最高度的完美是“对神的智性之爱”,并要用这种爱把人间的七情六欲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在宗教上,这位犹太老学者像斯宾诺莎那样离经叛道,衣着和生活习惯已经很像“外邦人”(“gentile”,即非犹太人)。他躲在犹太街区的阁楼里自成一统,以图书和学问为伴,还有一架望远镜供他“仰察天空的虚漠”。但是使他参领透彻生活乐趣的,并不是什么科学器具或纯理性的深思,而是一位帮助他从病中康复的文盲老姑娘。当隔壁邻居“黑多比”把她珍藏多年且从未用过的嫁妆一一向他展示的时候,菲谢尔森博士的身体战栗起来,斯宾诺莎式的科学理性顿时像阳光下的冰块一样融化。两人举办了传统的犹太婚礼,由拉比来主持。婚后,年事已高的博士恢复了生命活力,他惊叹自己的青春,也惊叹自己的“愚蠢”。也许肉体的激情一旦唤醒,灵魂的渴望将更加强烈。还可以断言,“黑多比”将使她的丈夫重新融入犹太社区。假如他们住处楼下热闹的广场“像是缀满了罂粟种子的椒盐卷饼”,“市场街的斯宾诺莎”或许会成为这卷饼里一粒普普通通的调料。
按照我们熟悉的模式,菲谢尔森博士即使要结婚,也应该找一个新式学堂的毕业生。“黑多比”不识字,也没有“脱盲”的要求,这样的落后女子,即使是明媒正娶的,信奉“进化”和“科学”、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进步男性知识分子也尽可以把她休了。我们习惯于假定,冲破“旧礼教”和“封建”家庭樊篱是新青年(如巴金《家》里的觉慧)的必然选择。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我国引起的热烈反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同情娜拉的命运,赞美她的勇气。整整一百年前,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里表述了很有代表性的观点:“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易卜生向友人推荐“有益纯粹的为我主义”,并写了一段深得胡适之心的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救出自己”就是履行娜拉在剧中所说的“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
在辛格的眼里,这种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为我主义”也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病态。让我们先从短篇小说《三次偶遇》以及作品中隐含的对中东欧犹太人聚居区的态度谈起。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居区名称不一,用得较多的是“ghetto”(“隔都”是译名之一)。长期以来犹太人在区内按照自己的传统方式生活,有自己的救助基金和救济院,甚至在法律上也独立,拉比法庭有一套惩罚仪式,比如《羽冠》就提及有人犯了“对抗社区罪”,被关押在专设的小屋里,甚至上了铁链。辛格笔下的隔都保留了犹太习俗,与外界比较隔绝,人口众多,街巷湫隘,楼房破旧密匝。《小鞋匠们》的一开头就写到还在使用中的坍塌老宅:“地基下沉,小窗户歪着,木瓦房顶上一层霉绿⋯⋯椽子实在是烂得很,都长蘑菇了。割礼时需用木屑止血,人们只需揭下一片外墙,手指一捻就行了。”至于区内的公共卫生,鞋匠的儿子如此抱怨:“希伯来语教师打孩子;妇女们直接把泔水倒在门外;开店的在街上闲逛;没有厕所,人们随地大小便,在净身浴池后面,甚至大庭广众之下,造成了传染病和瘟疫的流行。”当外面的世界在不断“前进”的时候,古老闭塞的隔都就成了被文明遗忘的角落,一个有上进心的犹太青年出于对“自己的责任”应该克服隔都心态,走出隔都。但是辛格却揭示这种观点可能含有的意识形态偏见。
《三次偶遇》中的叙述者“我”就是一个不满犹太人聚居区现状的年轻人。他的经历与辛格本人有点类似:父亲是拉比,但他不相信上帝在西奈山赐予摩西一部律法,不想子承父业。看到旧世界的瓦解和新人类的诞生,“我”也跃跃欲试。他十七岁离开家乡老斯蒂科夫,折腾了几年后因病回家,后来得知能到华沙一份意第绪语文学刊物做校对,将去未去之际很是得意。村里鞋匠的女儿莉芙基尔刚和父亲店里的学徒扬奇订了婚,她曾到“我”家借过一杯盐,归还时“我”见缝插针地向她灌输新思想,还吹牛说做了作家。这位“新青年”把一套文明进步的语言背得烂熟:外面的人看电影,听歌剧,上图书馆,但是在老斯蒂科夫,人们保守落后,不懂卫生、科学和艺术。这样的地方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一片泥潭:
“逃出泥坑吧!”我喊道,就像垃圾小说里的诱奸者,“⋯⋯等我成名了,我们就去旅游,巴黎、伦敦、柏林、纽约。那里,人们在盖六十层的高楼,火车在街上和地下到处跑⋯⋯”
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这不是我在说话,而是某个启蒙运动的宣传老手附在了我身上,通过我的嘴来讲话。
“逃出泥坑”与胡适所说的逃离冰海沉船,两者约莫相似。这番话在一个乡下姑娘身上产生了奇效,立即破坏了一桩也许不自由但未见得不幸福的婚姻(就像胡适父母的婚姻)。莉芙基尔也要像“我”那样挣脱自己的文化与宗教之根,她撕毁婚约,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一个由美国返回波兰的犹太移民,发觉上当,最后跟芝加哥的意大利后裔结婚,改宗天主教,终于完成了美国梦的第一步。“我”也从波兰移居美国,他没有急于到大熔炉里自我改造,反而生活在美国的意第绪语圈子里,用母语表达乡愁。他一系列的作品反映的不是新大陆的见闻,而是被自己抛在身后的老斯蒂科夫的景物和人事。这时的故乡早已不是死气沉沉的“墓地”,可惜他只是在人生阅历大大丰富后才能领略渗透在战前波兰犹太社区生活中的价值。莉芙基尔读到这些署了化名的故事泪流满面,立刻猜到作者是谁。她毫不犹豫地赴纽约找到“我”,提议与他结婚,重做犹太人的女儿。
《羽冠》表现了类似的认祖归宗的热情。小女孩艾卡莎爱上了读书,读了禁书《圣经·新约》,还学了法语、钢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提出要见一见求婚者,没有中意的。祖父又介绍了学经堂学生泽马契,不许两人见面。艾卡莎签婚约时才见到未来的夫君,此时耳边响起已故祖母的声音,让她别签,她遵命了。结果泽马契骂她泼妇,发誓永不原谅她。艾卡莎背弃了犹太教,还与外邦人结婚,更名玛利亚。但是年岁渐长,她越来越相信是魔鬼劝她改宗的,决心重做犹太人。等待艾卡莎的,又将是何种命运?难道她永远满足于独自诵读感恩祈祷词?辛格作品里那些走出隔都试图融入基督教社会的犹太人一般都不会幸福,他们总想着回到隔都重做犹太人。读到这些归宗认祖的故事,笔者也在担忧,是不是有着一种本质主义的宗教观、种族观在制约着他们的选择?
理想化的隔都与意第绪语文学
《三次偶遇》《羽冠》刻画了个人为追求所谓自由幸福产生的失重感、负罪感。辛格一再表明,在波兰的犹太共同体里,有一种难以释怀的、使个人的存在具有社会意义的东西;那里的生活绝非“愚昧落后”之类的语言所能概括、形容。在老斯蒂科夫和芝加哥、纽约等大都会之间,不能用一条进化发展的直线相连。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标举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否定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
辛格精心呈现的是隔都的独特的魅力——即使它不为启蒙运动的光芒所照亮。对任何贬低隔都的言论,辛格都不以为然。他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辞中说,别人在隔都里只看到悲惨和耻辱,犹太人却发现幸福;“伟大的宗教所宣扬的,生活在隔都里讲意第绪语的人们每天都在实践着。⋯⋯隔都不仅是少数受迫害者的避难之处,还是一个实验着和平、自律和人道主义的伟大地方”。难怪辛格笔下的老一辈犹太人在说到不厚道的犹太青年出走纽约和巴黎时非但不羡慕,反而会说:“这样的骗子还能去哪儿?”(《以色列的叛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都认识到纳粹以及东欧国家反犹主义的危害,但是笔者也以为,不必将隔都理想化,改造隔都,使之在法制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符合与时俱进的国家标准,也是不容回避的话题。
辛格的哥哥伊斯雷尔·辛格(1893—1944,也是旅美作家)一度就是启蒙思想的宣传老手。他年轻时常以无神论的观点刺激当拉比的父亲,父亲会骂他邪恶之人。在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篇全面评价辛格的文章里,作者这样写道:“艾萨克认为,他父亲的辱骂正好证明他理屈词穷。”可见当时在接受辛格的作品时有意把艾萨克往伊斯雷尔一边推,仿佛这样一来他的人生观与宗教观就比较安全、正确。辛格在不少方面(包括1935年赴美)受到哥哥的帮助,但是在他作品中,伊斯雷尔否定犹太传统的一些言论往往出自反面角色(甚至魔鬼)之口,这不难从本书中好几个故事得到印证。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两兄弟都是意第绪语作家,这使他们与一大批用英语写作并充分融入美国社会的犹太裔美国作家极为不同。辛格曾说,意第绪语是为外邦人和所谓思想解放的犹太人看不起的,但它却是无数犹太神奇传说的宝库。可以说,意第绪语是辛格的“回忆之母,情人中的情人”(波德莱尔诗句),他坚持使用这一语言来界定他的文化身份,同时使之成为连接他和波兰犹太社区生活的牢固纽带。二战期间,讲意第绪语的欧洲犹太社会遭到致命打击,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又提倡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成为濒危语种。辛格半开玩笑地说:“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复活的犹太亡灵都要读书,我得为他们做好准备才行。”调侃的口吻背后是沉痛,因为他知道意第绪语主要是亡灵的语言。
辛格使用意第绪语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心里某种隐痛。他作品里像他父亲那样老派的犹太教徒(一般都属虔信派,即哈西德派)总是得到他莫大的敬意。《爷孙》里的外公整天读经唱赞美诗,他的一年四季就是各种犹太宗教节日周而复始。他在故事结束时对那些歧视犹太人的俄国警察说:“是的,我是犹太人。我向上帝祈祷。”《短暂的礼拜五》里的施穆尔-莱贝尔和妻子苏雪又是一对典型的质朴单纯的犹太教徒,他们严守各种教规,为准备安息日整日操劳,晚间不幸煤气中毒。这对老夫妻在弥留之际依然恩恩爱爱,作者以飘忽动人的笔法描绘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也有一些教徒身上蕴藏了惊人的宗教热诚。
施穆尔-莱贝尔等人对自己祖先的神启的宗教坚信不疑,他们生活在犹太教哈西德派的相对窄小的圈子里,丝毫不受犹太启蒙运动的影响。辛格也曾描写过信仰中的困惑,甚至是对信仰的全面否定,但是否定却是通往肯定之途。在《那里是有点什么》里,贝契伏镇年轻的尼切米亚拉比看到好人受欺压,犹太人被残杀,而上帝对这一切不加过问,他终于发怒了。此时魔鬼以怀疑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引诱他、折磨他。于是他把犹太男子必备的祈祷巾和护经匣扔在一旁,以反叛的姿态来到华沙。目睹了都市里一幕幕纵欲的景象和形形色色的物质主义造神运动,他心力交瘁。尼切米亚拉比回到贝契伏镇时失魂落魄,几乎已奄奄一息。就在他的意识将离他而去之际,一道他未曾见过的光芒在他脑子里晃动,这大概就是显示上帝无限仁慈的神光了:
在东方,天空渐渐红了。“那里是有点什么。”拉比喃喃自语着。
贝契伏镇的拉比与上帝之间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创世记》中的雅各(又称以色列,犹太人先祖)就曾与神摔跤。信仰因经历一个怀疑的阶段而更成熟,更持久,这也是《旧约·约伯记》的主旨。《那里是有点什么》不妨被视为新版的约伯醒悟记,拉比在昏迷中所见的晨曦则是T.S.艾略特所说的“半猜到的暗示,半理解的礼物”。
傻瓜吉姆佩尔与阿Q:不能以机械方法看待的人类道德
面包师吉姆佩尔被人称为傻瓜,村里人都爱欺侮捉弄他。他糊里糊涂地与已有身孕的埃尔卡结了婚,时时受妻子虐待。埃尔卡患了乳腺癌,临终前请求吉姆佩尔宽恕,并告诉他,他们的六个孩子没有一个是他的骨肉。吉姆佩尔葬了妻子后,心里的愁苦和愤怒无法排解。此时魔鬼鼓动他报复:“全世界都骗了你,也该轮到你骗这世界了。”吉姆佩尔敬畏上帝,不敢存害人之心。魔鬼告诉他没有末日审判,上帝也无非是那“深潭泥沼”,良心的顾忌尽可打消。吉姆佩尔受诱惑后偷偷往面团上撒尿,要让耍笑过他的人尝尝他的厉害。但埃尔卡的亡灵显现了,警告他说:“你这个傻瓜!难道因为我虚情假意,一切就都是假的?”吉姆佩尔猛然警醒,尽管他的作为无人知晓,他还是把已经搅拌了尿液的面包从炉膛里取出,在冰冻的地上掘了个洞,把它们全部埋掉(“慎独”的典型事例)。从此吉姆佩尔开始流浪,东西无定。他渐入老境,坦然等候动身去“真实的”世界:那儿“没有算计、没有嘲弄、没有欺骗。赞美上帝:在那里,即便是吉姆佩尔也不会被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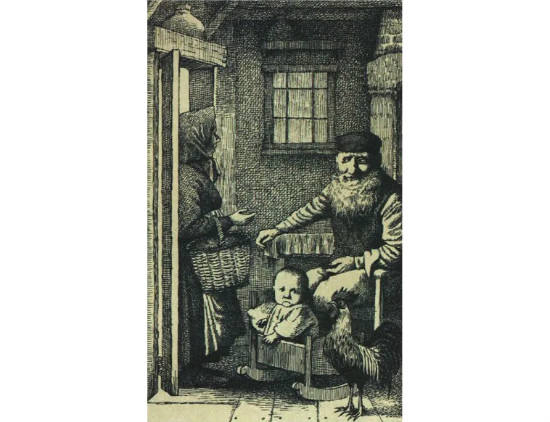
辛格小说外文版插图
这里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吉姆佩尔与其作恶一刻,不如做一生傻瓜。他的道德世界独重动机。假如这批面包烤出来很香,是不是动机便可以不再追问而且用尿液掺拌面团将成为一道工序呢?在电影《红高粱》里“我爷爷”当众对酒篓子撒尿是为了抖威风,图报复,可是我们注重的是实用与功利的结果而非道德动机。经尿碱勾兑的高粱酒更醇美,大家为此还兴奋一番。
其次,或许有人会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样的套话来形容他们对吉姆佩尔的态度。在我们的文化里,吉姆佩尔这样的人因所谓的“过于软弱”和“姑息养奸”而容易被看不起。要是说某人抱了“满腔仇恨”去“与命运抗争”,那就是莫大的褒奖。“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之类的话语支配了我们的本能反应。也许我们的敌我界限过于分明了。如鲁迅在《野草》的题词里列出这几个对立的范畴:“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对“仇”“兽”和“不爱者”就要痛打,出言则以多刺伤人为上品,绝不讲什么“费厄泼赖”。
但是在辛格的世界里,仇恨、愤怒和报复心等暴烈的情绪有待克服(我国也有“制怒”“惩忿”的观念),而内心的平和才是值得敬仰的境界。吉姆佩尔没有睚眦必报的雄心,倒有一颗仁恕的大心。他和欺软怕硬的阿Q全然不同:阿Q在心理上“常处优胜”,吉姆佩尔对胜败则有点木然。吉姆佩尔的事业是做一个好人,没有曲承颜色的心计,也记不得什么奇耻大辱,一心为灵魂的纯洁含辛茹苦。他因善良而不设防范,也因善良而面对魔鬼的引诱绝不退让。《短暂的礼拜五》里的施穆尔-莱贝尔也是类似吉姆佩尔的“傻瓜”。他心存感激,屡屡受人捉弄也从不在意,从不生气。镇里要找送信的人,他总是抢着去,即使路途遥远,他也高高兴兴地上路,从不以为这是仁爱之举。这两个“傻瓜”像是犹太传说中隐匿在人间的谦卑的义人,是他们在默默地给世界撑起道德的标准。
辛格笔下也有女性的“傻瓜”,她们可能做过在常人眼里不合正道的“傻事”,但是她们也具有吉姆佩尔的仁厚与善良。在《克洛普施托克的引言》里,年轻作家迈克斯·伯斯基为查证一段德文诗歌的出处,求教于在华沙教授德国文学的犹太女子特蕾莎·斯坦小姐。这位作家是辛格笔下诸多唐璜式的人物之一,大胆得几近无耻,然而在他半是炫耀、半是抱怨地说自己正同时与四个女人有染后,他听到的话居然是“你这个可怜的孩子”。迈克斯利用对方的同情与善意强行向她求爱,想不到被接受了。比他年长二十几岁的特蕾莎·斯坦小姐爱上了他,坚贞不渝。迈克斯在他猎物名单上增添了一位十六世纪西班牙圣女特蕾莎般圣洁的人物,继续把他的情爱东抛西掷。他一面勉强敷衍斯坦小姐,一面不断向她倾倒自己在情场上的垃圾经历,这一切从未激起听者的妒忌和怨恨。为了斯坦小姐的体面和清名,迈克斯不应该讲述这个颠覆死者形象的故事。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觉得斯坦小姐与这个浪荡子做出来的荒唐事构成她身上的瑕疵,我们不会笑她,反而因她那种类似吉姆佩尔的“愚忠”而笑自己开明的盲目。真正令人失望的是以她这样的纯洁和宽厚最终仍不能使迈克斯稍稍有所改变。
斯坦小姐是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的产物,《泰贝利和魔鬼》中的弃妇泰贝利则是没读过书的村姑。泰贝利的几个孩子都夭折了,丈夫远出不归。她是不幸的,但她生性喜乐,从不埋怨生活亏待了她。犹太社区里教师的仆人阿尔乔农穷困潦倒,丧妻五年,也没有子嗣。他见泰贝利独居,起了邪念,假扮犹太传说中的鬼怪赫米札,乘夜色潜入她的卧房,利用她的惊慌和迷信迫她就范。从此他每周两次光顾她的小屋。阿尔乔农满脑子奇思怪想,口才极好,随意编说的故事都像山谷里的闲花野草,清新可爱。他也许早就迷上了泰贝利,不然她一年来穿用过的衣裙和披肩,他怎么一件件一条条都说得出来呢?泰贝利听这鬼怪夜半胡言,倒也开心,时间一久也就爱上了他。有一晚阿尔乔农因病未能按时赴约,泰贝利久候赫米札不至,心中悲切。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阿尔乔农孤零零地死去,没人为他送葬。泰贝利见办丧事的抬着尸体走过,不知道就是他在扮鬼,出于对死者的同情,她跟着担架,“把这个寂寞地活着又寂寞地死去的无用之人送到他安息的地方”。又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被封存在心底。
斯坦小姐和泰贝利的爱情都是难以理解的,人的行为中怪异出格之处恰恰是辛格纵横无忌地展示睿智的地方。《凡维尔德·卡瓦》里有这样一句话:“有许多人类行为是毫无动机可言的。”故事里的主人公是司马相如那类“含笔而腐毫”的作家,他应约写一篇概述意第绪语文学的文章,开始还顺顺当当,但写到“纯种”一词后就离题万里,探讨起马的生理学和解剖学特征来。人类社会的无限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许就取决于人的行为无法预测。当我们习惯于从经济角度或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理解人的行为或社会状况时,我们就把自己和自己的同类视为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小狗了:它们总是在给定的状态下做出可以预料的反应。简单机械的因果律和决定论无助于伟大文学的产生。
辛格小说的政治观念:人人皆可能是纳粹
辛格极少直接描写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但这本集子有几个故事涉及广义上的政治,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来谈。
在《爷孙》里,恪守传统的犹太教徒与年轻一代的犹太裔世界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表现为对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历史进程的探讨。莫德凯·梅尔先生属华沙隔都里的哈西德派,整天研读经书。独生女儿嫁给一位立陶宛的开明犹太人,他就断绝与她的父女关系。故事发生时梅尔的妻女都已病逝,俄国刚在日俄战争中被打败,境内(包括波兰)的罢工和骚乱接连不断。火车出轨和暗杀之类的恐怖事件也时常传来。人们为了想象中的社会正义不择手段。从未见过的外孙弗列此时找上门来,他的举止穿着已没有丝毫犹太人的痕迹。外公外孙仿佛生活在难以沟通的世界里。弗列读的是经济方面的书籍,对人间苦难的成因有着简单现成的答案。他信奉进化论,否定上帝的存在。梅尔的反应有点像辛格本人的父亲,恨不得对外孙大喊:“恶棍、耶罗波安、尼八养的,从我家里滚出去!”外孙告诉外公世界为什么不公道,要使全人类得解放,犹太人必须联合一切被压迫者推翻沙皇,由“人民”来统治国家,将来一切按需分配,捞取油水的商人将不复存在。外公则对美好的乌托邦有所怀疑。弗列携枪参加示威游行,随时准备回击那些“阻碍进步,试图让这个世界在黑暗中停滞的人”,但最终还是被俄国警察枪杀。梅尔曾以《创世记》里以扫和雅各的故事(“以扫倚靠刀剑度日”)反驳外孙,他反对暴力和仇杀的立场不会动摇,但他对死去的弗列也怀悲悯之心,相信他动机纯正,所做的一切缘起于对受苦受难者的同情,灵魂必能得救。面对反犹排犹的沙皇警察,梅尔唯一的武器就是他在故事结束时说的一句话:“我向上帝祈祷。”
假如《爷孙》触及使用暴力是否合理这样的道德议题,辛格还将敏锐的目光投向有可能被警惕地设为禁区的领域:受迫害者的操守和不幸事件的利用价值。

《纽约客》拍摄的辛格工作室。
辛格在犹太裔意第绪语作家中是有点争议的人物,有人指责他仇恨犹太人,想从犹太人内部对犹太人实施报复。意第绪语作家芬伯格说,基督徒和背弃犹太教的犹太人喜欢读辛格的作品,“就因为这些故事中犹太人被表现得比外邦人还要邪恶”。我想这类指控之所以出现,并不完全是因为辛格把吉姆佩尔周围的人写得太灰暗。
我们说到现代史总会有一种近乎幼稚的好人与坏人、受害者与施害者的预设。有的苦难史被神圣化,于是苦难本身就成了巨大的权力资源。滥用这种权力,彼时的受害者可能沦落为此时的施害者。我们需要考查受难的故事如何产生、演变,如何被阐释并赋予特殊意义,我们也应探究受难与现今政治外交利益的错杂关系。可是这些至关紧要的问题却容易被搁置起来,甚至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变为禁忌。辛格的勇气和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一方面谴责纳粹暴行,一方面又拒绝煽扬集体悲情,拒绝把犹太民族在二战时的不幸遭遇当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政治和道德的资本。这位犹太民族忠诚的儿子在着力刻画历史悲剧对本民族造成创伤的同时,也用批评甚至有点挑剔的眼光来看待犹太社群内部可能存在的问题。为了犹太民族的灵魂的纯洁,他不惧众怒。他深刻揭示,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并不是只有一个声音,一张面孔;受过迫害并不意味着获致美德,在有的情况下,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只一纸之隔。
《旅游巴士》里那位犹太女子塞琳娜是集中营幸存者。二战结束后,一位瑞士银行家与她结了婚,仍被她骂为“反犹分子”(她不时搬出来投击别人的最有效武器)。和泰贝利、斯坦小姐等人相比,塞琳娜只以怨天尤人见长。她总是从昂贵的店家拎回大包小包的商品,可见十分阔绰,还要抱怨丈夫小气。每到一处观光,她总是不能按时回到旅游巴士上,让一车人等候,她也绝无一丝歉意。故事叙述者不得不向她指出:“夫人,您的所作所为对犹太人的伤害,超过所有反犹主义。”这样的语言大概触犯了作者的一些同胞。
在有的故事里纳粹成了给人方便的借口,各种心病都可以找永远不会回嘴的纳粹来担负责任。《玩笑》里那位德国犹太人瓦尔登博士在编撰一本希伯来百科全书,这部巨著就同乔治·爱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里卡苏朋先生的神话研究一样永无竣工之日。
辛格在这样的故事里暗示,纳粹做出来的事情,其他人也做得出来。在长篇小说《冤家,一个爱情故事》里,主人公旅美犹太人赫尔曼周旋于三个女人之间,其中之一对他说:“干吗总是要提纳粹呢?我们都是纳粹。全人类都是!你不仅是个纳粹,还是个懦夫,连自己的影子都怕。”那部作品中最大的骗子是纽约的兰珀特拉比。他集房地产商、犹太教领袖、慈善家、社会闻人和作家于一身,整日奔忙。但是他的每部著作,每篇演讲,都由赫尔曼捉刀。犹太民族在二战时的经历是兰珀特拉比的滚滚财源。辛格在这部小说的“序”上说,他自己“没有荣幸地经历希特勒的大屠杀”。“荣幸”一词暗含讥诮,它所传达的信息不难领会。
辛格刻画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犹太社区里的常人,不少还是十分卑微的角色。他相信,越渺小,越伟大;越贴近尘土,越靠近上帝。
辛格笔下脱离犹太教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这是他令读者失望的一面,但是从分析、揭示作为罪恶的“骄傲”而言,这个短篇对于自我认知具有极大的参照价值。英国学者C.S.路易斯(1898—1963)的《魔鬼家书》是高级魔鬼“私酷鬼”致侄子“瘟木鬼”书信的汇编,专门教授一套从心理上拖人下地狱的伎俩。路易斯以资深魔鬼的口气剖析人性的弱点,让每个读者都对自己意识中最隐蔽、真实的动机有所警惕。下面这个例子应该让习惯于积极评价自己的中国传统文人警醒。“私酷鬼”知道如何攻破常人的心防,他说,让“病人”(持守美德不甚坚定者)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转向自我,转向自己的美德:“一旦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具备何种品德,对我们而言,那种品德就没那么可怕了,一切品德概莫能外,不过,这招对谦卑特别管用。在他真正虚心起来的那一刻,要把他一把抓住,并在他脑子里偷偷塞入‘哎呀!我变得谦卑起来了’这样欣慰的念头,而骄傲——对于自己谦卑的骄傲——几乎立刻就会出现。”骄傲是魔鬼击溃善人心防的最强大武器,忘记自己,让自己消失在爱的对象之中,这是魔鬼最惧怕的态度。路易斯揭示,意识到自己的美德其实是骄傲的起点,容易致人堕落。我们诗文里的自美自夸实在数不胜数,路易斯看来,自夸者已经深得撒旦的精神了。辛格深知骄傲之害,他笔下的善人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美德。这,恰是魔鬼所痛恨的。
(注:本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辛格自选集》前言,由出版社授权刊发。较原文有删减。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陆建德
编辑:宫子、李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