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何安安
2001年,一位名叫丹尼·沙利文(Danny Sullivan)的建筑师声称,他在蒙斯一家旧货店翻找东西时,发现了一部记录有天使的影像资料。不出所料,这是一场骗局,就像有人声称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为这段视频支付了35万英镑一样。
但沙利文所声明的这份影像资料的出处非常有趣,他创造了一位名叫威廉·多伊奇(William Doidge)的精神研究人员。沙利文声称,多伊奇曾经在1914年8月的蒙斯战役中与苏格兰卫兵作战,而在蒙斯,有英国士兵声称真的看到了天使。在此之前,天使是在很久以后,也就是1952年才于科茨沃尔德被摄影机拍摄到的——当然,这个故事虽然众所周知,但也被证明没有任何现实依据。
1914年9月,威尔士作家阿瑟·马肯(Arthur Machen)在《伦敦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弓箭手》的小说。里边提到来自阿金库尔战役(发生于1415年10月25日,是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的幽灵弓箭手在蒙斯帮助英国远征军。令他沮丧的是,这个故事被广泛认为是真实的,一个“谣言的雪球”变成了“最确凿的事实”。“如果说我在文法上失败了,”马肯后来写道,“那么,我在不经意间,在欺骗的艺术上成功了。”
从战争中进入一个充满魔幻思维和神秘经历的鬼怪世界

《一场超自然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魔法、占卜和信仰》(A Supernatural War: Magic, Divination and Faith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 欧文·戴维斯(Owen Davies) 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精装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超自然故事是阿瑟·马肯的创作,但在当时的前线,却有许多关于超自然现象的真实报道。在《一场超自然的战争》中,欧文·戴维斯带领我们从战争中进入一个充满魔幻思维和神秘经历的鬼怪世界。历史学家汤姆·格里菲思(Tom Griffiths)写道,“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德是坚定不移的复杂性。”这就是我们在戴维斯的书中所看到的。他笔下的占卜师既是治疗者,又是骗子;他笔下的灵媒既是顾问,也同样是骗子。科学与魔法、理性和宗教之间不存在对立,因为这些二分法会掩盖其间的错综复杂和矛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普遍认为,这场战争使得“迷信”的信仰和习俗得到了极大的复兴。教会对护身符和人们佩戴护身符表示担忧,国际媒体却对占星者和先知的预言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一些国家当局由于担心这会对公众士气造成影响,而定期对占星者和灵媒进行打压。但另一方面,在战场上,所有国家的士兵都试图通过魔法和宗教仪式来庇佑自己;在家庭里,人们同样试图通过寻找通灵者和神秘学家,以便了解远在他方的亲人们的命运,或与他们的灵魂进行交流。即使抛开对战争的担忧不谈,被怀疑是女巫的人仍然会受到虐待,但人们也会继续求助于魔法和魔法师,以获得个人庇佑、爱情或者成功。
欧文·戴维斯揭示和审视了关于超自然力量在战争年代中的作用和信仰,通过当代观点,探讨了西方二十世纪早期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战时超自然的神秘学,以及这场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通灵和魔法的普遍信仰和关注的延续。戴维斯在《一场超自然的战争》中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充满神秘力量的世界中的那些非凡的人物。
1914年的欧洲注定要经历一场巨变
在许多人看来,1914年的欧洲注定要经历一场巨变。1908年出版了军事科幻小说《空中的战争》(the War in the Air)一书,在书中,作者以其先知般的想法、图像和观念,使用太空飞船用于战事以及即将来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小说的英雄是一个“思想超前的年轻人”,也是一个“自行车工程师”。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并不是唯一一个构思这场重大冲突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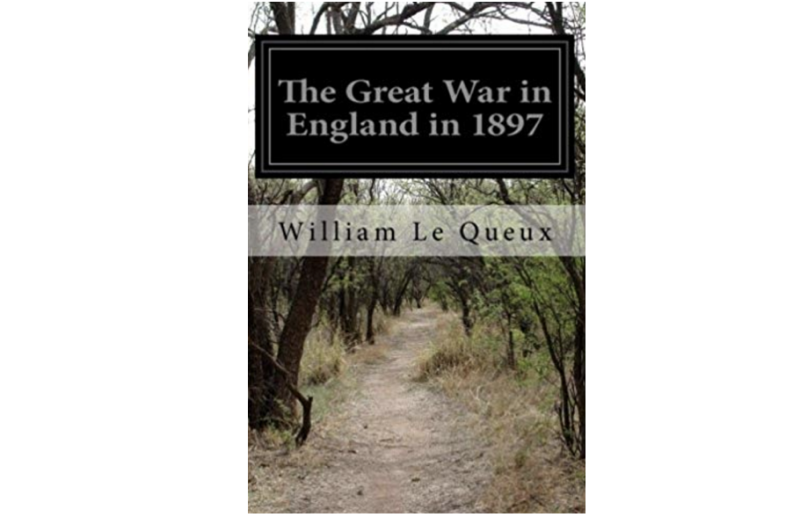
《1897:英国的伟大战争》(The Great War in England in 1897),威廉·勒·奎克斯(William Le Queux) 著,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6年4月版。
几年前,《每日邮报》(Daily Mail)连载了记者威廉·勒·奎克斯(William Le Queux)的一部关于入侵德国的小说。在他创作于1894年的《1897:英国的伟大战争》一书中,奎克斯将德国列为英国对抗法国和俄罗斯的盟友。这些虚构的故事对神秘主义和历史预言进行了补充——从诺查丹玛斯 (Nostradamus)到18世纪的预言家乔安娜·索恩科特,古老的预言获得了全新的解读。在法国,公元七世纪,圣徒奥迪尔曾经预言德国将在一场大战中被击败。德国也有类似的记载,比如一本由提洛尔僧侣写于1717年的小册子,里面预言了一位德国王子将获得胜利,这本书被重新发现于1821年,并于1916年出版。

《1897:英国的伟大战争》于1894年首次出版于伦敦。
和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一样的神秘学者们吹嘘着自己早在1910年就成功预言了即将来临的战争。在1909年至1912年间,泰丁顿的一位灵媒曾多次通灵过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他转述了恺撒关于“阳光下微笑的玉米地里的红色罂粟”的警告。长期以来,巴黎名人底比斯夫人(Madame de Thebes)一直在预测普鲁士军国主义在最后一场战争中的消亡,法国将在这场战争中“重新焕发活力”。占星家们重新找到了观众,就像他们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所作的那样——唯一的差异是大众媒体对他们给予的宣传。

恺撒遇刺(公元前44年)。
人们把战争和天启联系在一起
基督教类型学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框架。无论是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还是表现主义者,比如马克斯·贝克曼和奥托·迪克斯,每个人都把战争与天启联系在一起,要么是幻象隐喻,要么是准确的预言。一位圣经学者评论道:“在整个基督教史上,从来没有反基督者如此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的力量。”

马克斯·贝克曼《鸟的地狱》。画作以刚劲有力的笔触及鲜艳夺目的色彩,将观者带到阴森可怕的地下世界,目睹鸟形怪物对人类施以酷刑。
从战争爆发以来,关于神秘力量的故事比比皆是。法国天主教军队在马恩战役和俄罗斯东正教军队在奥古斯托夫战役中报告说看到了圣母玛利亚。一位在蒙斯负伤的英国军官说:“我并不喜欢唯心论。但是,当你一次又一次地亲身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其中一定有某种东西。”战场上的幽灵并不新鲜:罗马军团看到了卡斯特和波利克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士兵们看到了圣人。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认为这很自然:“一名士兵从另一名士兵那里获得灵感;所有人都急于承认眼前的奇迹,在发现错误之前,他们就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的机械化屠杀,还在于它将新旧思维习惯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等新兴学科意识到,在20世纪,人们呈现出对回归传统的渴望。美国心理协会的首任主席格兰维尔·斯坦利·霍尔认为,蒙斯的天使,正是社会压力的迷人体现:“战争让人们如此紧张。”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兴奋地看到战壕里“口头传统的奇妙复兴”。人们通过电话或者电报,简单地传递着几句毫无根据但对听者来说却意义重大的谣言。以美国远征军的身份在法国服役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美国文化人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认为,士兵们的护佑仪式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图腾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梵蒂冈的观点认为接触灵魂是邪恶的
现代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对有组织宗教的信心危机。天主教比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更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因为它配备了令人安慰的仪式以及一系列的圣人和天使。许多英国国教牧师发现他们的服务被遗弃了,因为天主教牧师提供更加优越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天主教会谴责唯灵论者为恶魔,而英国国教与灵媒的关系则更为矛盾,他们认为任何产生持久精神的东西都值得宽容。博迪牧师(Reverend A.A. Boddy)是英国圣公会(英国的国家教会及安立甘宗的母教会)的一名牧师,他曾在前线服役(他认为战争预示着第二次降临):一名抬担架的人说,他在一次轰炸中进入战壕,发现这些人在“一群天使”的监督下“祈祷”,所有在场的人都能看到他们,没有人受伤。博迪牧师在一本名为《蒙斯的真正天使》(Real Angels of Mons)的小册子中提到了这个故事。
尽管博迪牧师对神秘学充满热情,但他认为唯心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并同意梵蒂冈的观点,即接触灵魂是邪恶的。相反,一位名叫菲尔丁·菲尔德的伦敦牧师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问道:“唯心论是魔鬼的吗?”他不这么认为,并为英国人民了解真相的权利辩护:“他们的丈夫和儿子每天都在被杀害,他们需要一些活生生的、合理的指导和教诲。”唯灵论家坚持认为,他们的服务对新死者来说是必要的,新死者的灵魂处于伤痕累累和困惑的状态。一旦新死者在面纱后面舒适地安顿下来,灵魂们就会返回战场去帮助天使和白人同伴,而这些由灵魂组成的军团每天都在扩大。
不是每个士兵都在前线有过超自然的经历,但到1918年,对魔法和灵性的信仰已经普及。护身符是普遍存在的。士兵们戴着心形护身符、石南花枝、四叶三叶草、兔子的脚、微型马蹄、有洞的鹅卵石(传统上是一种驱除巫婆的东西),以及描绘圣人、天使、基督和圣母的天主教徽章。德国人带着“天堂信(Himmelsbriefe)”——据说是基督写的。提洛尔军队的内衣里缝着蝙蝠的翅膀,塞尔维亚人戴着第纳尔腰带,阿布鲁佐的士兵们在战斗前会在肩膀上撒上几撮当地的土——这是一种便携式的家园,就像一位爱尔兰军官珍爱的一块煤块。
被子弹和弹片刺穿的圣经被认为具有预防魔力,就像在英国和美国内战期间一样。高地兵团的一名士兵对着他叔叔在布尔战争中携带的一块黑石头起誓,这块石头是另一位祖先在滑铁卢携带的。符咒贸易开始变得流行,最为昂贵的是用贵重金属和宝石做成的吊坠——但廉价的小饰品更为典型。制造商会在报纸上登广告,最受欢迎的护身符之一是“fums up”,一个由金、银或黄铜制成的小婴儿(或侏儒),通常有一个木制的头(这样主人就可以“摸木头”)。这些护身符有的戴在表链上,有的戴在胸针上,有的藏在服务礼服的口袋里。象征财富和保护的符文、符号、万字符也很受欢迎,动物吉祥物也是如此——从鹦鹉到乌龟再到小熊。在埃及的澳大利亚军队设法抓住了一只袋鼠;新西兰人在法国养了一头叫摩西的驴。
超自然思维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不仅是因为战争对社会的影响,而是因为这种信仰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流行。大萧条给战后的政治焦虑增加了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而这反映在占星术和历书的不断增长上。1930年,《星期日快报》(Sunday Express)开设了英国第一个占星术专栏。根据一项大规模观察调查,在短短几年内,伦敦三分之二的女性相信未来是由星星预测的(只有五分之一的男性承认这一点)。到1942年,《大众观察》估计大约有一半的英国人相信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更多关于幻想和预言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德国被压制,因为它们不利于国家对真理和权力的垄断。
在欧美人们仍然相信女巫的存在

《格里莫伊尔:魔法书的历史》(Grimoires: A History of Magic Books),欧文·戴维斯(Owen Davies) 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除此以外,如果想要更多了解关于魔法的故事,同样由欧文·戴维斯撰写的《格里莫伊尔:魔法书的历史》是个不错的选择。出现于中世纪晚期的格里莫伊尔(Grimoires)也被称为魔典,它是中世纪最为古老的魔法书。没有任何书会比恐惧更加令人恐惧,也没有任何书会比恐惧更加受到重视和尊重。在《格里莫伊尔:魔法书的历史》中,戴维斯阐明了这些未经发掘的书所具有的许多迷人的形式,以及这些书所拥有的一切。
很难解释魔法的善良与邪恶,就像无法解释魔法本身一样。在它们最善良的时候,这些被禁止的知识揭示了如何制造强大的护身符和魔法符号,提供治愈疾病、寻找爱和驱邪的魔力和咒语。但在另外一些书中,也提供了如何控制无辜受害者,甚至如何召唤魔鬼。
戴维斯追溯了这一极具弹性和适应性的流派的历史,从古代中东到现代美国,为西方文明在过去两千年的基本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本书展示了魔法和魔法写作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丰富地展示了它们在基督教传播、文化成长和西方传统从殖民时代到现在的影响中所起的作用。正如《月亮的胜利:异教巫术史》(The Triumph of The Moon: A History of Pagan witch)的作者罗纳德·赫顿(Ronald Hutton)所言,“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不仅因为它的研究深度,而且因为它的广度,从马萨诸塞州到马提尼克岛,再到毛里求斯。它一定会成为这方面的经典著作。”显然,这是一部包罗万象、引人入胜的历史。
需要提醒的是,如同相信魔法的存在一样,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各地的人们仍然相信女巫的存在,并且在法律已经被废除很久以后,仍然支持用暴力对抗巫术。在乡村地区,这种观念非常普遍,在城镇里盛行的则是唯心论,或者如它的批评者所描述的“现代巫术”。
综合编译 | 何安安
编辑 | 李永博
校对 |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