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的《宠儿》是伟大的小说,用莫里森的话来说,它的目标是让我们“重现记忆”奴隶制,尽管忘却似乎更有利于健康。那么在当今时代,阅读《宠儿》,益处何在?我们如何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来理解和应对当今形势,来回应全球化时代、包罗蔓延的网络空间和毫无止境的反恐战争或西方内部分裂等问题带给我们的变化?
最近,美国文学评论家J.希利斯·米勒的《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在这本书的第四部分,米勒对莫里森的《宠儿》进行了长篇的重点分析。在书中,米勒从我们时代的国际变化开始谈起,进而讲述了莫里森为什么重要,以及阅读莫里森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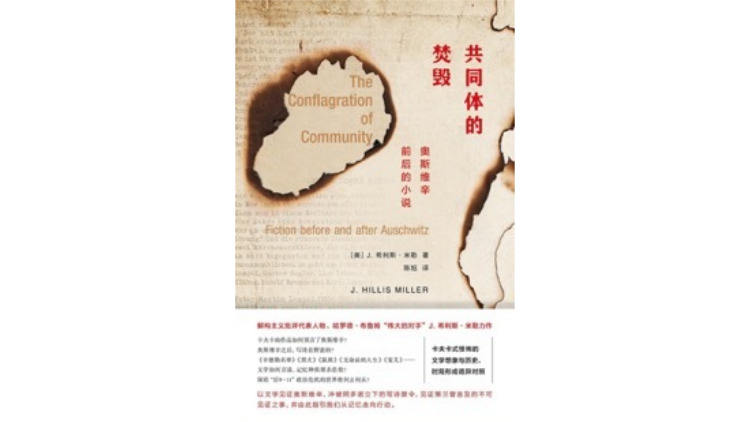
《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美]J.希利斯·米勒著,陈旭译,守望者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
作者丨J.希利斯·米勒
如今这世道
自1987年《宠儿》发表以来,往轻处说,许多事情木已成舟。冷战结束了。回顾起来,冷战似乎只是小冲突,其背景正如乔治·奥威尔所预见的那样,是国家大规模集聚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对抗局面。
远程技术革命使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可通过电邮、互联网和iPhone等手段实现即时交流,将他们潜在地联系在一起,这改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使“全球化”成为现实。我们的政府以及与其勾结的银行和大公司,在贪婪的驱使下,用欺骗的手段将美国和整个世界带向经济衰退,房产泡沫破灭,随之而来的是全球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失业率奇高。我们累积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贫富悬殊加剧,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西方的“圣书的宗教”彼此交战,尽管它们的起源都可追溯到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从基督教宗教激进主义或从伊斯兰教宗教激进主义的视角来看,某些科学观念,比如相信进化论、相信妇女有选择权或相信全球变暖的证据,都是魔鬼蛊惑的结果。
这三大信仰体系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它们决定着近段时期的世界历史,比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全球恐怖主义、反恐战争以及伊朗和朝鲜准备发展核武器的防卫计划。现在朝鲜取得了成功。如果你被宣布为邪恶轴心的一部分,并被威胁会受到单边“预防性的”“政权更替”,你会怎么做?我想你会做好准备,尽一切力量保卫自己。
然而,如果没有科学、全球资本主义和新的远程通信技术,就不可能有恐怖主义、反恐战争和核武器。让“9·11”变成所谓全球重大事件的,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超过两千人的有形死亡,而是媒体、电影将这一事件传递到世界各地,那些电影展现了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楼倒塌的过程,它们具有让人不安的双重阳物(double phallic)的象征。(我说“让人不安的双重阳物”,是因为弗洛伊德宣称阳物的双重化等同于阉割,这正象征了西方资本主义在双子楼倒塌时所遭受的冲击。)

布什政府随即宣布反恐战争开始。恐怖分子和布什政府都希望双子楼倒塌的画面能经常出现在所有地方,还有媒体本身也希望如此。媒体有这样的希望,部分原因是为了从广告中赚取更多利润,因为广告与那些重复播放双子楼坍塌的影片交织在一起。只要一有机会,那些影片现在仍不时会播放。恐怖分子运用他们所谴责的那些技术手段,正如他们用飞机、炸弹,用媒体播放奥萨马·本·拉登那些挑衅的警告,还用手机联络或引爆“简易爆炸装置”。
美国的宗教右派使用媒体(如脱口秀、“远程福音”布道、网站和博客),还通过他们对政府的影响,使用高科技武器,比如,用无人攻击机打击塔利班基地组织,而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平民则成了“附带伤害”的领导层中可见一斑,黑水集团作为平民承包商,其雇佣兵曾在伊拉克展开行动。那种共谋在布什政府的构成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那届政府执政的灾难性的八年时间里,其成员先后出现过像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这样的宗教狂热分子,像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这样的石油公司前CEO,还有像道格拉斯·菲斯(Douglas Feith)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乔治·W.布什则将福音派宗教信仰与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以及公司基底结合在一起,尽管他本人作为一个石油公司管理者也同样失败。
再者,我们想象不了他晚上读卡尔·施米特论主权的情景,无论关于他重生的基督教信仰可能被说得多么真实可靠。他说进化论目前尚无定论。只有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他才会极不情愿地承认气候变化的确存在,他和他的政府及工业盟友,除了“自愿遵从”之外,抵制一切想要缓解气候变化的尝试和努力。这种态度即使在巴拉克·奥巴马在任的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改变。
代表石油和煤炭的游说团体相当强大,它们对政府决策产生很大影响,就如代表医疗保险和制药公司的说客成功使国会通过了一项对其做出巨大让步的医保改革法案。两党参议员们从这些公司捞取了数百万披着合法外衣的“竞选献金”,但在我看来,这些献金是买选票的贿赂。
我们如今的世道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特征,与我讨论的共同体的焚毁的话题密切相关。互联网自1987年开始崛起并普及,诸如手机、iPod和iPhone之类的设备现已无所不在,这使得七八十年代的后现代小说——比如莫里森的《宠儿》或多克托罗在那个时期的小说——以及反思那个时期文学的著作,如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看起来有些古怪过时,它们似乎是从一个现已消失的过去的世界传来的声音,在那个世界里,纸质书籍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共同体,很可能是由电脑游戏玩家或博客参与者所组成的奇怪的网络社群。一个既有的博客网站,在一天之内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阅读和写作。这是一种奇怪的共在形式,因为网络共同体的成员可能不会选择用自己的真名。然而,这些共同体也可能产生强大的政治文化影响。

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的博客“绿色小足球”(Little Green Footballs)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在2010年1月24日刊登了乔纳森·迪伊(Jonathan Dee)的题为《右翼骂战!》(“Right-Wing Flame War!”)的精彩文章。该文细致地呈现了乔纳森如何将其博客发展成右翼主要阵营,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每天阅读并参与,但乔纳森之后突然倒戈,投入左翼,反对福克斯新闻、拉什·林博、莎拉·佩林以及他之前的同事们。一场激烈的“骂战”随之兴起,乔纳森和他以前那些极端的共事者在网络上你来我往地发表攻击性言论。现在如帕梅拉·盖勒(Pamela Geller)这样的右翼人士痛斥乔纳森是“叛徒、变节者、卧底”。
这些良善的人属于网络空间中极为奇特的共同体。正如迪伊所评论的,这种远程技术的虚拟共同体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除非被刻意抹去,否则所有这些博客无论多久都会同时在网络上继续存在,它们以电子格式的形式实现了塞丝所说的“没有什么会死去”。乔纳森早期那些极端保守的激昂演讲仍然能在他的网站上找到,与他近来变得相信气候变化之后所发表的言论公开发布在一起。
除此之外,比肩而立还有他近来转而反对比利时极右翼政党“弗拉芒利益党”的言论,而他之前支持该党。这些“虚拟现实”可能看起来太过无形,不会对“真实世界”产生影响,但是它们的确影响了人们投票以及其他行为方式。美国当下右翼民粹主义的茶党成员通过互联网团结在一起。
不久之前,他们说服马萨诸塞州的人们把斯科特·布朗(Scott Brown)选进了美国参议院,布朗在此秉持了共和党人坚定地“只要说不”的决心,他誓言阻止医保改革,赞成水刑,反对碳排放限额和交易,阻挠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施管理。
伴随其他国家和全球发生的变化,这种局面将会产生新的后果。时间将表明局势会如何变化。
阅读《宠儿》,益处何在?
对于理解,甚或改善我们如今的世道,文学有什么作用?下面以莫里森的《宠儿》为例,加以说明。我们应该阅读、讲授或者分析这部小说吗?如果应该,理由又是什么?
如我所言,《宠儿》首次发表于1987年,比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单行本(1991年)出版早四年。读者因而也许可以合理地假设,就像我所认为的那样,《宠儿》是一部后现代作品——无论这么说除了在简单的时间划定之外还意味着什么。所谓的后现代文学能帮助读者面对当今世界吗?
《宠儿》开篇的时间是1873年,读者会逐渐发现小说的中心事件是十八年前,塞丝杀害了自己幼小的女儿,以免她被带回,沦为奴隶。她还试图杀害自己其他三个孩子并自杀。整部小说围绕这个事件,对其暗示、抵制、复指,直到最后才以耸人听闻的细节直接描述。
更确切地说,小说从“学校老师”的视角,描述了塞丝抱着她濒死的孩子的场景:“里面,两个男孩在一个女黑鬼脚边的锯末和尘土中流血,女黑鬼一只手搂一个血淋淋的孩子在胸前,另一只手抓着一个婴儿的脚后跟。”用手锯割断婴儿喉咙的事件,在小说中只有间接的指涉。这一“难以形容的”或至少“从未描述的”事件,是《宠儿》的主导主题。它不断地再现,是小说中“重现记忆的”后台事件,组织起小说的整个叙事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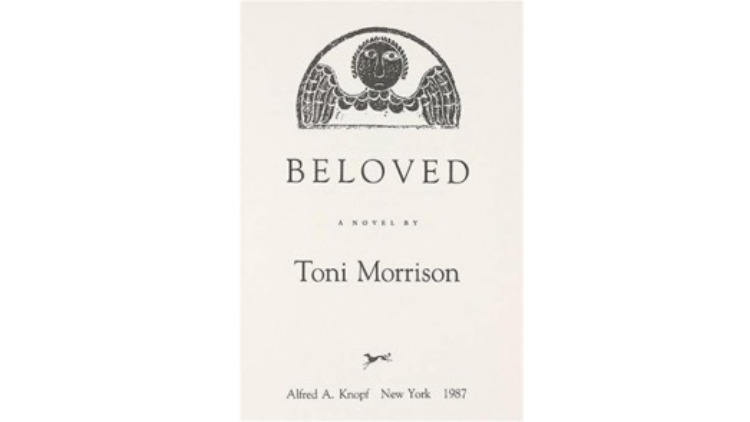
《宠儿》英文版封面
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自相纷争,就如现在一般,如今乔治·W.布什在2004年仅以51%的选票当选美
国总统,剩下的人都没选他,而且其中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激烈反对他及其在八年任期内颁布的政策。这种结构在不同层级的共同特征是一种严格说来不可思议的悖论,一种不合逻辑的逻辑。这种非逻辑的特点是打破内/外的清晰划分。
一方面,南北战争在蓄奴州和自由州,即在南部联盟和北部联邦之间进行。另一方面,正如民间对南北战争的看法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场内部战争,一场“内战”,一场手足相残、父子悖逆的战争,每一方都杀害了自身最珍贵的部分。
在与美国相比的更小范围内,美国当时南方社会本身也自相纷争。南方共同体由白人奴隶主和黑奴的共生关系构成,每一方都在经济和文化上依靠另一方,每一方都与另一方在家里共同存在,都昼夜不停地惧怕彻底陌生的另一方。尽管白人将黑奴带到了美国,但许多人仍视他们(现在也如此)为陌生的存在。
一个例子就是目前“出生地质疑者”广为扩散的阴谋论,他们怀疑巴拉克·奥巴马并非真正出生在美国,没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因为宪法规定竞选美国总统必须是在美国出生的公民。
想象一下南方种植园里白人奴隶主住在宽大房子里的情景,近旁有多达百数的奴隶,包括下地干活和干家务的奴隶在内,都住在奴隶小屋中。这些奴隶主定会终日恐惧,至少会隐约地一直害怕得要命,总是害怕自己被杀死,害怕妻子和女儿被奸污。奴隶同时存在于白人共同体的内部和外部。我们能够理解——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宽恕——奴隶为何会遭受性虐待、鞭笞、折磨、断肢和私刑。这些做法企图驱赶外来者或彻底制服他们,却并不成功,而与此同时,奴隶主每对一个奴隶执行私刑,都毁坏了一部分他们自己的珍贵财产。
在与南方社会相比的更小范围内,黑人“共同体”本身——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也是这样的结构,它为支离破碎的黑人家庭所撕裂,而且对于既定的奴隶群体可能发展出的任何团结一致的情感,都会因其对白人构成威胁而遭到系统性破坏,这也是黑人共同体遭到撕裂的原因。
这种对共同体的刻意破坏,是奴役者、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征服者的常见行为,就如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尽可能地铲除了当地可能存在的任何对部落或宗族的忠诚,为西式民主的“自由”开道。辛辛那提黑人共同体与其自身的关系是《宠儿》的主要议题。

在更低层级上是每个人物与家庭的关系,以及每个人物最终与自己的关系。这最后两种自相似的分形形式都包含了以下这对内外关系,即,整个黑人“共同体”之于那“另一边”看不见的逝者的另一个世界,后者被认为会以实体显现甚至会以暴力的形式侵犯现有世界。
另一边的存在对这些人而言是已知事实,承认这一点对于理解《宠儿》中的黑人共同体的行为至关重要,因此他们要安抚他们所认为的被塞丝杀害的婴儿的鬼魂。这对理解那个共同体中的个人行为也十分关键,比如塞丝做出的“不可能的”决定,割破她女儿的喉咙,以便把她送到另一边的安全之地,同时也扼杀了她本人最美好的那部分。
在类似的意义上,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相信自己会成为神圣的殉道者,死后会过上天堂的美好生活。我们只有在考虑到他们这种信念时,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这也像布什及其幕僚的行为,只有在他们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只有虔诚的基督徒才能获救的语境下才能得到理解。
正如德里达所注意到的,这一点还像技术资本主义体系依赖我们对越来越复杂的机器和软件程序的信念,而非我们对其运作过程的了解。我的邮件无法“发送”时,系统会反馈说,“连接中断因为另一边没有回应”。跟莫里森的黑人共同体类似,网络空间也有这一边和影子、幽灵、幻象般的另一边。
在上述所有层次范围内,这种结构就像身体免疫系统驱赶外来入侵者,然后在我们称为“自免疫”的过程中转而反对自身,我对这个比喻的运用受益于德里达在《信仰与知识》(“Faith and knowledge”)及其他地方的相关精彩论述。然而,我要感谢W.J.T.米切尔(W.J.T.Mitchell)让我认识到这个比喻的奇特之处,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词都是一个比喻的比喻。
这个词完全源自社会政治领域,含有共同体的陌生人或外来入侵者必须被驱逐之意,生物学家借用该词来替身体免疫系统的运作过程和自免疫的灾难后果命名。然后,德里达又借用这些医学术语来描述人类共同体的特征。此处德里达的深刻洞见带有“晚期德里达”所特有的充沛乃至奔放的情感,他声称免疫和自免疫是每个共同体或多或少都有的特征。
德里达说:“我们感到自己有权做出扩展,可以讨论自免疫化的普遍逻辑。今天似乎绝对有必要思考信仰与知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思考普遍根源的双重性。”由此推定,只有通过这种思路,共同体才能被理解。
德里达强调免疫和自免疫的过程在任何共同体中的运作都按部就班,自然而然,无可避免,不容分辩,它并不由共同体中的个人或集体的选择而定。每个共同体都尽力保持自身纯粹、安全、“神圣不可侵犯”,不受外来者玷污。
我们能认可塞丝的做法吗?
首先,我想问,我们是否能同意塞丝谋杀她的女儿,我们是否能认为这种做法是道德的,能为所有人提供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
一方面,我的问题似乎不对。如果自免疫逻辑机械地支配着塞丝的行为,就像乔治·W.布什在任期间,自免疫逻辑同时支配着恐怖分子和反恐人士,支配着那些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使他们有时像梦游者或机器人,麻木地受控于他们所不知道的那些力量,那么我们对塞丝的赞扬或责难就似乎毫无意义。她做这种事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塞丝说她“决定了”。她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无畏地说,“是我干的”。她宣称自己送孩子去安全的另一边既是突发自然的事,也是她有意决定的事:“我带走孩子,把他们放在安全的地方。”尽管社群责备塞丝,但塞丝却从未自责。她认为自己的做法自由自主。
我认为必须从两个角度看待,即从非逻辑的角度和自免疫的非逻辑的逻辑角度看待,后者作为隐喻,实现了两次跨领域使用。尽管在生物体内,免疫系统的运作不是生物自觉自愿,但在这个词来源的社会领域内,在我们需要做出选择时,自免疫行为负责任地或不负责任地做出回应。

为了正确地行事、让孩子摆脱奴隶制,塞丝必须采取错误的行动。她毫不迟疑地决定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另一边,但这个不安的、怨恨的、不愿宽恕的鬼魂回来谴责她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犯下无可挽回之罪,欠下永无止境之债,斥责她违抗了“你不可杀生”这条古老的《圣经》诫命。一个活在奴隶制之中的婴儿与一个安于死亡之域、安于另一边的婴儿,塞丝不可能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却不得不选择,她选择了后者,选择给予孩子死亡的礼物,但她无可避免地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认为我已经表明,阅读《宠儿》可以间接了解那些主导机制,它们在当今这个世界、“恐怖分子”的世界、反恐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网络空间和全球的远程技术军事的资本主义中起作用,在此意义上,阅读《宠儿》是有用的,甚或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么说多少有些让人惊讶。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细读《宠儿》也许甚至比在自毁的自免疫理论视野下直接讨论当前政治更好,就像德里达在《恐怖时代的哲学》和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我的回答是,两种方式都可行,但人们可从细节更具体的小说中看出该理论的小型分形样式。
《宠儿》所表达的自免疫逻辑,具有文学在情感和语义上所特有的丰富性和具体性。这种语言的丰富性将意味着,或者说应该意味着,我们所称的文学,在虚拟空间威胁其存在的情况下,将会或应该继续存在。如济慈所言,以文学的方式表达某种模式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胜过任何抽象的分析——无论那种抽象分析多么有说服力。
在这个感人的故事中,塞丝的生和宠儿的死让读者理解了这种逻辑,但不是将其作为一种抽象的论证,而是带着一种生动的情感特质,正是这种特质让我们更可能做到不仅理解,而且肩负起我们该负的责任,在我们自己的摩利亚山上尽量做到最好。上帝不会让我们任何人只有塞丝的选择,尽管我们有可能一直在以某种方式做这样的选择,选择对某人忠诚,就因而必定选择了背叛另一个不同的人对我们提出的忠诚要求。
正如德里达所说,我们所有人每时每刻都站在某种形式的摩利亚山上,手中的刀或手锯举向我们最爱的、“最好的东西”。
作者丨J.希利斯·米勒
整合丨吴鑫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