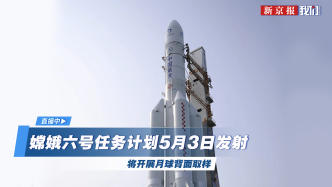近些年,在国际文学版图中,裘帕·拉希莉的名字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甚至,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表示,裘帕·拉希莉是他所钟爱的作家——或许是由于他们俩都是外裔人口,以及在美国社会所遭遇的文化冲突等共同因素。
作为印度裔美国作家,尽管笔下总是出现印度人的身影,然而裘帕·拉希莉出生于伦敦,成长于美国,完全是在西方环境中长大,甚至自己的专业也是文艺复兴方面的研究。但是,凭借着出色的文笔,她年纪轻轻就成为国际上的文学新锐,成为备受瞩目的作家。
2000年,裘帕·拉希莉以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获得普利策文学奖,成为最年轻的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第一部长篇小说《同名人》被改编成电视剧,《陌生的土地》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第二部长篇小说《低地》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英国曼布克奖。此外,她还揽获了诸多如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美国国家人文奖章等多项文学奖。

裘帕·拉希莉
近期,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了裘帕·拉希莉的首部长篇小说《同名人》。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小说讲述的依然是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在文化冲突中去发掘人类活动的精神状态。尽管裘帕·拉希莉的笔下总是出现印度人的身影,但实际上,她生在西方、长在西方,对印度的感性认识,也不过是来自仅有的几次去加尔各答的短暂旅行。在译者卢肖慧看来,由于家庭的影响,东方文明显然在她身上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烙印,这为她提供了更高的立足点、更多的可能性。
在众多对她作品的评价中,总是会见着关于移民文学的字眼:一方面是因为她自身“长在一个印度家庭,讲印度话,吃印度饭,接受印度的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笔下总是出现异乡移民的离散叙事。但在她看来,自己的作品并不能称之为“移民小说”。
在接受《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枕边书栏目的采访时,她曾经对“移民小说”有过这样的评述:“我不知道如何界定所谓的‘移民小说’。作家们总是倾向于描写自己的故乡。碰巧的是,许多出生于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作家,因为个人选择,或者出于客观需求或环境所迫,最终去了另一个地方生活,也因此写下这些经历。如果某些小说能被归类为移民小说,那么剩下的应该叫什么?本土小说?清教徒式小说?我不认同这种分类。从美国历史的角度看,所有的美国小说都可以被称为移民小说。霍桑的作品写到了移民。薇拉·凯瑟也关注移民。自文学的发端起,诗人和作家便不断叙述着穿越边界、游荡、背井离乡,以及与未来的相遇。异乡人本就是史诗和小说的创作原型。异化和同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始终是文学的基本主题。”(《枕边书》,[美]帕梅拉·保罗编,濮丽雅译,浦睿文化丨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版。)
《同名人》是她的首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印度家庭来到美国建立新生活的历史,也是他们在异域走过的心灵历程。通过姓名这个线索,《同名人》讲述了在细流无声的日子里,两代人的爱与孤独,每个人都在经历的寻找与错失。在《同名人》中,她仍旧围绕移民在异国的归属感缺失写作,用一个家庭创建新生活的历史,展现了日常生活中每一个普通人的孤独和爱。
经历生与死、相聚与别离,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故事里的每个人都在两种文化间撕扯、挣扎、逃离与回归,何处才是真正的归宿? 书中人物的生活,永远是不成功之下无可奈何的回返,是一串带有悲剧色彩的回归的足迹。这是潜藏在作者着意描绘的斑斓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之下的生命的脉络。美国固然只是暂时的寄寓之所,而人物的生活道路实际上也远离了他们的精神故乡——印度。那么,何处才是真正的归宿呢?
下文是裘帕·拉希莉《同名人》的译者卢肖慧特别撰写的译者序,该序言并非收录在书中。新京报文化频道获浙江文艺出版社授权刊发。

《同名人》,[美]裘帕·拉希莉著,吴冰青、卢肖慧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版
裘帕·拉希莉:“生在美国的迷茫的印度仔”
作者丨卢肖慧
裘帕·拉希莉祖籍印度加尔各答,1967年出生于伦敦,三岁即随父母移居美国罗得岛州。父亲在罗得岛大学图书馆任职——短篇小说《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即是以她父亲的经历写成的,母亲也拥有孟加拉语文学与戏剧硕士学位。知识家庭的气氛的熏染下,作者从小喜爱写作。作为移民的后代,在成长过程中,她慢慢迷恋上了纽约──那个富有包容力、既充满活力又非常多元化的地方。后来,她来到纽约,就读于伯纳德学院学习英语文学,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不过,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单纯以创作谋生是很不容易的。于是,她前往波士顿大学研究院深造,希望同时在学术界谋求发展。在波士顿大学,她获得了多个学位,包括英语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比较研究三个硕士,以及文艺复兴研究的博士。她曾自嘲说学位“多得可笑”,而父母却是十分看重。她有强烈的艺术创作冲动,却不愿、抑或不敢全副身心地投入,于是做学问就成了一种最好的妥协方式。

裘帕·拉希莉
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问世,并夺得2000年度的普利策小说奖以后,这一切考虑似乎都成为不必要的了。这部小说集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使她一夜间成为美国文学界最耀眼的新星。如今,她早已卸去杂务,专门从事写作了。她在作品《解说疾病的人》中,展露出美妙的才华,刻画了一群游离于古老的印度与令人迷乱的新大陆之间的人物形象。她对文化冲突的把握如此细腻深刻,行文运笔如此沉潜优雅,就一位时年不过32岁的文坛新人而言,是极为难得的。《解说疾病的人》获奖后三年,她一直潜心于首部长篇小说《同名人》的创作。
这部人们满怀期待的小说《同名人》,讲述了美国出生的印度男孩果戈理童年、少年直到青年的人生经历。这是一个印度移民家庭来到美国三十多年建立新生活的历史,也是他们在异域走过的心灵的历程。1960年,年轻的艾修克在前去探望祖父母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游历英国的商人戈什,受到鼓动、感染,远行的神经被隐隐触动了:
戈什摇摇头。“你还年轻,自由啊。”他说,摊开双手以示强调。“别亏待了自己。趁现在还不晚,别犹犹豫豫想得太多,卷起铺盖卷就走,多游历游历。你不会后悔的。到时候就太晚啦。”
不幸,这趟火车随后脱轨倾覆了。戈什死了,艾修克也受了重伤,躺了整整一年才好。这场车祸促使他下决心离开印度,“他想象自己不但能走,还能远行,离开他出生又差一点死掉的地方,离得远远的。”他一生的轨迹由此彻底改变。他来到美国留学,以自己的才智和努力,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获得了大学教职,获得了新大陆的认可。他从印度娶来了仅仅见过一面的阿西玛为妻。这对移民夫妻在异乡别国,细细碎碎地编织起一幅平平常常的白手起家的生活图景。
这幅图画里,开始是令人不愉快的油腻腻的厨房餐具和铺着脏乎乎黄白格子纸的橱柜,渐渐地,添进了从“庭院甩卖”买得的二手旧家具,添进了日本制造的丰田花冠轿车,添进了带花园带车库安装了报警系统的中产阶级小洋房,添进了同是生活在他乡的孟加拉邦朋友,添进了孟加拉话语、孟加拉菜肴,添进了对故国对亲人忧伤的思念,特别是,添进了美国出生而有着俄国名字、印度父母的小说主人公男孩果戈理的粉红小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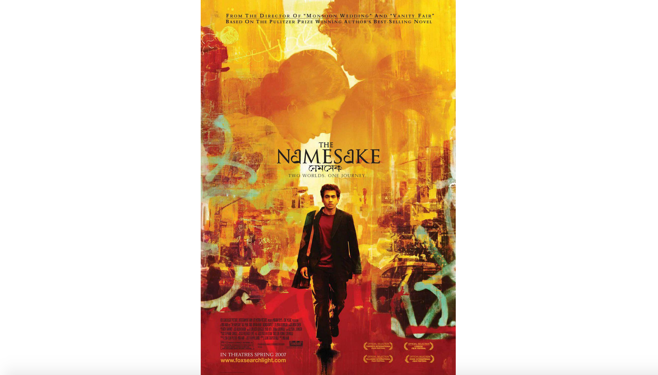
《同名人》电影海报
果戈理聪慧努力,不招惹是非,有着印度移民孩子勤勉的长处。然而,他同时也具有叛逆性,不愿听从父母的安排,还背地里吸过大麻,有着美国孩子的个性。从小时在后院玩泥巴,到中学里为名字伤脑筋,从求学于耶鲁和哥伦比亚,到成为颇有抱负的年轻建筑设计师、结识纽约上层家庭的女友,从与同样背景的毛舒米结婚,到最终离婚而内心孤独尝到人生无奈:主人公一生的经历,都伴随着微妙的矛盾张力;而这一切发生的舞台,乃是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处,是传统与现代化消长起伏的争斗之所。
作者不动声色地把主人公推到了这样的特殊环境,叙说着细流无声的日子里并不平静的故事,叙说着他的喜忧、他的沉浮,他对印度文化的内心反叛,他对美国文化的矛盾挣扎,他的爱情和爱的破灭,他的失败落寞,他寻找心灵慰藉的努力。这幅由主人公父母辛勤编织的热闹图景,临到末了,画中人物一个个一件件慢慢地消匿:父亲离开了人世,母亲回去了印度,妻子也背弃了他,房子变卖了,家具送的送、扔的扔,母亲电话簿上从不忍划掉的名字也都不复存在了。小说结尾处,历经迷茫困顿的果戈理,又一次回到小时候住过的屋子里,与作家果戈理开始了心灵的交谈。
如果说,关于“我是谁”的问题,只是哲学思考的永恒主题的话;那么,对于生活在异乡的人们来说,这早已成了切身的现实问题。因为身份认同(identity)的依据乃是文化,在多种文化并存的环境中,人们不但觉得新奇有趣,更是常常深感迷茫。在小说中,作者着力揭示了这个问题。那是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人们一方面努力适应新的环境以求生存,一方面又免不了要寻根问祖、思旧怀乡。
即使是移民的后代,文化的归宿感也常是模糊的、双重的,拉锯似地取舍不定,而一旦两方出现矛盾冲突,这种不稳定状态就可变得富有悲剧意味。名字是一个人文化身份的象征,作者特意安排主人公名字的故事贯穿小说的始终。主人公出生时,阴差阳错取了“果戈理”的名字,于是他的身份的“分裂”便有了具体的依托,书中很多故事都围绕着名字来生发。
小说中安排了一个隐喻,是一幅十分艺术性的意象:象征果戈理真实身份的,是他的外曾祖母──代表了古老的印度文明──为他起的名字。不幸的是,这个名字在邮寄途中丢失了,它从未到达剑桥,而是在印度和美国之间漂荡,永无定所。这,原本就是果戈理未来的命运:他没有归宿。他将长久地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不知道该接受哪一个,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究竟属于哪一边。可以说,主人公所体味到的文化归宿感的缺失,是或隐或现弥漫全书的基调。

《同名人》电影剧照
作者以女性细腻的笔触,真切地描绘了这两代人在异质文化氛围中的感受和反应。艾修克夫妇生长在印度,他们的自我定位是孟加拉人,他们的文化归宿是印度。他们一直保留着印度的语言、饮食、宗教,一切的生活方式,不肯轻易放弃;果戈理的母亲阿西玛丧夫后,更是要回印度长期居住。然而,他们毕竟从那个拥有古老文明和丰富历史传承的民族躯体上剥离了下来,他们心灵的历程,必然是深沉的孤寂和无依。对此,阿西玛有着最为深切的感受,她深感生活在异国他乡是“某种终生未了的妊娠──一种永无休止的等待,一种无法摆脱的负担,一种长相伴随的郁闷”。
印度辉煌的古代文明,深厚的伦理、宗教、历史、饮食、服饰等等的传承,构成了艾修克和阿西玛内心沉重的负累,其沉淀越是厚重,越是割舍不断,对美国文化便越难认同。于是,他们只能漂游于印度和美国之间,成了无根之萍,成了真正的孤儿。为了慰藉思乡思家之情,他们唯一可做的一点可怜的事情,便是每隔一年举家回一趟加尔各答省亲。那绝不是为了休养劳顿的身心,而“是一种义务的履行,促使他的父母回去的首先是一种责任感”,一种面对自我内心的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们因为自我放逐而产生的亏负和罪疚,达到内心的平和。
果戈理出生在美国,没有父母的文化负累,然而他并不轻松,因为一开始就身处两大阵营的夹缝之间,是所谓边缘化的ABCD──“生在美国的迷茫的印度仔”。他希望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可是家庭的影响早已深植于他的血液里。他的叛逆性,滋长于不知何去何从的矛盾之中,而这种叛逆性又并不彻底。他不愿延续父母的印度式生活方式,于是结交美国女友,出入纽约上层家庭;可是,他骨子里还是打上了印度传统的印记,父亲的猝然辞世使他意识到,原来他与美国女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而唯一的结局只能是与女友分手,离开那个代表美国文化的家庭了。他的内心充满矛盾,而外在的行为摇摆不定,这是“抉择”之难。因为一作抉择,便意味着舍弃。

《同名人》电影剧照
那匹站在两堆同样的稻草前的布里丹之驴,到底该如何弃取呢?面临这样的困境,果戈理和妻子毛舒米采取了迥乎不同的态度:他固然反叛印度文化,却没有豁出去的勇气,还想两者兼顾;而她的选择,却是另一种典型,即决然的逃遁,“沉湎在第三国语言、第三种文化里,那成了她的避难所。”她把印度和美国一起抛弃,游移到法国去找寻自己的归依去了。然而,无论做出怎样的抉择,既已身处这样的困境,命运的悲剧性就都是无法避免的了。
作者笔下的人生际遇,是一连串“突兀而无法预料、没有筹划的偶然”,是扑朔而无法预料的。艾修克车祸的故事,直接脱胎于作者父亲一位族兄的真实经历。书页攥成的纸团从手中跌落的那一闪的白光,竟就这样决定了艾修克未来的一生,决定了他的远游、他在异乡的艰辛、他对故土的牵挂。果戈理得到这个名字,也仅仅是因为一封信的丢失,此后这名字便“那么久长地塑造着他、折磨着他”了。他与毛舒米婚姻的终结,也是导引于不可思议的偶然:系里的行政助理在分发信件时突然死去,而喜欢收拾整理的毛舒米替她分完,无意中居然发现了少女时代偶遇的德米特利的求职书,随后事情便不可收拾了。似乎这是一切生命的共同特征:决定人生之路的,不外乎有限的几个偶然瞬间而已。
然而,这些偶然瞬间编织成的生命历程,却并不偶然地都带着悲剧色彩。那也许是生命的本质吧:从无到有,虽历经繁盛,却终将重归于无。“在这个国家,他的躯体不会占据任何土地,也不会有一块刻着他名字的石头的。”果戈理十一岁时,一次来到墓地野外考察,竟生出如此悲凉的想法。与充满孩子似朝气的新大陆不同,古老的文明就像垂垂老者,对生死命运的问题探究得更深入。按他们的习俗,艾修克死后,不但人要火葬,甚至生前的用具都不要留下来。于是,他的生命仿佛被彻底抹去了一般,只在生者的记忆里留下依稀的影子,没有了实物的证明。
他们一家三十年的生活也经历同样的兴盛与衰败。起初仿佛是一张白纸,慢慢有了人物,有了色彩,灵动起来,而这一切却似乎注定要被某种力量拂拭了去,无可奈何地,最后又回到了白纸一张,也许多的只是一抹暗影罢了。生命的悲剧色彩还在于无奈,不管作了什么样的努力,却事事终难遂人愿。一直想重新塑造自己的果戈理,为了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又是改名字,又是疏离父母,又是结交美国女友。然而,他惨淡的努力终究还是归于失败了。
在果戈理和毛舒米婚姻破裂的前夕,作者写道,“他从书本上抬起头,看看天空,天色正逐渐暗淡下去,云霞浓烈而瑰丽,金光流溢;他四周鸽群盘旋,飞得离他近得骇人,他不得不时时停下脚步。他突然觉得惊惧,缩起了脑袋,事后又觉得自己很荒唐……鸟群箭似地倏忽振翅而起,又齐齐地滑落在比邻的秃树枝丫间。这景象使他不安。他屡屡见到这不讨人喜欢的鸟儿栖息在窗台上,在人行道旁,可还没见过它们站上了树枝。”好一派无助、落魄的凄凉气氛,无奈若此,真可谓“鸟惊心”了。作者笔下的生命,更是充满罪疚感的。

《同名人》电影剧照
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艾修克一家抛下了印度的一切;这似乎本身就是一种背叛,构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大的罪疚,是一道枷锁。这道枷锁夺去他们心灵的自由,而对解脱和自由的无望的渴求浸透了他们的生命,令人暗生怜悯之情。果戈理无时不受名字的折磨,他要改掉它,获得解脱。不幸这解脱本身又增添新的罪疚。好不容易改换了名字,然而得知它的来历──原来是在“诉说着一场灾难”──以后,他又觉得辜负了父亲,转而羞惭不已,一种对父亲的负罪感油然而生。小说充满了这样的无奈和不如意,读者在不自觉中跟随作者,前去面对了。
与当前许多描写移民经历的小说不同,拉希莉并没有为她的小说安排奇崛曲折的情节,书中看不到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看不到不同寻常的大悲大喜。她只是以最直接最自然的方式,以沉静而略带忧伤的笔触,叙写主人公平凡一如常人的生活。她以自然主义的风格,从客观叙事者的角度娓娓道来,故事的场面犹如精细的白描,一笔一划之间,一种气氛隐隐然营造了出来。小说中大量的细节,便无一不和谐地统一起来,无一不在反映着两种文化的差异对人物命运的影响。
在她的短篇小说中,尚有为表现人物内心苦痛的核心主题而设的戏剧性场面,而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这样的戏剧性场面已几乎看不到,她更倾向于采用寓言式的隐喻来表达对人生的看法。作者以天真质朴的眼光观察,以优雅平实的语言叙述,这样的真诚,让人不由想起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们来。
作者的短篇小说,颇有契诃夫的味道,而在这部长篇中,她引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里出来的。”──人物的命运固然如《外套》里的阿卡基一样卑微无奈,而作者的写作何尝不也是受其影响。小说的风格是冷静而客观的,正如作者所言,她只是展示矛盾,不做价值判断,也不寻求解决。小说有着浓郁的散文风味,不以情节取胜,而以感觉见长。我们阅读这部作品,像是口含一只橄榄,似乎是平平淡淡的,而味道却在一丝丝慢慢透出。
作者的创作态度一丝不苟,极其谨严,应是得益于她曾接受的学术研究的严格训练。凡书中涉及的关于新英格兰地区的风物、遗迹的细节,以及三十几年跨度之中的事件、人物,无不一一考察,都是完全真实的。作者笔下的世界可说是现实的精细翻版,她像一个摄影家,捕捉到了大量真实而不散乱的细节。
在虚构的细节上,作者也是十分讲究的,比如果戈理初会毛舒米时,见这位研究福楼拜的学者的头发“梳拢在后面的发髻里”,而这正是奢淫的包法利夫人最爱的发式,作者在这里便早早地暗示了毛舒米的不忠。这样的写法,把读者引领入完全真实的文化场景之中,给予了他们极大的体验和领会的空间。
总之,这是一部真挚感人而又精巧细腻的作品,是作者继《解说疾病的人》之后又一部十分成功的创作。《纽约时报》的书评说,“拉希莉女士……采取短篇小说集中难以忘怀的室内乐素材,重新谱写了自我放逐和文化认同的主题,成就了一部交响作品。”诚然。
作者丨卢肖慧
导语丨吴鑫
编辑丨徐悦东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