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葛格
在#MeToo运动余波未散的当下,本届威尼斯参展影片《我控诉》(J'accuse)的处境有些微妙。该片改编自法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讲述了在反犹主义浪潮下被栽赃入狱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A. Dreyfus),在关键人物皮卡尔上校(G. Picquart)的努力下,历经两次不公正的审判,终于在入狱12年后被无罪释放的故事。

《我控诉》电影剧照。
罗曼·波兰斯基对于德雷福斯事件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希望将这起法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案件改编为电影。此前,英国作家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曾与波兰斯基合作过电影《影子写手》(The Ghost Writer)。在得知波兰斯基希望拍摄德雷福斯事件后,二人再次携手合作。《我控诉》脱胎于哈里斯于2013年出版的小说《军官和间谍》(An Officer and A Spy)。在历经种种波折后,该片终于在去年开拍,并在今年威尼斯电影节上亮相。
性侵丑闻是波兰斯基身上无法抹去的阴影,因为那起发生在1977年的性侵案,波兰斯基仍然是美国法律体系中的逃犯。#MeToo运动的兴起,也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他的抵制。
波兰斯基并没有正面回答是否试图用这部影片,在#MeToo运动的讨伐声中为自己辩解,但他认为,自己的处境和德雷福斯有着相似之处。作为反犹主义思潮中的著名案例,德雷福斯事件在今日仍然值得人们反思。
《我控诉》与德雷福斯事件
1894年12月,法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因一张出现在德国驻法大使馆的告密字条,而被真凶诬告为向德国传递军事情报的间谍。时值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反犹主义早已日渐抬头。1886年,爱德华·德吕蒙(Édouard Drumont)出版的《犹太法国》(La France juive)畅销法国。在他主导的《言论自由报》上还曾发表文章,将为报国而从军的犹太军官歪曲成借机“成为法国的主人”、“聪明地抢夺大饼”的投机分子,大肆煽动恐慌。
德雷福斯出身于阿尔萨斯地区的犹太家庭,自幼受到普法战争的影响,立志从军。18岁时德雷福斯进入巴黎的精英军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表现优异,毕业后一路晋升。然而,随着犹太人逐渐成为众矢之的,在德雷福斯进入参谋部工作之前,就有上级因为他的犹太身份,对他做出了负面评价。虽然德雷福斯最终还是进入了参谋部,并成为当时唯一的犹太军官,但随着反犹主义思潮的深化,同僚对他愈发偏见,他在参谋部得到的人事评价也越来越差。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尽管德雷福斯在这起间谍案中完全无辜,但他的身份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非常适合被拿来做替罪羊。参与调查的军官一致认定,字条上的笔迹和德雷福斯的字迹相同,虽然仅仅只是类似,甚至有几处差异,而且字条上的信息与德雷福斯当时的实际状况也对不上,这张字条作为指控德雷福斯的唯一证据,还存在许多漏洞。但军队上下先入为主的判断和精心的构陷,依旧指控德雷福斯为向德国传递情报的间谍,把这个不受欢迎的犹太军官推到了军事法庭上。法官们秘密审理此案,并在三天后做出有罪判决。德雷福斯被当众剥夺军衔,斩断佩剑,作为重犯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外海上的恶魔岛上服刑。
事件的转折,发生在1896年。法国军情处的新主管皮卡尔上校在秘密侦查中,发现当年德雷福斯事件的真凶应是另一名军官埃斯特哈齐(Esterhazy)。但是,军方为了维护声誉,立即将皮卡尔远调至突尼斯,以此隐瞒真相。此事被媒体公开后,立即掀起轩然大波,社会上出现了两个相对立的阵营。
在支持德雷福斯的一方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小说家左拉(Émile Zola)。1898年1月13日,他在巴黎《震旦报》上公开发表致总统弗朗索瓦·菲利·福尔(Francois Félix Faure)的公开信,这封信被该报主编克雷孟梭(G. Clemenceau)冠以标题“我控诉!”,自此成为名篇。不料,左拉随后便遭到攻击,被军方判处诽谤罪,不得不流亡英国,并继续为德雷福斯发声。

《我控诉》原文。
真凶埃斯特哈齐于1898年秘密受审,但被判无罪,他随后逃出法国。1899年,新上任的总统埃米勒·弗朗索瓦·卢贝(Émile François Loubet)要求重新审理德雷福斯的案件,但法庭仍然判处德雷福斯有罪,但总统对他发出特赦并释放。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免罪并恢复军阶,整个事件在12年后才终于结束,从政府、军队到师生、平民,法国社会从上至下全都卷入这起事件。时至今日,德雷福斯事件仍然不断提醒人们警惕极端的民族主义对正义的歪曲。
知识界的激辩与反思
德雷福斯事件将19世纪末的法国社会撕裂成两个阵营。反对的一方主要由保守的右翼分子、反犹人士、天主教人士组成,支持的一方则由共和派的资产阶级、知识界人士以及新教徒构成。双方都以爱国为前提,反对的一方坚持认为德雷福斯作为叛国者,应该遭到严厉的处罚,为了军队和国家的名声和荣誉,也不应该重新审理案件。而支持德雷福斯的阵营则呼吁法庭重新公正地判决,维护德雷福斯的平等权利和社会的公正。在这场席卷全社会的辩论中,双方人马都在代表己方利益的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互打笔仗,通过舆论来争取实现自己的诉求。

乔治·克雷孟梭
在左拉发表大量文章及后来的公开信之后,支持德雷福斯的一方迅速壮大起来,例如普鲁斯特、涂尔干和莫奈都加入了声援德雷福斯的队伍。克雷孟梭首次在法国使用“知识分子”一词来统称这些参与社会公共讨论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等。但不同的立场使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法国社会中发生分化,是一场法国人的精神内战。
德雷福斯事件也成了当时法国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例如普鲁斯特便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穿插了这起事件。而反对将国家利益凌驾于真相之上、为德雷福斯积极奔走的涂尔干更是从这起事件中获得启发。在他看来,德雷福斯事件的爆发不仅是反犹主义发展的结果,也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面临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同样是一个征兆。
1942年,汉娜·阿伦特发表文章,专门论述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国社会的影响。之后,在其重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再次谈到这起事件,认为德雷福斯事件不过是后来发生种种的预演,是法国政治的试金石。在她看来,法国社会在事件后走向衰落,正是因为不再有真正支持德雷福斯的人,几乎没有人还在为共和、民主、正义奔走,就像左拉当年那样。

《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而在当今的法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对于移民潮的恐惧和随之而来的极端右翼势力抬头,作为前车之鉴的德雷福斯事件再次对人们敲响警钟。
波兰斯基并非无辜,
也不是德雷福斯
波兰斯基现在住在法国。1978年,他被指控于1977年3月在洛杉矶郊外的好莱坞诱奸了13的岁少女萨曼塔·盖默,在终审判决前夜,波兰斯基逃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去过。
在《我控诉》首映当日,波兰斯基没有出席任何现场活动,而是接受了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的采访。布鲁克纳是法国知名学者、小说家。此前,波兰斯基曾将布鲁克纳的小说《苦月亮》(Lunes de fiel)搬上银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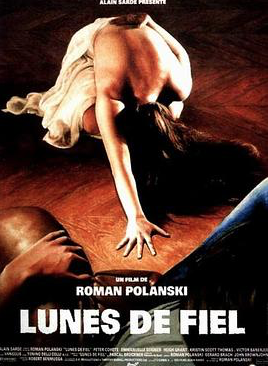
《苦月亮》,1992。
在对话中,较之在反犹主义浪潮下蒙冤的德雷福斯,布鲁克纳将波兰斯基的处境形容为“来自新麦卡锡式女权主义(neo-feminist McCarthyism)的指控”。但当被问到,是否想要还击那些在他看来无端的指控时,波兰斯基认为这么做毫无意义。
当然,波兰斯基无法抹去自己犯下的性侵罪责。
当年,他没有与法官达成辩诉交易,逃往欧洲,至今仍被美国追捕。但在当年的受审过程中,美国媒体大肆渲染他的犹太身份和发生在前妻身上的谋杀血案,这些过往经历或许让波兰斯基对发生在德雷福斯身上的事情产生了共鸣。他曾经形容自己在那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像是一只老鼠,被猫当作玩物盘弄,而主审法官则是那个滥用正义的人。

在昆汀新片《好莱坞往事》中扮演波兰斯基前妻莎郎·泰特的玛格特·罗比。该片对那起血案进行了改编。
在2012年的报道中,波兰斯基曾谈到,今天发生在针对少数人群当中的“猎巫”行动、秘密的军事审判、失控的情报组织、政府的掩盖和偏激的媒体报道,正是对当年德雷福斯事件的重演。他也曾将#MeToo运动形容为一场“不时发生在社会中的集体癔症”,就像曾经发生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运动一样。而对这场运动表示支持的人,不过是出于恐惧而表达出的一种“伪善”。
哈里斯在当年小说出版后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将德雷福斯事件和波兰斯基的案件相提并论,对于性侵案的受害者们来说的确是一种冒犯,毕竟波兰斯基确实并非完全无辜。
然而,这两起事件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舆论在不完全了解实情时,便以各自的立场群起攻之,拒绝审视案件中具体的法律问题。
尽管四十余年前那起案件中的受害者萨曼塔·盖默,已经公开原谅了波兰斯基。并且,在身为导演的波兰斯基看来,他已认罪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然而,在#MeToo运动的呼声中,波兰斯基仍然是被口诛笔伐的对象,他被美国电影学会除名,时常遭到女性团体的抗议,依旧是个逃犯。
波兰斯基和无辜的德雷福斯并不相同,更不能对比。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德雷福斯事件在当今社会再次重演保持警惕。
作者 | 葛格
编辑 | 张婷
校对 |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