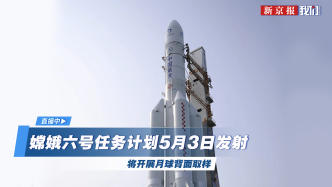在高中时,作家马鸣谦读了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敦煌》,当时就诧异于为何中国没有同类型题材的创作。多年后,当马鸣谦成为一位写作者,这种“耻感”仍是隐秘的写作动机之一:“文学创作的经验来源,不能只来自当下现实和日常生活,其实可书写的经验是很宽广且多向度的。”他于2019年出版的《降魔变》,延续他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并将写作背景放置于近年来渐成热点的敦煌。
《降魔变》来源于敦煌壁画,讲述的是释迦摩尼降魔成道的故事。“变”意指铺衍故事,马鸣谦在小说中延纳了这层意思,并融入了对敦煌壁画背后的人们的想象。小说从敦煌当地归义军建立,张氏兄弟重新恢复汉人为主的政权、敦煌重新划入大唐的疆域之内开始,讲述了唐末归义军争斗的历史悲剧,故事在外部政治压力和内部家庭冲突的双重结构中展开。
《降魔变》是马鸣谦“佛教三部曲”的第三部,入选了2019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榜120本入围书单。推荐语称:“中国悠久的历史脉络中,隐藏着太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对于小说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宝藏。从鲁迅的《故事新编》到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写作风格不同,故事中的历史感却一样迷人。马鸣谦延续这一脉络写就历史小说《降魔变》,以带有古雅气息的文字、多变的叙述视角,讲述了唐末归义军的争斗、消亡史。”
事实上,关于敦煌的历史研究与影视已有不少,但在本土文学领域,《降魔变》却少有涉足敦煌的历史写作。历史小说写作的难点在哪儿?如何看待关于敦煌的文学书写?如何看待历史小说的书写传统?历史小说还有哪些可以开拓的空间与尝试?
12月28日,新京报·文化客厅第二十六场联合中信出版·大方、中信书店·启皓店,邀请《降魔变》的作者马鸣谦,作家张柠,以及主持人、书评周刊记者董牧孜围绕以上问题进行了对谈。

为什么敦煌成为文学想象的对象?
张柠认为,敦煌进入中国人的想象,得益于外国人,是外国人刺激了中国人对敦煌的想象。“敦煌学”是国际显学。外国的探险家、地理地质专家、考古学家认为敦煌有“宝藏”,因此到处勘探、绘图,购买文书、器皿,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博物馆里藏有很多这样的“废物”。对于“敦煌学”而言,“大师”都在国外,“中国人原本见怪不怪,历史太悠久了,满地都是文物,有什么好想象的?”
近几十年,中国也开始研究敦煌,但多数研究者集中在社科院、兰州大学、故宫等地方。“一带一路”提出来后,敦煌更是成为一个热点。而当敦煌成为全世界的想象对象,它很自然地就会进入文学创作的视野。
然而,对敦煌的文学创作不是历史本身,它是对历史应该如此的想象方式。张柠认为,历史是一大堆碎片,历史学家试图呈现它,为我们讲述这些碎片联系在一起是什么故事,告诉我们敦煌应该是什么样子。但他们的研究不能穷尽敦煌的全部,这个“全部”到底是什么?这就给文学想象留下了空间,文学想象是对“确实如此”的重要补充。施蛰存曾根据《高僧传》里的《鸠摩罗什传》创作一个与西域有关的历史小说《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传》只有几千字,而施蛰存的《鸠摩罗什》有两万多字,这就是作家想象力的结果。

活动现场
马鸣谦认为,从中国古代遗存的很多文物、图像、文字、文书来讲,敦煌的发现是个特异存在。通常,我们是从《新唐书》《旧唐书》《明实录》《清实录》等官修史书来了解古代历史,而敦煌的价值在于,这里发现的很多文书是由僧人保存的,它们不是官修史书,有些文书一面是图像,另一面是文字。
这也提示我们:在中国古代史当中,敦煌的图像文书很特殊,很多古人的活动痕迹都保留在这上面。如果我们更了解敦煌,就会发现很多具体的、个人的材料,其中记录了很多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和工作的痕迹,而这些个人化的文书记录正是他最感兴趣的,他尽量抓取这些记录。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这些密集而丰富的个人化材料,是一个宝库。
对话马鸣谦视频:为什么敦煌会成为文学想象的对象?
“新历史小说”究竟“新”在何处?
马鸣谦谈到,想象力是任何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但历史题材的文学写作正是从这些有关敦煌的历史材料开始的。在开始写作之前,他花了大量时间研读敦煌学各方面的史料,从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到冯培红的《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等史学著作。在学者研究基础上,马鸣谦做了大事年表,囊括饮食、风俗等古代人的生活方式,他希望借此厘清人物的位置与面貌,并想象与描摹出古代人是如何生活的。“如果只是很面具化地描摹,我作为写作者是很不满足的,我想让他们通过文字获得具体的生命感和生活感。”
当然,光有材料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很多文学的技法与手段。马鸣谦表示他花大量时间来面对这些材料,思考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他并不在乎悲剧有多残酷多惨烈,他想探究悲剧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演化,包括张氏的权力是怎么过渡到曹家身上,震动敦煌的这个大事件又是怎样归于风平浪静。
马鸣谦认为,要理解历史当中的人物,必须了解其内心。在写作《降魔变》之前,他再次通读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以寻找在结构上可以化用的东西,他不想做过于线性的叙述与表达,因此,《降魔变》采用四幕剧的结构,还进行了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的变化。
张柠则认为,在历史材料的运用上,应该以敦煌为点辐射开,不仅可以利用敦煌文书,凡是跟丝绸之路、西域相关的材料都可以用。写小说需要细节,衣食住行和流行文化的书写都要符合历史真实,不能瞎编杜撰,而历史学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材料和细节。当然,在写作时,也不能直接将碎片和细节呈现给读者,应该将其串联为一个整体,这体现了作家的思维水平。

《降魔变》,马鸣谦著,大方丨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版
张柠谈到,历史主义的小说有很多,而《三国演义》这种古典的历史小说和我们讨论的“新历史小说”并不相同,古典的历史小说以正史为基础,它的价值观与正史相通,只不过在正史疏漏的地方塞进一些材料而已。比如刘邦把女人比作衬衫这个是历史小说家的想象,但他对历史总体的价值系统、价值观跟正史是一样的。而 “新历史小说”是颠覆我们的历史价值观的,它书写被历史删除、遗忘的人,它的价值观是被历史删除的价值观,新历史小说希望以此重构对历史的理解。
对话张柠视频:中国新生代作家的碎片化美学书写
历史小说书写传统中
有哪些可以开拓的空间和尝试?
从鲁迅的《故事新编》到王小波的《红拂夜奔》,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上文脉相续。对于历史小说书写传统,张柠谈到,每一个时代的作家所创作的历史故事,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强烈印记。比如鲁迅的作品都带有讽刺,他的目的是重新复活一个人性的故事,一个爱的故事。而王小波的创作观与张柠很接近,王小波的小说不是类型小说,而是严肃文学,充满对人的思考。
马鸣谦则认为,王小波的几部历史小说都写得很精彩,但他那种张扬恣肆、充满表现力的语言风格很难撑完一部长篇。每一个写作命题都会命定地让写作者去寻找一种稳妥、准确的语言,王小波的语言有很多现代小说的反讽和夸饰成分,而《降魔变》要表达一个戏剧性的悲剧事件,因此王小波的叙述方式并不适合《降魔变》。
马鸣谦谈到,他也看到现在有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包括网文,但要区分写作的态度,《降魔变》不是类型小说。他希望对历史材料进行精深地研读,再腾空而起进行小说的写作。如果一部作品大部分是靠想象、空想,那就不能称之为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应该是一个很严谨的题材。

根据马伯庸历史题材小说《长安十二时辰》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剧照。
马鸣谦还谈到他对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期待,一是类型文学上的,他希望马伯庸以及很多年轻作者都可以做更多探索,无论是采用现代小说的写法,更强调文学性,还是更类型化,更偏向故事完成度和读者感受的写作。他谈到,很多现当代的日本一线作家一直在利用中国历史题材进行创作,包括类型文学或更偏向于严肃文学的作品。
作者丨聂丽平
编辑丨吕婉婷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