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沈卫荣
我是1月21日晚上才从北京飞往美国探亲、过春节的,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上网就发现国内疫情告急、形势急转直下,从此这个假期就不能是假期了。连时差也不用调了,反正寝食难安,除了刷微信,从各种朋友圈看各种各样关于疫情、关于武汉的消息之外,其他一切事情都无足轻重了。
1月26日又传出科比意外去世的消息,悲痛难遏,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不算是科比的粉丝,当年看球时始终只支持和他对立的球队,总希望有人能打败他。以前我看不惯他“老子天下第一”的那副样子,现在想来自己心里早已承认他就是天下第一了。想起Elton John的那首歌《风中的蜡烛》,生命何其脆弱,连如此不可一世的科比竟也会在盛年中像风中的一支蜡烛就这样被吹灭了。

沈卫荣,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中文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西域语文、历史,特别是西藏历史、藏传佛教和汉藏佛学的比较研究。近著有《大元史与新清史》《回归语文学》等。
回到家等待我的是可以装满一个大箱子的新书。每个假期回家前,我都习惯在亚马逊上买一批新书,供假期随心所欲地翻阅。这次年终竟有余钱,买了格外多的书。但第二天我就把它们全部装箱了,至今没有打开。疫情汹汹,哪里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要不是疫情,现在应该是结束假期,启程返校的日子了。可说来惭愧,我没看一本新书。不停地刷微信之间,我读的唯一的书是家里所藏的陈寅恪的著作。这些书以前都曾读过,重新翻读,体会大不一样。
年前我受邀参加了两场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活动,讲我眼中的陈寅恪和他的学问。我总觉得眼下很多人谈陈寅恪都不过是在表达他们自己,陈寅恪不过是一个象征符号,别人把对一位理想型的知识分子的学问、情怀和气节的所有期待都寄托在他身上了。我怕自己也是如此,为了倡导人文学术要回归语文学,就说陈寅恪是一位语文学家而不是思想家。这次我在假期中重读他的书,特别是他归国后前十年间的著作,就是想用语文学的方法和态度来仔细品味他的作品和学问。除了要确信我说陈寅恪是语文学家的观点没错之外,还想能更好地领会他的学问到底好在哪里?他的学问在当时国际、国内学术背境中究竟处在哪个位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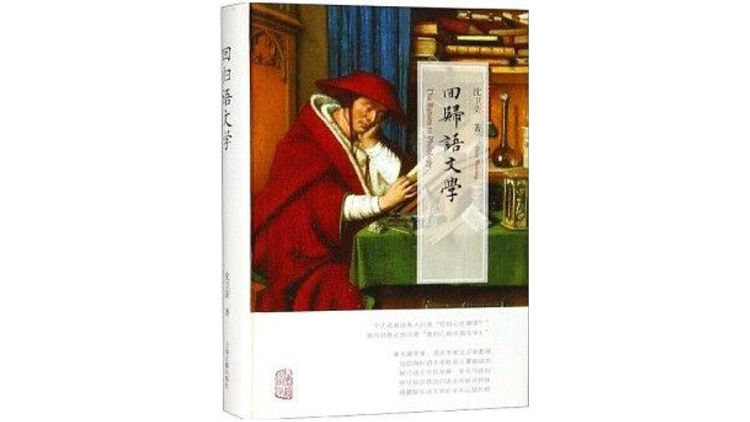
《回归语文学》,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版
至今我重读完了陈寅恪发表于1927至1937年间的所有学术论文,对陈寅恪是一位优秀语文学家的事实深信不疑。我认为,尽管他在海外受的都是梵文/印度学和中亚(西域)语文学的训练,但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他的学问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兼擅汉学和“虏学”,并以“虏学”助攻汉学,超越了只擅其中之一的乾嘉诸老或者西方汉学大家。他擅以语文学的方法读透汉语文本,用他丰富的知识积累,来语境化和历史化文本,从中探寻文学实相和历史真实。
我甚至觉得他倡导的“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说的实际上就是一种语文学的立场和态度。人文学术研究必须是语文学的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才是理性的和科学的,才能摆脱神学(宗教)、哲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束缚,人文学者和其学术实践才能有独立和自由。我也更加怀疑他所说的平生只做“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并没有很多思想史上的意义,它只是一种相当高调、自信的学术宣言,不古不今、不中不西背后的意思是亦古亦今、亦中亦西。陈寅恪曾自称“平生治学,不敢逐队随人,而为牛后,”所以,只有“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才能开风气之先,且独领风骚。他这样的学术自信,确实比我们今天号召的要与国际学术接轨有底气、有创意的多。
至今我只是挑选了陈寅恪著作中我能读得懂的部分读了,我的感觉是他于“虏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的国际学术背景下是预流的,但不是不可超越的。对于我这样不通汉学的人来说,他著作中表现出的他于汉学方面的造诣反而是我无法企及的。新学期我在清华要给本科生上一门题为《语文学和现代人文科学》的课,我准备把“陈寅恪与语文学”这个题目作为这门课的第一讲。虽然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明白为何当年没有洋学位、也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的陈寅恪竟能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还被奉为是大师云集的清华园中的“教授之教授”,但是谈陈寅恪与语文学无疑是有益于理解清华人文学科的传统的。
希望疫情很快就能过去,我能够如期重返清华课堂,和同学们一起讨论陈寅恪和语文学。
撰文丨沈卫荣
编辑丨李永博 张进
校对丨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