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阿唐
几年前尝试写作,朋友劝我离开沈阳,说投身到更广袤的世界才能实现自我,才能下笔有神。直至《冬泳》出版,我告诉朋友,班宇班老师就住在沈阳,劝我离沈的建议才渐渐止息。
是的,班宇至今仍留在沈阳,就住在铁西区,这使得班宇与其他书写故乡的作家不同。鲁迅虚构的鲁镇,沈从文眷恋的湘西,莫言魔幻的高密……故乡与其说是写作的缘起,不如说是作者重构的文化意象,这些意象与其思想一以贯之。故乡是漂泊者的虚构,对童年故乡的叙事体现的是作者当下的心境和旨趣。沈阳对班宇而言,更像是卡夫卡的布拉格与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并未直接书写城市,笔触却始终笼罩在城市梦魇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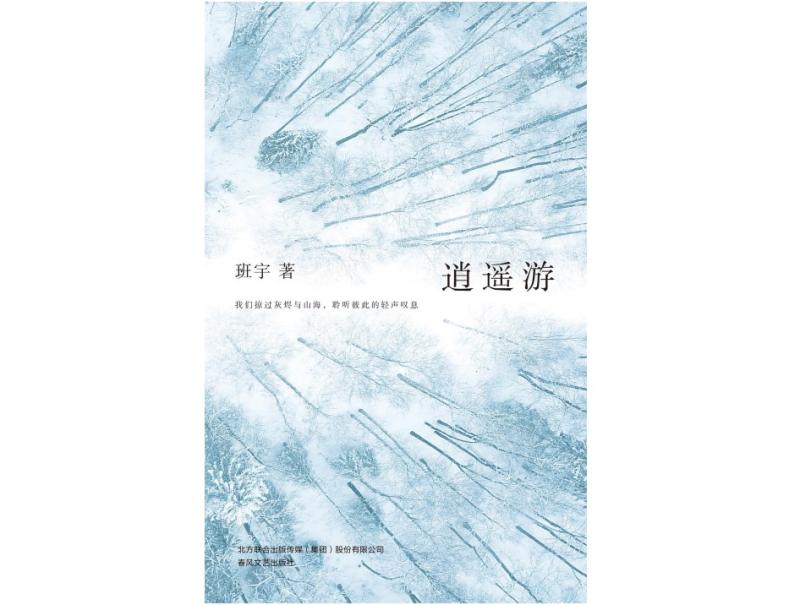
《逍遥游》,班宇著,理想国|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
《逍遥游》出版的时候,我在沈阳已经生活了十年,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提到东北,耳边听到的仍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许多科技项目就在这样的宣导下产生和实现。在辽宁,人们仍活在共和国长子的梦魇之中。天亮了,梦仍在继续。“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道诅咒,生命力比城市本身还要顽强,《双河》中比喻,像刚洗净的果实,落在地上自然生长。而我始终没搞懂这个口号的对象是谁。对新一代人,过于陈旧,没有生机;对老一辈人,又显得莫名其妙,荒诞不经。同样,所谓“东北文艺复兴”这一伪命题,也不会给东北作家和读者带来文化自信,东北既不会成为沈从文的湘西,也不会成为金宇澄的上海,而班宇因为生活在沈阳,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也只能是他写作初始的尝试。

《冬泳》,班宇著,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9月。
《冬泳》出版的时候,朋友谈起父母下岗的遭遇,至今仍有阵痛。这种成长背景,会将人分流为两种不同的人生,一种竭力飞跃东北,怀抱青春理想投身北上广深,另一种则将青春热情来追寻稳定的工作,而本地民营企业工作的人被看做这两者的过渡。在沈阳,即便规模达到两三万人的公司工作,在上一辈人看来仍是在给个人公司打工,比起为国家工作仍不稳定。某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朋友讲,当年在北京,公司发起全国营销活动,要求零点开始。只有东北区死守时间,其余区域都提前十分钟开始。最终的胜负,并不以是否准守规则来判定,而是业绩的达成。因此,论及东北落后,与其简单粗暴将原因归结为“人情社会”,不如说,在东北文化基因中,人们难以抑制对宏大体系的迷恋,就像卑微的奴仆从未想过与规则共舞,只能在迷恋之中逐渐异化。即便都知道事业单重组,对事业单位的迷恋仍影响显著,这体现在人们对后代的择偶标准中。所以,在《渠潮》中,警察为遵守更高的规则和使命,抹去了人的个性,让其在时代洪流中自生自灭;在《蚁人》中的蚂蚁生意,被推动地盛极一时,造成千家万户的悲剧。
沈阳人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在这苦寒之地,人的个体性体现在社交账号上,更多时候,人们甘愿抹去个性的光彩,甚至在社交账号中,也因有领导的在场而变成了职场真人秀。这样的环境下,人的精神分裂为超脱的自我和随波逐流的自我,这两者互相嘲讽。很难说哪个真实。那个为生存隐忍退让的,很难代表真实的自我,而那个彰显个性,却仅占据生活中极少的时间。尼采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在此形成对照,互为彼此的叙事对象。与此相同,在历史洪流中,个人际遇也是叙事对象。在对历史的叙事中,皆从偶然出发探索必然,而在东北,探索逆向进行,即从看似必然的律令出发,最终却俯拾散落一地的偶然碎片。
《逍遥游》收录的小说,不仅指出了这一逆向状态,而且超越了必然与偶然的辨析,指向了写作,甚至存在本身,这是班宇的难得之处。书中能看到较为传统的叙事,如《夜莺湖》《逍遥游》,也能看到先锋叙事的试验,如《双河》《山脉》。两者都指向人的存在——我们如何抵达真实,如何逍遥游。
班宇虚构了不同的写作者。在读者的时间中,虚构和真实事件同时发生,真幻莫辨,但班宇显然有着更清醒真切的认识。我们如何与个人的历史和解,个人的历史如何与时代的历史和解,这才是难以抵达的真实之谜。人们常说,现实比小说更离奇,这意味着,现实违背人的认知逻辑,而小说,即便先锋试验,也都在寻找或建立某种逻辑叙事。班宇冒险的是,他挑战的不只是文学叙事,而是存在本身,在一个个文本中自我指涉,让意义分崩离析,让万物静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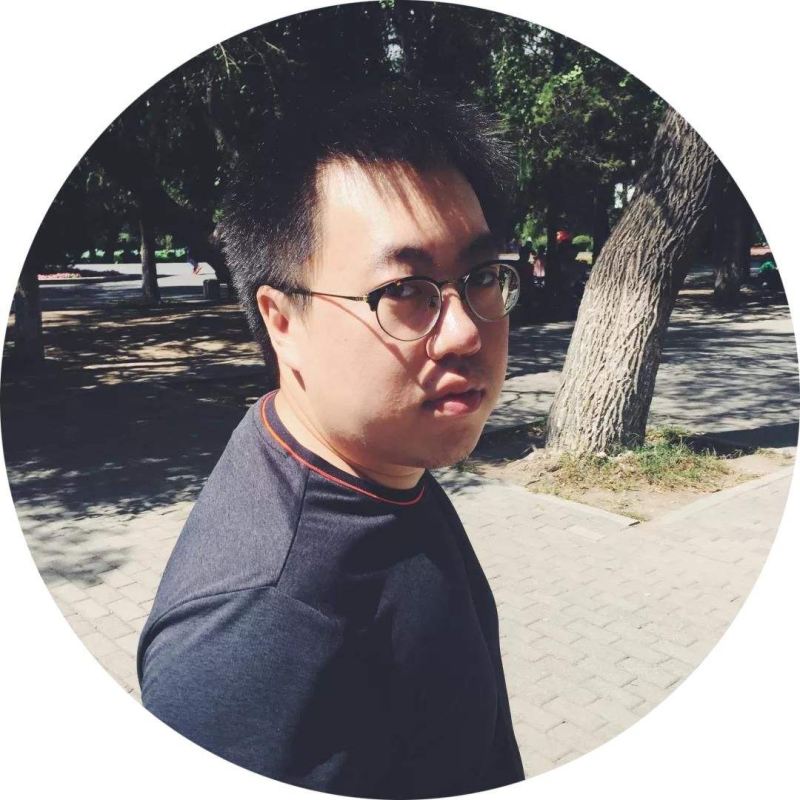
班宇
在现代小说中,写作者常反观写作行为本身,就像在说话时分析语法,在航海中钻研船只构造。写作是在虚构,写作行为对作者而言又是现实,当作者通过虚构反观现实,将看到荒谬的真相。在班宇在叙事中做了更深的探索——现实由虚构塑造,在虚构中踟蹰前行。
占据人的并非全是外在世界发生的事情,有很大部分是内在时间。因此,《双河》中,“我”睡去后,刘菲的故事自然生长,而外面下雨则无关紧要。对“我”而言,刘菲的故事显然更为真实。《双河》为何不是两条河?因为“双”是一组对照。左边一条河,右边一条河。“我”的小说是虚构叙事,这影响了现实中言言的说话方式,同时,“我”真实发生过的回忆却是周亮的叙事。在《安妮》中,B觉得“仿佛自己从不存在,而是由别人的想法构成的。”“我”失去了对过去的叙事而失语,女儿名字叫言言,当我与女儿和解,也就重获了对过去的叙事,因此飞机上,在言言熟睡的脸上,“我”找到了逝去的时间。时间是什么?是现实生活的叙事。
《安妮》中,B不断回忆前女友的事情,与其说在补充,不如说B沉迷在这种叙事中,只要叙事还没终结,人生的可能性就尚未封闭。B的岳丈和未婚妻的闺蜜K,分别代表封闭的和尚未开启的叙事。人寻找自我的同时也在逃避自我。所以,一个故事讲得足够清晰,就没必要写了。存在逻辑缺口,虚构与现实间还存在裂痕,叙事才能继续。《蚁人》中,人形蚂蚁的躯壳在月下反光,形成黑镜,“我”看见自己的倒影。文本无法从文本中得到诠释,我也无法从自身认识自我。我们必须虚拟一个他者的角度,才能将叙事的触角深入存在之根。然而,这个他者,实际上仍是自己,因此,我就在叙事中无限循环,落入往复的黑洞。
《山脉》将这个问题推至极致。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博尔赫斯最初的写作,虚构一本小说,写这本小说的评论。班宇承接了这种叙事,讲述一个书评人评述不存在的小说。在这一叙事中,文本内外的班宇一样,都在通过叙事来摧毁叙事。我们虽被告知,通过小说片段、评论、讣告、日记、访谈能推测小说全貌,但实际上永远不能抵达,我们的推测过程,也是在和文本外的班宇一同建构小说的过程。文本外的班宇将文本《山脉》的中心部分挖去,只留下零散的碎片和逆光剪影,而文本内的班宇的《山脉》始终未完成,我们还知道,其中有角色用未完成小说手稿点燃山林。这不但拓宽了小说叙事的空间与可能性,也让作者与读者在彼此关照的同时自我指涉。读者阅读时,遇到的不是班宇,而是自己。班宇虚构了班宇,我虚构了我。不论作者班宇,还是随书评人阅读的我,都在这虚构中重建并获得意义。
“现实与虚构本来就是同一个词语,虚构的情节被写出来,也会逐渐变成现实,一切都会发生,只是时间问题。或者说,现实也是对虚构的一种投射、复制。”
《山脉》第三章,讲述勘察员C考察地方历史。我们说历史传承,当下通过历史来获得意义。然而,如果历史断裂处显示,其本身也是虚构的,或由碎片拼凑而成,我们对待历史和未来的态度,便极为可疑。再次回到今天的沈阳。不论哪个行业都在重建对东北未来的叙事,即便这种叙事仍逃不开过去的笼罩。官方律令的叙事是企业沉浮,企业沉浮的叙事是个体的人生际遇。我们忽视了自己踩在偶然性的脆弱玻璃上,而此时必然性尚未建立,我们无法获得必然性的整全,就像通过镜子的碎片无法重塑其本来样貌。回到东北人在时代中的人生际遇,其荒诞感并不体现在对现实的嘲讽与批判上,而是体现在一本正经的严肃谈话中,如《夜莺湖》中,苏丽弟弟死去,“我”用“生命没了,学习不止”来劝慰。
《山脉》中虚构了一篇不存在的小说,也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归宿和本源。“这里是生命的最后,万本归一,却也如初生一般,我站在这里,每天都能看见无数的亡者,操着各地的方言,前仆后继,化为乌有。”我们看不到《山脉》,看不到讣告的作者,也找不到终极本源。我们就像卡夫卡的K,永远无法抵达,只能在抵达过程中获得意义。而消失与从未存在的区别就在于这一探索和抵达的过程,西西弗斯就是这样。《双河》中,我们看到,人生实际上就是在双河之间踽踽独行,不知道流向哪里,哪条河都无法代表自己,我们只能在不断地对照和反观之中存在。
班宇不断地自我指涉,像蛇咬嗫自己的尾巴。“神木恒久不死,变做空虚,伸手即可捕获。”这里是庄子的无何有之乡,在这里,我们抵达逍遥之境。
撰文丨阿唐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