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一词总会被人误认为肤浅,而深刻的人往往会给人留下苦闷沉重的印象——能否在这二者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阅读的快乐、游戏的快乐、消费的快乐……获得愉悦感的不同方式又是否有高低优劣之分呢?
更具体地说,一个人喜欢巴赫或者喜欢贾斯汀·比伯,是否有高下之分呢?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是在对不同的快感做比较:听巴赫获得的享受与听贾斯汀·比伯获得的享受,这两种快乐有高下之分吗?
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中,哲学教师斯科特·塞缪尔森梳理了哲学家边沁和约翰·穆勒对这些问题进行的探讨。他们围绕快乐与痛苦的标准做出了细致剖析。快乐符合功利主义的原则,人应当将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但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却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在快乐之外,人还想要更多。或者说,有一些更具有长久快乐的价值之中,往往包含着痛苦的成分。比如,写一本小说、跑一场马拉松,是能带来长久满足感的事,但在它们之中,一定包含着痛苦的付出。
关于快乐的讨论,也帮助我们更辩证地看待生活中的痛苦时刻——它们并不全然是坏事,有些快乐,是借由痛苦才能达到的。
原作者|[美]斯科特·塞缪尔森
整合|宫子

《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作者:[美]斯科特·塞缪尔森,译者: 张佩,版本: 未读·思想家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20年6月 。
快乐是值得推崇的功利主义
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与其期待超自然的正义,不如努力在此时此地将痛苦最小化、快乐最大化,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确定拥有的时间。这就是边沁所谓的“功利原则”,另一位功利主义哲学家穆勒经常将其称作“最大幸福原则”。然而,他的哲学却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无神论,因为它驳斥了信仰存在的基础,即对痛苦的根本接受,认为痛苦是人类旅程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另一种说法是,边沁的哲学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的概念。传统观念认为,自然是神设定的一系列限制,如万有引力、死亡、黄金法则等自然和道德法则,如果我们无视这些法则,最终就会受到惩罚。而边沁和穆勒认为,自然不过是原始数据,我们应该对其更改,以实现人类可接受的结果。比如,死亡和疾病不应该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被接受,我们应该与其抗争,乃至将其更改。而且,并没有所谓的“自然法则”,也就是道德准则在支配着我们,我们只是拥有能够或多或少满足的欲望。少年穆勒最早接触边沁的思想时,最令他兴奋的正是边沁推翻了旧的自然概念。“‘自然法则’‘正当的理由’‘道德感’‘自然正义’诸如此类……都是巧饰过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新时代开始了。”
用“功利主义”概括源于边沁的道德理论,有些误导人。边沁所说的“功利”,不仅指有用的东西,还指对实现满足感特别有用的东西,他声称,满足感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边沁认为,痛苦和快乐是对我们“有绝对掌控权的两个主人”。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对我们有绝对掌控权的主人,应该引导我们不仅去增加自己的快乐、减少自己的痛苦,而且要去为每个人实现最多的满足感。我们应该以最好为目标。边沁认为,既然快乐是好的,那么更多快乐就更好,以此类推,最多的快乐是最好的。约翰·穆勒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中的表达比边沁更为有力,他指出,最大幸福原则源于我们内心的两种冲动:第一种,我们对自己快乐的渴望;第二种,我们天生对他人的道德冲动。将两者合在一起,你就会明白,我们不仅应该为自己带来快乐,也应该为我们所影响的每个人带来快乐。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代表作包括《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政府片论》等。
如果我们想给功利主义起一个更花哨的名字,不妨将它叫作“伦理享乐主义”(ethical hedonism)或“道德快乐主义”(moral voluptuism),无论是哪个希腊或拉丁词,只要意思是“给每个人最多的满足感”就行。
简言之,边沁想让理性掌控我们的命运,这样世上就有尽可能多的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从 18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他的思想逐渐流行起来,先是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然后在改革过程中的英国。逐渐地,边沁的一些激进提议在整个现代化的世界中被接受 :经济自由的福利国家、女性享有的平等机会、离婚自由、政教分离、同性恋合法化,这一过程虽然缓慢,但毫无悬念。
不能在快乐中放弃价值判断
尽管约翰·穆勒很孝顺,从未反驳他父亲及其导师的功利主义,但他对功利主义所做的改变之巨大,以至于它几乎需要起一个不同的名字。虽然穆勒独特的功利主义作为理论是否站得住脚,仍存有很大疑问,但笔者认为,穆勒对边沁核心思想的改动,证明了他具有一种无可指摘的哲学品格:他努力解决生存的真正悖论,即使这样会让他的理论看起来站不住脚。
在穆勒的代表作《论自由》(On Liberty)中,穆勒阐明了成为现代性第二天性的政治原则:“违背文明社会任何成员的意愿,对其正当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伤害他人”。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们就能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想法乍一听像是功利主义在政治领域的一种完美应用。压迫、征服和奴役都是痛苦显而易见的根源,因此,“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权利体系,似乎是一剂完美的解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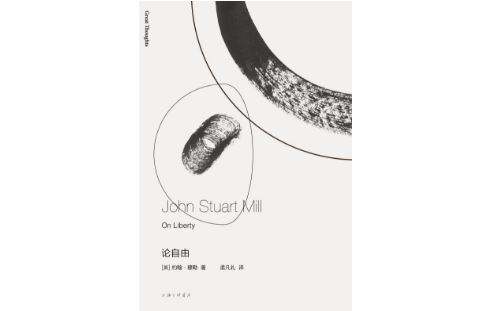
《论自由》,作者: [英] 约翰·穆勒,译者: 孟凡礼,版本: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4月。
但自由,尤其是穆勒在其杰作《论自由》中所颂扬的那种无所不在的自由,包含了某种对苦难的非功利的包容。以常见的言论争端为例,在一些情况下,对某种言论的镇压,可能打着为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旗号而被合理化,事实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例如,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促使一些公民希望镇压可耻的恐怖主义宣传, 尤其是恐怖分子在网上使用的那种心理操控 。
穆勒令人震惊地陈述了他的功利主义原则 :“如果所有人都持有同一种观点,只有一个人除外,而这个人所持观点正好相反,那么剥夺这一个人说话的权利,并不比剥夺所有人说话的权利,更加公正。”简言之,穆勒认为,自由的价值高过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换言之,他所谓的“最大利益”包括真理或自由等价值,而这些价值并不能约化为最大化的快乐。
换言之,自由赋予我们作恶的权利,而这些恶恰恰是几乎所有道德体系(包括边沁的功利主义)试图消除的。如果我们想根除痛苦,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颂扬自由?如果我们想打击恐怖主义、减少犯罪,将人类彼此施加的伤害最小化,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守法律?如果我们想将痛苦最小化,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仰人的自由?
在穆勒看来,尊重人的权利主要是因为人无完人,我们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正确。我们很容易去打压那些看似虚假、邪恶的事物,却在后来发现它们无害,甚至可能是正确且有用的。人的判断难免出错。我们没那么高明,怎么能保证对打压谁的观点的判断不会错误呢?对于容易犯错的我们,包容不同的声音不是更好吗?更何况,即便是毋庸置疑的错误或邪恶的信仰,只要能表达出来,难道不会让我们更生动地认知真理、更热情地捍卫真理吗?
虽然穆勒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但它与边沁对人类理性的信仰背道而驰。边沁功利主义的优势在于,我们中最智慧的人应该认真思考困扰我们的问题,想出解决办法,并将其付诸实践。穆勒认为,自由不仅有助于减少痛苦,还是我们的自我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起将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理论,用尊严或自然权利之类的概念,捍卫对自由的信仰,难道不更令人信服吗?而在某些时刻,这样的功利主义原则难道不是更有指导意义吗?
快乐是否有高低之分?
穆勒对功利主义所做的第二个改动,是区分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而边沁坚决反对这种区分。边沁有句名言 :“如果快乐的量是相等的,玩图钉和吟诗作赋一样好。”换句话说,打保龄球和读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诗一样好,或许更好,因为喜欢打保龄球的人更多。在我看来,尽管边沁做出了几乎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的分析,确定了某些快乐的强度、长度、纯度以及生产能力,他却拒绝接受听巴赫音乐的快乐必定比听如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这类的流行音乐的快乐更好。

加拿大流行歌手贾斯汀·比伯 ,图片为比伯纪录片剧照。
如果你从其中一种或是两者之中都能获得快乐,那当然再好不过。但巴赫迷不应该鄙视比伯的粉丝,比伯的粉丝也不应该鄙视巴赫迷。在边沁的道德运算中,如果某种事物能给人带来快乐,它就是好的 :没有比感受本身更高的衡量标准了。如果音乐学校、演奏家和管弦乐团等维系巴赫音乐遗产的传统都消亡了,只要人们还跟随比伯的音乐摇摆,那么对边沁而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
如果这个世界巴赫的音乐越来越少,却到处充斥着比伯的音乐,那么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的人来说,这就是对边沁功利主义理论的直接反证。边沁的哲学不仅没能说明价值的高低之分,也没能正确理解某些行为的是非之处。
不难想象,功利主义理念支持色情产业,至少某种类型的色情产业,因为色情产业为大多数人带来了快乐,只牺牲了极少数人的利益。事实上,我们不妨想象一种情况,一部成功的色情片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对演员造成任何伤害。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只是比消费者情愿认为的要少得多。这样的色情产业真的在道德上是好的吗?事实上,没有对演员造成任何伤害的色情作品,真的在道德上比跑一次马拉松或写一部小说更好吗?
毕竟跑步和写作包含痛苦的成分,而且很少能像一部还不错的色情片那样带来广泛的快乐。难道除快乐和痛苦之外,就没有其他我们应该用来评价人类努力的价值标准了吗?事实上,我们许多最有价值的活动,难道不都包含着一些不可消除的痛苦吗?
穆勒试图通过区分快乐的高低来拯救功利主义,使其不至于被这一问题驳倒。是的,色情片能为消费者带来快乐,但这是一种低级的快乐,穆勒会如此辩驳。如果色情片能在不造成任何伤害的情况下,给很多人带来快乐,那么它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但它仍然没有跑马拉松好。尽管跑马拉松会为运动员带来痛苦,但它会带来一种本质上比看色情片更高的满足感。穆勒称,我们在运用最大幸福原则时,不仅要考虑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快乐的数量,还必须考虑其质量。
穆勒在衡量价值时,使用了快乐和痛苦之外的标准吗?他声称,他决定快乐质量高低的测试,完全符合边沁的根本思想, 即快乐和痛苦对我们有着绝对的操控力。穆勒说 :“如果体验两种快乐的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更喜欢其中一种快乐,这种喜欢无关道德,那么这种快乐就更好。”显然,有时,我们认为的更高级的快乐是能够通过穆勒的测试的。但是,情况大多或总是如此吗?

桑德尔(Michael Sandel),政治理论家,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现为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讲授当代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他在哈佛大学讲授的《公正》课程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该课程被制作成哈佛公开课后在网络广为流传,成为风靡全球的哲学公开课。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微信公号“新京报书评周刊”阅读桑德尔专访《除了钱,美好生活还应当具备哪些要素?|对话桑德尔》。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他颇受欢迎的政治哲学课上,给学生播放了三个视频,然后让他们进行穆勒的测试,并对其进行评价 :第一个视频是一场顶级职业摔跤比赛;第二个是《哈姆雷特》中的一段独白;最后一个是《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的片段。观看结束后,他问学生,觉得哪个视频最有趣,哪个视频层次最高或最有价值。
《辛普森一家》常常被评为最有趣,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常常被评为最有质量。这个实验的结果难道不是恰恰证明,穆勒对功利主义的拯救是失败的吗?更好的并非总是最令人愉悦的,难道不是如此吗?正如桑德尔所说 :“功利主义将一切简单归为计算快乐和痛苦的粗糙算式,因此备受指责,穆勒想挽救功利主义,可他说的是与功利本身无关的人类尊严和人格的道德理想。”

动画片《辛普森一家》剧照。
穆勒拯救功利主义,使其不至于抹平人类生活的高度的唯一途径,便是改变功利主义的根本前提。穆勒想要根除无意义痛苦,增加有意义的幸福,但他还需要找到“快乐好、痛苦坏”的原则之外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无意义痛苦、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
我们想要幸福,但我们也需要意义。幸福和意义常常重合, 但并非总是如此。
我们尚不能确定,人类生活许多至关重要的事件中,快乐是否大过痛苦。例如,如果经过仔细分析,很可能会发现,抚养孩子带来的头痛比乐趣多。但是,仅从孩子带来多少快乐的角度试图衡量育儿的价值,这种行为本身难道不会显得过于片面吗?有时候,带来最多头痛的孩子,也是最受疼爱的那一个!
许多人类最伟大的追求——体育、文学、工作、慈善、爱情,不也是如此吗?是的,它们常常是满足感的来源,但它们的意义无法完全用快乐和痛苦来衡量,难道不是吗?穆勒深信,赋予我们意义的事物会让我们幸福,也许最终会是如此。我们当然也希望如此。但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在快乐和意义两个时而冲突的目标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本文摘自斯科特·塞缪尔森《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由出版方未读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 | [美]斯科特·塞缪尔森
整合 | 宫子
编辑 | 走走 罗东
导语校对 |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