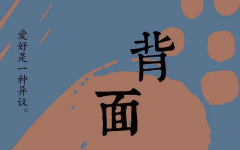刀尔登在其杂文集《不必读书目》的题记里说:“对传统观念的某一部分,我在这些年里,一有机会必加诋讦,但细细想来,真正不满的,是今人对这些观念的态度,而非那些观念本身,因为那是古人在许多年前的思想,格于形势,他们还能怎么想呢?今人的不智,是不能记在前人账上的。”这一“不满”也在其新书《鸢回头》中有所显露,而且有所扩充。
比如如何阅读《论语》这一问题(其中引含着如何面对这部传统经典中的观念的问题),刀尔登在《鸢回头》中给出的答案是:“不妨读之,最好是用轻松闲适的态度读之。”他认为,过高的期望会妨害对《论语》的理解;所谓尚友古人,就是平等对话,而不是卑贱地伸出手心来找打。
这种阅读是对话性的,甚至是审美性的,也基本上是非功利性的,即并非为解决个人的、历史的或时代的问题而读,因为“人类必须解决以获得进步的问题,遥远的孔子没有回答的责任。”当然,书中写到的另外两位遥远的智者——老子和庄子,也没有这个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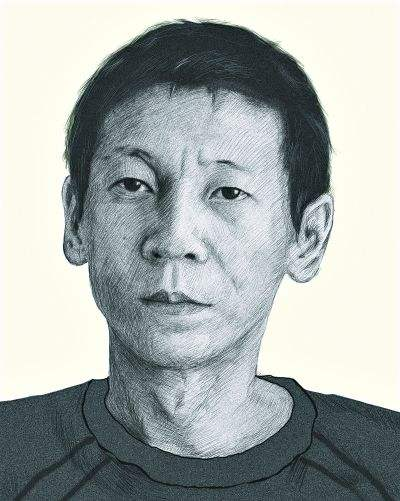
从前叫三七,现在叫刀尔登,本名邱小刚。有人说他海内中文论坛才气第一,有人说他是1977年后北大中文系出品的最优秀的三个学生之一,有人说他是当代大隐,有人说他是古代竹林七贤之刘伶。著有《鸢回头》《玻璃屋顶》《中国好人》《不必读书目》《七日谈》《旧山河》《亦摇亦点头》等作品。(图片源自网络。)
此外,书中涉及的一个基础问题是,我们在阅读《论语》《老子》和《庄子》时(尤其是《论语》),我们读的是什么?就像书中所说,“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在读什么,是《论语》本身,还是一部《论语》的接受史”。后人的“接受”既是阐释,且又不单是个人的阐释。权力的介入可以让一部作品中的“概念”成为通行准则,又不断改变其原本面貌:“人们把这些概念放到伦理的结构里,更放到权力的结构里,最后失去本来面貌,成为异己的力量。”在这种语境下,儒家的“仁”在长时间里反倒成了权力之柄。一种观念,美好到无以复加,在被利用的过程中竟可以“变形”至此,我们回望时看到的是迷雾重重,想要穿透实在不容易。以此推论,两千年后的我们在“接受”《论语》《老子》这样的古代经典时,接受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大概是刀尔登在阅读《论语》《老子》《庄子》三部作品时首先警惕的;并继而进入文本细读式的个人化分析。分析虽是个人的,又以各种方式不时与当下处境牵连,对此,不同的读者想必会有不同的感悟。
采写丨张进

《鸢回头》,作者:刀尔登,版本: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0年6月
“过高的期望会妨害对《论语》的理解”
新京报:你写《鸢回头》中的这些文章,有没有具体的契机?
刀尔登:可以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有的事情无话可说,有的事情有话不可说,那么,选择就不多了。所谈到的三本书,好些年里一直忽视着,这次是一边写一边重温,既是重温这三本经典著作,也是重温过去的一些想法。
新京报:有些人阅读、阐释《论语》《老子》《庄子》是为了解决当下的某些问题,你认为“历史中藏有我们的问题的部分答案,而我不大相信,旧日的创造,能以其原本的身份提供什么”。你这么认为的原因是什么?
刀尔登:西晋的陆机写过一篇《五等论》,里边有一句话叫“百世非可悬御”。古代儒生讲复古,言必托古,言必称三代,张嘴闭嘴不是万世法,就是百代师,对此,现代读者会说,连自己时代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何谈为后世立法,然而对这种质疑,古人已准备好了现成的答案,那就是后世的失败,和他们自己的失败一样,都是因为没有完全地回到古典精神。——这是一种不接受验证的态度,难以对话的态度。传统话语里无疑有超越时代的可贵的东西,但对这些,我认为,至少要问三个问题,第一是是否有针对性,第二是后世人是否能够轻易地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第三是当我们觉得一句话“说的真好呀”的时候,是在其本意上,还是在后世的理解上使用这句话。比如前面引的陆机的“百世非可悬御”,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将自己的理解附着其上,我们用它表达的内容,很多不是陆机所能想到的。
新京报:《“不仕无义”?》篇中说,“孔子的《论语》仍然是适合今天的读物。”这句话有其语境。脱离语境,从更广泛的层面看,你认为《论语》仍然适合当下读者阅读的原因有哪些?
刀尔登:我查了一下,原话是:“人类生活,在这里是政治生活的共通之处,使不同时代与地域的人,面临共同的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延续到今日,也并不奇怪,如果人类政治生活的权力本质并没有改变的话。这也是为什么,孔子的《论语》,仍然适合成为今天的读物。”这是有缺陷的表述,但也勉强能说清我的意思。
新京报:《我们在读什么?》篇中,你建议用轻松闲适的态度读《论语》,而不要紧锁眉头,一脸严肃。这样读的好处是什么?
刀尔登:过高的期望会妨害对《论语》的理解,我坚信这点。孔子被封为至圣先师,而且《论语》里他的话又是学生记录的,口吻往往是训诫式的或先知式的,更加容易让读者预设一种阅读姿态。所谓尚友古人,就是平等对话,而不是卑贱地伸出手心来找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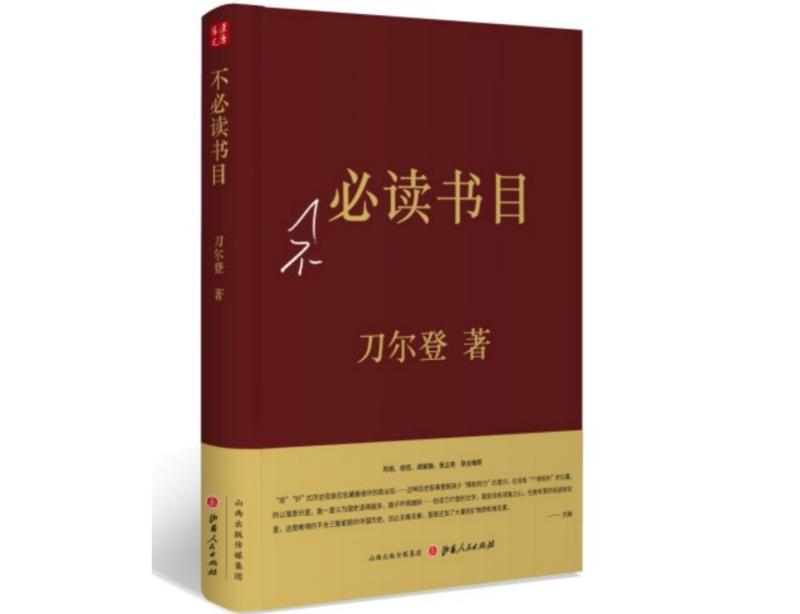
《不必读书目》,作者:刀尔登,版本: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6月
“一旦自由受伤,什么都受伤”
新京报:《要不要让孩子读〈论语〉》篇中说,“孔子是很好的人,但‘传统文化’中的孔子不一定是;〈论语〉是很好的书,但‘传统文化’中的〈论语〉不一定是。”能否请你稍为详细地说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刀尔登:“传统文化”是加了引号的,因为我也不清楚这个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不是一点不知道,是知道得很模糊。从《论语》中我们得知,孔子是个不错的老人家,有时还挺有趣,《论语》也是挺有意思的书,但后世对孔子及《论语》作粗暴的解释,将其人其书用来建立正统、压迫异见,也是我们熟悉的事情。
新京报:同一篇中还提到,如果初中的孩子只有较少的阅读时间,你更倾向于推荐他们读“文学书以及细节丰富的历史书”,而不推荐《论语》,因为担心孩子过早地被理论束缚住。理论是认知方式,同时又是束缚,你如何看待这种矛盾性?
刀尔登:我不记得说过《论语》会用“理论”束缚人之类的话,因为《论语》并没有完整、明显的理论表述。至于推荐细节丰富的书籍,是一贯的主张,无论对孩子还是成人,扩展经验、丰富心灵是阅读的第一要义。我最喜欢的一句莎士比亚是,天地间有无数事情,不是你的哲学所能梦想到的。孔子有所谓“四毋”,也是反对人自居一隅,便以为世界不过如此之大,以为万物在我,拒不承认世界的丰富性。举一个当今常见的小例子,是“最”字的滥用,“最”来自比较,一个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什么见识也没有,说起话来动不动就这个最好,那个最美,算不算坐井观天?
新京报:《走出森林》篇中说,孔子(对社会)的理想被“腐蚀、妥协、利用到无以复加”,以致“‘仁’反倒成了权力之柄”。其中原因在于权力之恶,而非孔子的理念。老子和庄子的遭遇也大致如此。但“我们无法不生活在权力中”,在这一前提之下,当面对一种看上去“无限美妙的社会观念”时,你认为怎么做、怎么想更合适?
刀尔登:在社会建设方面,人类产生过许多美好的观念,遗憾的是,它们并不都能引导至美好的生活。拿现在说,环境保护,种族平等,都是非常进步的观念,是现代的好东西。但如何实现呢?是求诸风俗,还是诉诸权力,是非常大的分野。我们的一大倾向,是一有什么事首先想到交由权力去做,而忘记了人类所产生的最美好、最生死攸关的观念,是自由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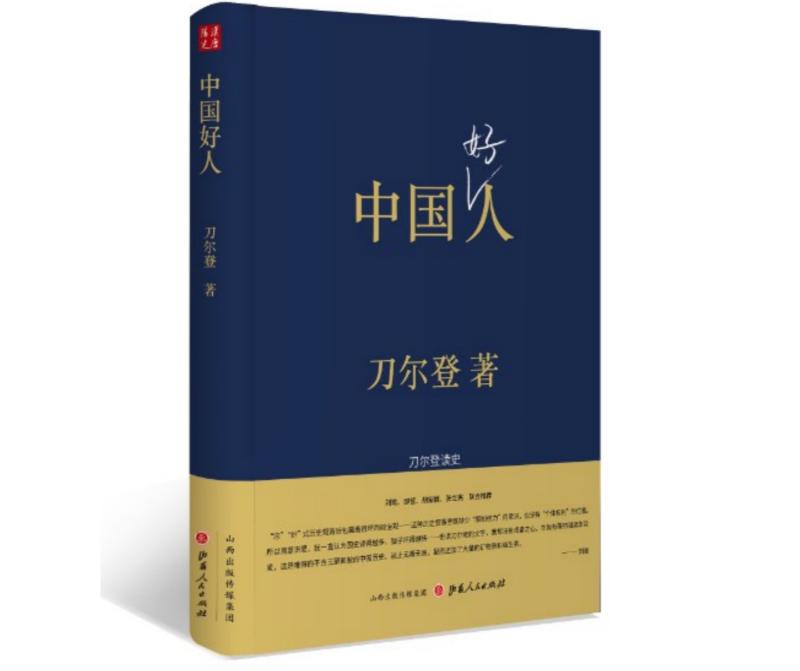
《中国好人》,作者:刀尔登,版本: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6月
“老子示人以高明,庄子示人以真正的内心冲突”
新京报:《卫国故事》篇中说,“孔子的真意为何?谁知道呢。”在其他篇目中,也有类似的意思。《论语》的内容往往缺乏语境,更缺少描述,阐释性极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阅读《论语》,只能获得“语义性的解释”而很难获得“历史性的解释”?获得“历史性的解释”是否才有可能抵达“真意”?有人说,阅读即是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意”是可能抵达的吗?
刀尔登:如果不从形而上来立论,就一般语义来说,“真意”可以作为一种合理的目标。至于能不能达到,因事而异吧,有时能,有时不能。能当然好,不能则不必强求。如果有人宣称对《论语》这样的一本书字字清楚,句句明白,那里边一定有错误,而且那态度是危险的。
新京报:《毋必》篇中有个例子,说弗吉尼亚大学某助理教授写信反对该校校长引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因为杰斐逊曾是奴隶主,公开信竟得到四百多名师生联署。一种正确的观念(种族平等)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后果?你认为应如何反思这种对“政治正确”的理解和运用?
刀尔登:先不说不要因人废言的道理,也暂不提历史原则的道理,只说一种观念,自我赋予相对于其他观念的优先地位,使由此观念生发的解释,变成新的正见,而这种地位的获得,并不是自由讨论所至,而是借助于权力来实现,——这种现像,我们会不会觉得熟悉呢?每一个读过点历史的人,都会觉得熟悉。
新京报:假如你现实中有一位朋友是类似庄子这样的“知识分子”,“高逝远蹈”,认为“予无所用天才为”,“道无以兴乎世”,你会如何评论他?
刀尔登:人各有志。我不会从这方面地评价他,而会从别的方面,比如他偷了只鸡,我就会说他的不好,他要是把偷来的鸡请我吃,我就说他好,诸如此类。
新京报:《却曲》篇中说,“所谓‘退路’者,庄子的路为我所不取……”你不取庄子提供的精神退路(逍遥、齐物),这一选择背后有你怎样的想法?
刀尔登:因为我难以想象这样一种方式在现实中不将是自相冲突的。
新京报:书中相对零散地提到老子和庄子的异同,比如“与老子不同,庄子是个人化的……”,“庄子比老子更入世”等。你认为,两位智者的异同主要有哪些?
刀尔登:老子示人以高明,庄子示人以真正的内心冲突。
作者|张进
编辑|张婷 董牧孜
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