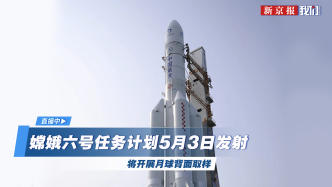德里克·贾曼不只是一位才华耀眼的天才导演,此外,他还是一名画家、舞台设计、作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园丁。除了电影,他还有日记《现代自然》《慢慢微笑》,电影日志《以卵击石》,随笔集《色》等作品。
近日,贾曼日记《慢慢微笑》的中译本出版。这是贾曼最后的日记,写于绝症之中。贾曼是当时极少数公开艾滋病情的名人之一。他一边怀着对生命的热忱与疾病抗争,一边奋力发声以消除大众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伴侣和朋友成为他生命终章里最坚实、温暖的后盾,在核电站旁建造的美丽花园则成了他的灵魂归宿。

英国导演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1942—1994),一生拍有《卡拉瓦乔》《英伦末日》《爱德华二世》《维特根斯坦》等多部艺术影片,曾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泰迪熊奖等国际性大奖。最后之作《蓝》在双目近乎失明的情况下完成制作,以超前的视觉理念和深情的自我剖析轰动影坛。
《慢慢微笑》集合起贾曼一些零碎的自传文字,去除重复以及有法律隐患的段落。剩下的文字都保留了德里克口语体的连贯风格——他曾经充满美感的笔迹,也随着病情的加重而退化了。
大部分的时间里,贾曼都保持手写的习惯——除了两次因病痛而无法提起他的墨水笔,只好口述日记之外。在写作最后的日记时,他已经失明,凭着对笔尖与纸张的记忆,他才能略带潦草地写下文字。
贾曼的日记,总计三十三本,全都书写在水彩本上,手工装订的黑边,一本本小小的刚够放进他的外套口袋。其中,两卷遗失了,尽管所有的日记都写上了“如有拾获,定有奖励”的字样,但仍然没有下落。
编者在按语中指出贾曼对于日记出版的态度矛盾:一度他曾指示编者在他死后将这些日记全部烧毁。可他仍然在持续写着,为每卷日记附上一些暂定的标题,比如“心安”“一阵失忆”“虞美人之战”“圣人之日”“在火焰中被击倒”“乌托邦里的一道寒意”“岁月老去”……贾曼总是为日记的标题竭尽心力。他在日记中对后来参演了他第一部长片的某位旧爱抒过一段情:“在《塞巴斯蒂安》的一场戏里,他浮出水面,慢慢微笑起来。”他在“慢慢微笑”下画了横线,编者便拿来做了书名。
早期贾曼身体还健康时,他在一卷日记的结尾颇为动人地写道:
“请阅读我锁进这些书页中的关于世界的思虑;然后放下书,去爱。愿你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无顾虑地去爱,并且记得我们也曾爱过。当阴影逼近,却更见星光。”
——德里克·贾曼,《自担风险》
本文摘编自《慢慢微笑》一书,由出版社授权转载。

《慢慢微笑》,[英] 德里克·贾曼 著,王肖临 译,一頁folio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9月。
一九九一年
7 月6 日 星期六
热浪继续来袭。我睡在开往阿什福德的火车上,火车带着我穿过浅蓝的亚麻田。
花园从未如此好看,在正午的阳光下显得令人心醉神迷。
肯打电话说他昨晚读完了《现代自然》,他发现我沮丧的个性和他在《爱德华二世》的片场所了解到的截然不同。“我得了肝病,”我说,“那些肺结核病菌害我得了黄疸,我的眼睛看上去像是裂缝泛黄的油漆。”之前我感染肺结核病菌后,立刻就治好了。
今天,我比以往都更清楚地感知到我的双脚立于何处——花园里的花开得更甚从前,所有的野花都开了。
~
艾伦· 贝克在去莱伊参加E. F. 本森 1 纪念活动的路上顺便拜访我——我们边沿着海滩散步,边谈论建立同性恋档案馆的可能性。
~
寂静的傍晚,隔壁的红发男孩爱德华用他的气枪瞄准如火的夕阳。夕阳的残光为虞美人染上深红,牛青草焕发出虹紫色,我的天蓝色T恤反衬出展望小舍耀眼的原木。一阵和煦的微风在怒云下摇动着草地的剪影。爱德华发了最后一枪,夕阳缓慢沉到莱德教堂后,消失在那座待售的小屋后面。
随之而来的黑夜中闻得到大海的味道。

贾曼对植物有异乎寻常的痴迷,其位于肯特郡邓杰内斯的花园已成为著名景点。
8 月21 日 星期三
珍惜一些朋友,侮辱剩下的那些人。
一九九二年
4 月4 日 星期六
我疼得近乎筋疲力尽,我拖着独轮手推车穿过卵石路。我的身体一侧永远痛着,并且依然感到愤怒和沮丧。我和很多朋友一样有妄想症。保罗打来电话,说的话听着像是在回应我之前感觉强烈但却未曾表达的事情。我的弱点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学识渊博而睿智的人可以做任何事,却无法认同这是个扭曲的时代。
~
我用刀和锥子在小块画布上施暴,直到颜料如鲜血般流淌。小小的谋杀案。当这些悲伤的画的作者逝去,热情也将转冷,留下的只有粉尘。我的意识无法集中,就像灰烬一样暗淡。HB说:“把话说完,来啊,我赌你也不敢。”
~
我就着一杯冷水吞下了药片,考虑要彻底狂野地叛逆一番。马克医生说他大部分的病人都放弃了治疗并且掩饰着自己的病情。在道德的钢丝上平衡,在偏见的飓风中摇摆,我继续努力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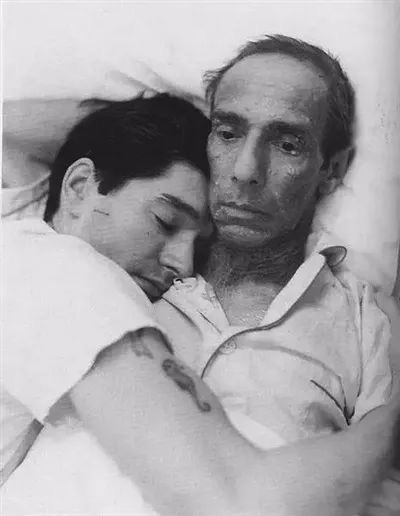
德里克·贾曼的晚年。
~
一只硕大的黄蜂在寒冷的东风中绕着花园飞行。阳光依然灿烂。
年迈的渔夫面朝黄土,日复一日蹬着车经过这里,他饱经风霜,一如活在十九世纪。他忘记了什么事,掉头往回骑。
~
尼基打电话来说《卫报》的新艺术版面编辑已经炮轰我有一段时间了,但由于他还只是助理编辑,并没有人认真听他的。报社记者们对他这样的态度感到很不满——毕竟还有其他人物值得小报去关注。我整个童年都在读《卫报》,它曾让我感到欣慰,现在当他们面对严肃的问题时,却决意直接抹黑对方,这让我感到无比困惑。我希望这种接连不断的冲击不会削弱我仅剩的一点“健康”。
4月15日 星期三
石墙运动组织发来了乞求信,迈克尔· 卡什曼主席声称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天方夜谭。我想改变一切,包括我的生活;我坐在这里等着,坐以待毙。HB和我一起在冷雨中在10路公交车站等了半小时——他的感冒很严重。
我们在海德公园角站掉头,浑身湿冷,只有植物才会享受这种湿冷。莫奈画了他的花园,我画了疾病的荒野,我的悲伤主题,这可不是爵士乐。
5 月18 日 星期一
上帝是个无神论者。

德里克·贾曼。
8月12 日 星期三(节选)
我的视力在夜间又恶化了一些。现在我正和HB一起坐在圣巴托洛缪医院里,等着他们给我输液,用的药物是更昔洛韦。
HB说要把他的血输给我。他说他的血能杀灭一切,而且这么做还很浪漫。
输血很顺利,正在进行中,我看到血液进入管子里,然后又流进了我的手臂。
我伸出手,试了试是否一切正常。我的右眼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视力。这种感觉很奇怪,好像有个影子伴在身边。HB在我身边同行,时隐时现。我还是能看见他的脸和手的,但中间的部分全都是空白。我视域的中间带已经消失了。护士说,这种情况会稳定下来的,据她所说:“我见过通过吃药稳定病情长达一年或数年的人。”
我做出了决定,要趁我还有时间,还能分辨色彩的时候拍摄《维特根斯坦》。那孩子可以对着摄影机讲述他的故事。要黑色的窗帘。学生们可不可以扮成罗马人?我们能不能建一间房,把里面刷上不同颜色的油漆?
我一直没有从其他角度想过这件事的后果,虽然总会有些其他的病症会要了我的命,但是想象失明的情景和真的失明是两码事。HB比平时更有爱意了,如果我无法再看见他的样貌,我还是能快乐得起来的。唯一让我紧张的事情就是早上剃胡子。我无法忍受别人碰我的脸,我的皮肤很容易受刺激,即便是我给自己剃胡子的时候,都会屏住呼吸。
~
回到圣巴托洛缪医院,这里的背景音乐很安静。加里护士使出吃奶的劲才找到了我右胳膊里的一根血管。在第三次尝试之后,终于见到了血。史蒂芬说,如果有根针插进他的胳膊里,他肯定会晕倒。这种事情得习惯才行,虽然我现在还是得在抽血时闭上眼。来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废墟》以及其他盎格鲁-撒克逊诗歌,命运是最强大的,命运,命中注定。我把自己交付给命运,即便是失明的命运。
输液很疼,鼓起了一个大包,针拔出来了,感觉好像一阵电流穿过我的胳膊。
~
我离开医院时,外面大雨倾盆。我站在入口处,一位老太太被困在了暴雨中。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问她是否需要带她一程。她说:“你能带我去霍尔本地铁站吗?”在半路上,她哭了出来。她来自爱丁堡,她的儿子正在病房里。这孩子得了脑膜炎,双腿已经瘫痪了。她流着泪,我却无能为力。虽然她坐在我旁边,我却看不见她,只能听到抽泣的声音。

贾曼最后的电影《蓝》,在双目近乎失明的情况下完成制作。
8月19 日 星期三(节选)
我决定拍一部电影,叫作《蓝》。里面不用图像,因为图像会阻碍人的想象力,还必须要有叙事情节,图像会为了展现魅力而窒息。没有图像,就只剩下虚空中那令人爱慕的朴素。我在医院门口和詹姆斯分别的时候,他问道,你不会改变想法了吧?我答应他,不会。
~
输液输液。输液标尺从100开始往下降,到36的时候几乎过了一个小时。我今晚累坏了,没办法回到我那狂野的HB身边,他爱我,我爱他。
一九九三年
3月2 日 星期二
我们参加《蓝》的制作工作。在韦科市,所谓的耶稣和联邦警察持枪对峙,他开枪射中四个警察,自己则在交火中身受重伤。
感受到复杂的疼痛感,令我很迷茫,失去了感官。
我们在午夜前完成了《蓝》。保持着绝对的专注。我们刚开始工作时,西蒙· 沃特尼就来到了工作室。西蒙· 特纳彻底喝醉了,看上去很可爱。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了不起——这是我第一次能正眼看自己的作品。电影随着二十世纪的发展而变动,这是第一部能够接纳抽象知识的长片,它把电影带到了已知世界的边境,奥克苏斯河。
我把这部电影献给HB,以及所有相爱的人们。

《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之中《慢慢微笑:加曼的最后岁月》一篇的插图。
4月15 日 星期四
我注意到自己的字迹变得越发潦草,好像一只蜘蛛织出了墨色的网——我的手在颤抖。现在爬进或爬出浴缸都变得极为艰难,要花上半个小时——不如跳进去好了。我再也拍不了电影了,我也写不出什么作品了。我闭上眼睛,垂下头,承受病痛。什么都没有——如果我生病的感觉是疼痛,那现在的感受就是极其可怕了。我真的认真想过要自杀——但这不是我的性格。
医生们已经多次更改我的处方了,昨天,皮肤科医生来看我,给我抹上了软膏和乳液,给我吃了些药片。“我们需要取走一点你的皮肤做测试。”
我说:“你把我的皮肤全拿走好了。”你看,我已经快疯了。我说:“如果我真的病了,请让我死吧。”死亡的想法是如此美妙,所有的挣扎都结束了,不会再有记者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已经死了——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我再挣最后一点小钱,然后去折腾其他可怜的家伙。
这所医院真是个好地方,人们都很有魅力。那位护士坐在我旁边,用手臂搂着我足足半个小时之久。我在颤抖,身体赤裸,由于过于疼痛,甚至无法躺下。皮肤是人的主要器官,所以这样的病情可以致命。
今天我只感觉疼痛,那种痛苦的感觉已经减弱,我的大脑透视结果显示没问题。我开始吃东西了,浑身颤抖和步履蹒跚都是休克导致的症状。我的肺部还好。我决定再给自己的生命一次努力的机会。
~
今天下午,太阳出来了。我和HB一起散步,以便恢复“肺部功能”,他今天比以往还要帅。我还在因休克而颤抖,心里的事情仿佛被清理一空。我仿佛身处炽热的熔炉中,皮肤逐渐被烤得脱落。即便肉体被毁灭,我还是可以活下来,但心灵若是毁灭了呢?
6月16 日 星期三(节选)
今天,我觉得自己好极了。明天我会不会死掉?就像上周,我在热浪中一睡就是一两天。
天气凉爽,明亮的日光照耀在街道上,有种奇怪的宁静感,仿佛我们生活的世界只是一场幻觉。我在夏洛特街上的一间希腊咖啡厅吃了午饭,买了些颜料和一本黑色日记簿。

贾曼电影《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海报。
10月1 日 星期五(节选)
奇迹中的奇迹!昨天我彻底出院了,现在我正等着坐上维珍航空的大飞机,经由纽瓦克飞往纽约。最近状态有些起伏,但是视力足以让我将就着活着,不过,在我眼中,万事万物依然像是处在暮光之中。
《蓝》大获成功,对这部构想简单的电影而言,有些影评夸赞得有点过火了,不过,我的确很激动。《蓝》登上了今天《纽约时报》影评栏的首页。大家都很开心。有一个年轻人曾被车撞伤,司机肇事逃逸,他在极度抑郁的情况下想要自杀,看了这部电影后,他决定继续活着。
原作者丨德里克·贾曼
摘编丨董牧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