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王青
“一个时代,哪怕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拒绝沉重,可总得有百分之一的人守望并解读沉重。否则,社会便会是一只轻飘飘的舢板,极易在风浪中倾覆。”
——《千年沉重》
“非虚构写作”,大概可以算是近年来泛文学领域的香饽饽。
以学术界为例。何伟的《江城》,梁鸿的《出梁庄记》等非虚构作品将艰涩抽象的学术概念揉碎进具体而微的个体叙事,降低了阅读门槛,也让更多普通读者看到了时代汪洋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与此同时,互联网工具的普及放大了个体声音,也引发全民非虚构写作的浪潮。在各类非虚构平台上,专业或业余的写作者们从个体的生活经历出发,或讲述自己的故事,或挖掘被掩蔽的真实,与读者们一同咀嚼来自生活与社会的复杂底色。
但当我们提起报告文学,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是个啥”。作为诞生于上个世纪的文体概念,报告文学早已退居文学的边缘。虽然有不少学者与评论家认为当下火热的非虚构文学其实是报告文学的“变体”,但报告文学在大众视野中的消亡已是不争的事实。
报告文学(REPORTAGE)是散文的一种,介乎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也就是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要求真实,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地,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往往像新闻通讯一样,善于以最快的速度,把生活中刚发生的事件及时地传达给读者大众。—— 茅盾《关于报告文学》
就文学的内在肌理而言,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都生发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也都关注被主流话语遮蔽的现实问题与群体的微妙情绪。但就主题内容而言,非虚构文学与报告文学相比,明显呈现出某种“退却”的特征,例如,非虚构文学不再流连于历史的沉重回忆,转而沉浸在个人化、碎片式的当下生活。
如果每一代作者都背负了不同的写作使命,从报告文学到非虚构文学,历史的沉重感为何消失了?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找到了曾是报告文学作者、现为非虚构文学创作者的胡平。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胡平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学时期以诗歌与小说创作为主,后有感于时代与家庭命运的沉浮,投身于“为时代发声”的报告文学创作。
近期,胡平出版新书《森林纪:我的树,你的国》,上架建议为“非虚构文学”。与以往著作不同,这本书不再着意描画历史跌宕与命运沉浮,而是以自然为切入点,乍读起来,像是一本关于自然历史的游记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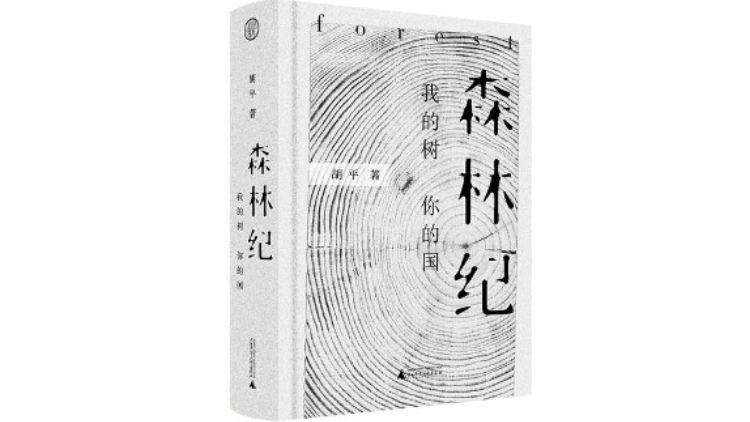
《森林纪:我的树,你的国》,胡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今天,胡平也更愿意被称为“非虚构写作者”。在他看来,报告文学是特定社会语境下的产物,当社会的底色变了,报告文学这一类型也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关于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关系,他认为,两者并不存在概念的交互或者延伸。许多非虚构文学作品看起来是“退却”了,但实际上是深入到人性的层面,关注更为内在的精神状态与时代命运。
“在当时,中国需要一种文体来承受‘不可承受之重’”:
从历史中心走向文学边缘的报告文学
新京报: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潮,也是报告文学的黄金年代。在众多文学思潮中,报告文学的发生背景是什么样的?
胡平:1980年代,中国的社会由阶级斗争转型为经济和平发展,回到常识常态。人们开始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重新审视曾经荒谬的、非人化的事件,也亟须将积压多年的情绪和话语一并吐露出来。最早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续不断有作品出现,掀起一股直面社会现实与历史进程的报告文学热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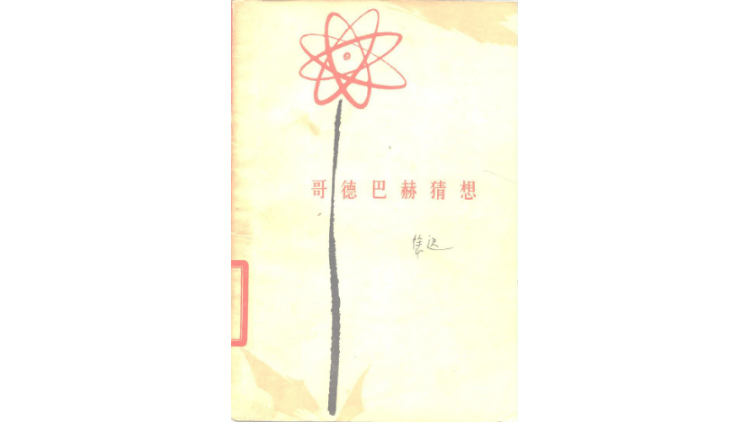
《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集》,徐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另一方面,媒体在那个时期还未完全打起精神来面对新的时代境况。于是,经历过惨痛历史的作家便主动开始书写介于文学与新闻之间的报告文学,借此充当时代的声音。
说到底,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个这样的文体,来承载过去许多的不可承受之重。
新京报:具体来说,当时的报告文学和虚构文学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如何看待这两种文学思潮的兴盛?
胡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许多小说界的知识分子惊觉中国文学的苍白,想要了解西方文学、外国文学的情况,也想要摸索出中国文学的新出路。所以,文学界出现了诸如寻根文学、朦胧诗,西方现代派、意识流之类的多元流派。
那么,谁来直面中国社会的本土问题呢?还得是报告文学。小说不是说没有,特别是一些经历过“反右”运动的老作家,像王蒙、张贤亮、从维熙等,他们也在小说中处理现实的很多问题。但报告文学直接面对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

张贤亮1984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肖尔布拉克》,收录他个人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土牢情话》,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坎坷生活。
新京报:有评论者认为,报告文学是个“舶来品”,进入到中国其实有100年的历史了,不同阶段,报告文学在内容、叙事方式上都有明显区隔。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胡平:严格来讲,报告文学是中国土地上一种比较独特的文学样式。它和西方的报告文学还不大一样。就我个人看法而言,西方的很多报告文学本质上还是非虚构文学,或者深度的新闻报道。
在当时,报告文学最大的作用就是对历史现象与历史真相的还原与反思。比如刘宾雁、苏晓康、卢跃刚等将原本老百姓接触不到的高层文件解密出来。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问题,重大的历史事件本身也需要时间的沉淀。到了这一时期,人们再回过头来梳理这些历史事件,找到了更清晰的逻辑链条。
新京报:好像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大家就不怎么提报告文学了?
胡平: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文学钟声已经不响了,众人喧哗也已褪去。一方面,文学走向商品化,人们阅读严肃文学的兴趣减弱,娱乐化的需求开始起来了。另一方面,中国的媒体也进入黄金时代,充当为时代、为社会发声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报告文学原有的社会功能就失效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报告文学其实是一种即时性的文学样式,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展开,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失。但同时,你说今天就没有报告文学了吗?其实也有,但它的作用已经不能与当时相提并论了。
新京报:我看到有些文学评论者将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做对比。你是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胡平:世界上的文字就两类,一个虚构文学,一个非虚构文学,这是普世意义的说法。在我看来,虚构文学主要是通过编织人物、情节、故事,来完成主题内容的创作。非虚构文学呢,它不能编织人物情节故事,而是以发现人物、情节、故事为前提,再通过作者本人的学识修养、人生阅历,以及思想的打磨来完成创作。对于非虚构文学创作者来说,只有把这三者融入情节故事,让现实与文学产生连接互动,才能延伸一个比较广阔的意蕴空间,让有同样感受的人,一看就能懂。
从客观上来讲,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没有所谓的概念的延伸。报告文学就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潮产物。当时代的背景变化了,报告文学的原本功能也就不存在了。
“不堪回首的记忆落满了我的身心”:
历史的沉重感从何而来?
新京报: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你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出身,大学期间也发表了许多诗歌。当时怎么会选择从虚构文学走向报告文学这种体例的?
胡平:大学的时候确实写了许多诗。但是这些诗歌虽然是诗的表达形式,主题和内容都是偏向现实主义的。比如,我在《上海文学》发表的第一首诗是《啊,人民》,第二首诗是《请你欣慰地闭上眼睛》,写的是彭德怀被平反的事情,都是一些现实主义的题材。

复旦诗社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合影(1982年)。前排左起:许德民、胡平、沈林森、孙晓刚,后排左起:汪澜、张真、曹锦清、景晓东、周伟林、韩云。
那个时候,各大文学杂志编辑涌进文学系的大学生群体之中,想要找到聚焦现实议题的创作,大家都需要感受时代的律动,反映人民的心声。
新京报:你早期的作品,包括上世纪80年代写下的《世界大串联》、《中国的眸子》,90年代的《战争状态》、《千年沉重——传统中国、乡村中国、内陆中国之文化描述》等,聚焦当代中国政治运动,透露出对历史的沉重感。为什么会特别聚焦这一类型的题材?
胡平:一个社会,大家活得都不容易,90%的人都是希望群众生活能够愉快一点,轻松一点。但社会总需要有些人要沉重的,否则,社会便会是一只轻飘飘的舢板,极易在风浪中倾覆。
我可能天生就是这种人,这也要从我的家庭经历讲起。我的父亲叫胡正谒,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法律系。后来辗转去了东北大学,又到了厦门大学教书。我出生于厦门。
1948年的时候,当时位于南昌的国立中正大学要办法学院,请到北大法学院的院长蔡枢恒(中国刑事诉讼法的鼻祖)坐镇。蔡院长是我父亲的恩师,很自然地叫了我父亲去协助。我们一家就此回到南昌,南昌也成为我成长的地方。
十岁那年,我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从那时候开始,整个家庭开始颠沛流离。当时,我的母亲要求进步,申请下放到农村改造,被分配在一个农场里,生活倒是还可以,也能吃到鸡蛋,米面。有时候,母亲也会将这些粮食送到县城,托人转交给我们。
有一年的6月份,是6月22号快过端午节的时候,她照常送食物给我们(从农场到县城要走一个多小时的水路),天太热,她在送过来的路上中暑去世了,但当时我们都赶不过去,周围也没什么熟人帮忙,最后她只能被随便葬在附近的山上。
我们家平反之后,我父亲和我想要去找坟迁坟。打听了半天,才找到当年埋我母亲的老农民。当时,他的年纪也很大了,记不清具体葬在哪里。我们只能到处挖,挖了好几条沟,也没找到。你想啊,挖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心境,我就不细说了。最后实在找不到,我们就把带着的酒洒了好几遍,点了爆竹,说明我们来过了。
从我童年一直到高中,这种不堪回首的、一地鸡毛的回忆,落满了我的身心。
新京报:除了家庭的影响,在复旦的那几年对你的创作有过什么影响?
胡平:最大的影响就是我明确了一件事——我写的每一个字必须是真实的,如果不是出于我心底的,不是真实的,我宁愿不写。
新京报:在早期的这些作品里,哪一部最能代表你对这段历史的思考,或者说最能代表你对历史之中个体命运的关注?
胡平:1949年以来,我所经历过的重大事件,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小人物的个体命运,我几乎都写进了过往的书中。比如,《玄机》 以1957年为视点,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整风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当代重大事件进行审视和反思,尤其关注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生存状况。更近一点的《瓷上中国》,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把瓷器、景德镇和中国三者结合起来,做历史追述和现实研讨,讲的也是中国瓷业在历史中的沉浮,陶瓷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

《玄机》,胡平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年10月。
如果一定说有一部,不如说是《玄机》这本书的一段话:“从晚清至今一百余年里,历史总是活在现实之中,时代的焦点与难题,虽然换了一张卷子,但题目总归是那些题目。”
“以森林为意向,实际关注背后的人和历史”:
从专注历史到关心自然,是一种退却吗?
新京报:这次出版的《我的树,你的国》可以被视为一部关注自然生态史的文学作品,和你以往的作品相比,不管是题材、风格、手法,都很不一样。当时为什么想要写这样一部作品?
胡平: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对森林是无感的。因为早年大部分时候生活在南昌,南昌附近没有森林,我也没有要寻找森林的想法。
大约是在2000年,我第一次去日本。日本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办法回避森林。日本的那种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观,像隆重的水墨画一样。日本人对岛上生物发自肺腑的深情也令我感动。从日本回来后,我发现自己对日本的森林很有感慨,但当时也还没有想到要写这个主题。
2010年以后,因为儿子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念书,我每年六月到十一月都会去那儿待一段时间。安娜堡有个别称叫“树城”,树非常多。每天早上,我一个人都会到林子里散会儿步,或者小跑一会儿。

胡平在安娜堡。
除了美国以外,我还去了很多国家,比如英国、加拿大、马耳他和意大利。每到一个地方,我有两个地方必须要去。一个是森林,一个是墓地。这么说吧,我几乎去过我所到过的所有国家的森林和墓地。
几年下来,我就很自然地想起要写这样一本书。在动笔写《森林纪》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明确,我既不是植物学家,也不是遗传学家,在自然相关的领域中,我就是一个“采花大盗”,不可能写得过专业学者。但是,我有自信能把自然生态跟人类的文明、人类的历史,以及一个民族的性格结合起来,穿插起来写,这是我的强项。

罗马台伯河畔。胡平/摄
新京报:近年来,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也是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本书中,你如何看待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你对自然或者生态文明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胡平:《森林纪》这本书,看上去是写各个国家的森林状况,内里最关键的是写森林生态对一个国家民族进程的影响。
我最主要的发现就是人类不能改造与征服自然,只能尊重自然,并且加以适度、有限地利用自然。
其次,人类只是大自然几亿万年来成长链条上的一段产物。人类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评判其他生命的命运,比如,谁比谁更伟大,谁比谁更好,谁比谁活得差等。
最后一点,自然的命运最能够透射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你只要看看山水、森林、动物的命运,你就能知道这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大概命运。如果森林给人的感觉是美妙的,自然舒张的,那么这个社会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长治久安的。
新京报:从关注历史到关心自然和地方文化,怎么会有这样的写作转向?
胡平:关心自然的背后其实关心的还是民族的文化和命运。历史本身就是人的命运组成的。看起来宏大的主题、事件等,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落到自然身上,也是整个自然的状况。

胡平/摄
我在之前的采访里也谈到过,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离“作家”这一身份越来越远。这其实和报告文学,或者说整个文学的衰落很相似。许多人认为我退却了,从一线退到二线,但实际上我是退到了人的层面,或者说思想的层面。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自己离“作家”这个身份越来越远。你如何理解自己在文学领域的身份?
胡平:我基本认为自己是一个非虚构写作者。但说实话,作家的身份都是别人叫的,我不需要标签化的身份,也不会将自己的创作局限在特定主题上。
我只关心我所要表达的东西,是否能如实地表达出来,读者是否认可我的创作,我所表达的观点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我不是畅销书作家,我的书如果能有一两万人愿意读,尤其是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同好愿意读,就算值了。
撰文|王青
编辑|张进
校对|李项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