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关于“家长群”众说纷纭,但归根到底,吐槽者居多,附议者居多,而更多的人则表示了自己“也想退群,但不敢退群”的两难处境。
事实上,“家长群”上热搜,引发全民关注,并非首次。就在上个月,“明天校门口见!”就上了热搜。两位小学生爸爸因为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在“家长群”约架,最终,第二天一早在学校门口,一位爸爸被另一位爸爸用U形锁敲破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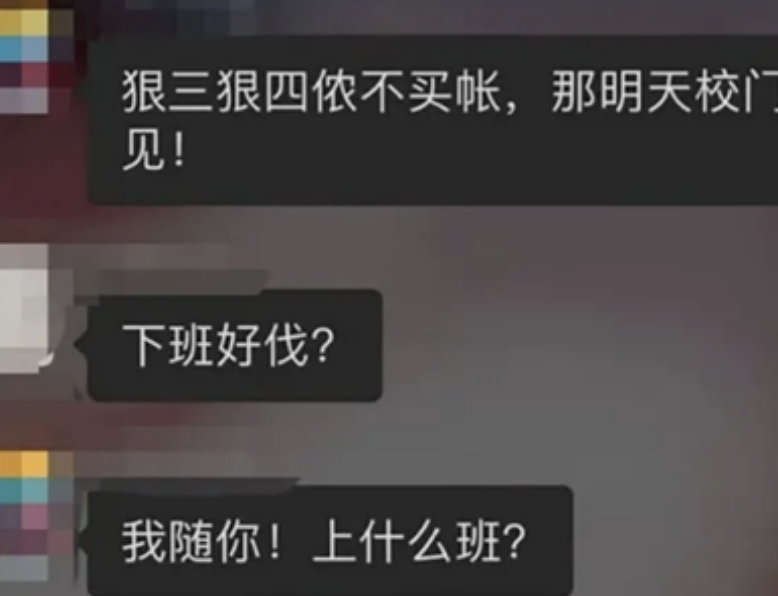
网络上流传的“家长群约架”截图。
除此之外,在“家长群”中炫富、攀比的现象更比比皆是,原本应该用于家校沟通交流的家长群,变成了“炫富群”“拼家群”“夸夸群”“争宠群”。学校里每个班级都会组建的“家长群”,俨然成了小社会,以致于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一种拍马屁叫‘家长群’,有一种炫富组织叫‘家委会’”。

网络上流传的“家长群炫富”截图。
“压垮成年人,只需一个家长群”“自从进了微信群,每天都是家长会”,看上去,家长们对于“家长群”积怨已久,老师们也满腹牢骚,一肚子苦水。显然,选择“愤而退群”的家长,绝不只有这位江苏家长,而一再引发大众关注的教育问题,也绝不只是“家长群”。
“家长群”该不该退,能不能退,敢不敢退?为什么“家长群”会一再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如何看待家长的种种焦虑?为何“家长群”会成为让家长和老师“压力山大”的“压力群”?家长和老师在共同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界限应该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蔡朝阳和安柏。
有过整整20年中学教学生涯的蔡朝阳曾是一位“麻辣语文老师“,以一本《救救孩子》引起过全国教育界轰动,与此同时,他现在也是一位初三学生的家长。安柏则是一位已经成功“上岸”的海淀妈妈,作为陪读妈妈,她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写成了《上岸》一书,希望她的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的心态和认知能够从焦虑摇摆,成长到坚定从容。
采写丨何安安
对话 蔡朝阳

蔡朝阳,文艺中年、资深奶爸、书籍出版人;曾为高中语文老师,人称“麻辣语文教师”,与推动学校语文教育改革的吕栋、郭初阳合称“浙江三教师”;2010年《时代周报》影响中国社会进程100人之十大教育工作者,2012年《新京报》年度教育书《寻找有意义的教育》作者,2014年“一席”年度演讲者。
1
“家长群“问题的根源,是扭曲的家校关系
新京报:江苏家长大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的短视频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在你看来,这位家长到底应不应该退出“家长群”?
蔡朝阳: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位家长是有道理的。确实,现在学校和家庭之间出现了一些关系的扭曲,学校和普通家庭之间责任和权利的问题有些倒置,学校方面过多地把学业要求加给家长,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位家长提出了很多关于学习的事情,所以双方之间发展到矛盾焦点的激化——就是彼此不能合作了,也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这位家长“愤而退群”倒是做得挺好的一件事情,至少让我们看到了矛盾激化事实的存在。同时,这也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焦虑的折射。前段时间《三联生活周刊》讲了一个封面故事,《“鸡娃”与自驱力:不焦虑方法论》,其实这位家长的故事也是焦虑的一种表现。
新京报:一些家长在认同这位江苏家长的同时,评论说:自己不是不想退群,而是不敢退群。
蔡朝阳:这个“家长群”问题,归根到底来自于扭曲的家校关系。一般,家长在加了“家长群”以后,不太敢得罪里面的老师。我们都知道的“画风”是这样的:老师说什么,下面都说“好”“好”“好”,大家都是非常服从的。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的小孩,尤其是初中以下的孩子,一天有近十个小时在学校里,处在老师的托管之下,我们看不到。我们也知道有些学校里经常会发生老师侵犯孩子——类似于体罚或者凌辱等极端事件。家长们迫切地想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是如何度过的?正因为家长不太愿意得罪或者说不太敢得罪老师,“家长群”里面就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权力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在小学和初中。高中以后会好一点,因为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他具有自己独立面对这些的能力。
退不退出“家长群”,我都觉得没有关系。事实上,作为一个初三的孩子的家长,我也一直在“家长群”里面,但是这个“家长群”里面在说的任何事情,基本上我是看不见的,因为我把它给屏蔽了。但是,有些具体的、事务性的东西,我还是会去看一看,比如说,明天早上要几点钟上学?需要带什么呀?今天什么时候放学?这些事务性的东西都会在家长群里面交流,微信群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交流的方便。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问题不在于微信群本身,以前没有微信,家校也在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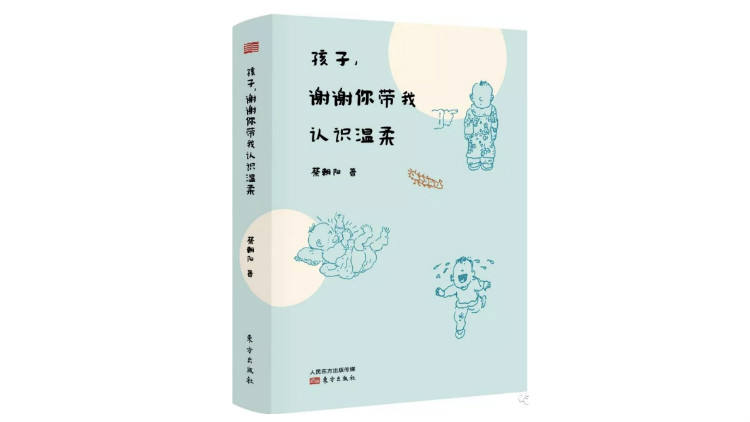
《孩子,谢谢你带我认识温柔》,蔡朝阳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4月版
2
互不越界,是良好家校关系的关键
新京报:是什么造成了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家校关系的紧张或者矛盾?理想的家校关系是什么样的?家长和学校应该如何分工?
蔡朝阳: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家校关系,因为每一个家长和老师都是个体,他们之间彼此沟通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相对较好的家校关系应该是彼此和谐的,让双方都知道对方的价值,在自己的框架之内不越界——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老师不要越界,家长也不要越界。但是界限的建立是非常麻烦的,它需要一个很长过程去形成社会的共识。我觉得这种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一种集体情绪,是整个社会的焦虑情绪在这件事情上的突然爆发。所以,我真的非常理解那位家长。当然,他采取的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但也是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
良好的家校关系一定是双方沟通顺畅,彼此尊重,这是我们都可以理解和承认的。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要有各自的边界:学校有学校的边界,家长也有家长的边界。学校的边界在于它的功能是知识传授、习惯养成,而家庭教育也有自己的边界,我们不能把这两者混杂了。知识的传授部分应该由学校来负担,家长要承担的部分是家庭教育以及对学校教育的辅助,包括孩子生活方面的照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很多学习任务压到家长身上。
新京报:如今,家校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了?
蔡朝阳:是的,这个边界非常模糊,导致家长也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家长了。我经常说,家长和老师,要把自己的职责分开,好妈妈(好爸爸)和好老师要把自己的责任分开。作为家长,要照顾好孩子的物质生活,让孩子在家里有安全感,让他安全长大,要拥有孩子的信任。而学习方面的东西最好由老师和孩子一起去完成,不要让家长越俎代庖。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制度性的设计,老师对于分数的要求非常高。学校里有一种评价体系,老师的很多评比项目,乃至工资和奖金,都跟学生的考试分数、平均分、优秀率紧密相关。老师非常看重考试成绩,因为考试成绩会给他们带来荣誉。他们对学生的成绩有比较高的要求,再加上学生人数多,管不过来,老师就会把这些责任转嫁到家长身上——这恰恰就是一种边界的模糊。
新京报:有没有办法对抗、避免或者说降低这种焦虑症的影响呢?
蔡朝阳:当然是有很多办法,我写过很多文章,也做过很多次公开演讲,都是讲这种东西。其实,如果我们对教育、学校、童年、儿童的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种焦虑就会降低。
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急功近利的,大家都在想: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然后每个人都在抢跑。这样其实非常不好。儿童的认知有时间阶段,他的大脑发育也有时间阶段。七岁的时候,你只能够理解七岁所能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老师、家长、学校都希望一个孩子在七岁的时候能够理解九岁或者十岁的东西,拼命地拔苗助长。这样怎么会不焦虑呢?
学校是孩子的一个生活空间。现在很多家长把好学校单纯地理解为:这所学校好,是因为这所学校可以让孩子的考试分数比较高,以后能够让他考清北,考985。但这是我们对学校这样一个空间的错误理解。学校是一段旅程,是一个让很多小伙伴在一起共同成长的环境。如果能够认知到这一点,那么焦虑也会显著地减轻。

《小别离》(2016)剧照。
3
日益脆弱的家校关系,
映射了这个时代的生存焦虑
新京报:“家长群”原本是帮助家长和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家长和老师之间的沟通却越来越薄弱了?
蔡朝阳:有些家长也会提出类似的疑问:我们交流的工具越来越先进,为什么老师和家长之间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在我小时候,我们与老师的关系是很好的。到了夏天,我高中时候的班主任帮我们家一起割稻子,割完水稻在我们家吃饭,因为当时我已经读高中了,他还会和我们一起喝一点点酒,这种关系其实是很和谐的。
为什么到了现在,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就变了呢?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时代的焦虑症在教育上的反应,它不是教育所特有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的生存焦虑。
在如今的环境之下,家长与老师在情感上的连接是非常薄弱的。它的薄弱就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把孩子看成是实现某样东西的工具。学校和老师都希望孩子能够考出好分数,以显示他们的教学成绩。家长也希望孩子考出好分数,以便实现清北的理想(或者985或者211)。孩子变成了一个实现他们目的的物品,不再是一个人,学校也不再是一段漫长的旅途。
新京报:实际上,不只是这位江苏的家长,包括老师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家长想“退群”,老师也想“退群”。站在学校、老师、家长不同的角度,如何找到这种和谐相处的模式,你有一些可以分享的经验吗?
蔡朝阳:我说了那么久,好像都没有为校方和老师讲句好话,对不对?事实上,我觉得该批评的确实是学校和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就教育这件事情,学校和老师是主要的施行者。理论上,学校和老师就应该是比普通家长更懂教育,应该更懂得孩子的成长是一件比较长远的工作。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和老师,就是因为他们是专业的,要帮助家长解决一些教育的问题。可是现在,老师反而加重了普通家长的焦虑。从这两个层面来讲,学校和老师是不是失职的呢?
我举个例子,最近一位老师很有名,她叫王悦微,是一个网红小学老师,也是我的朋友。她所在的学校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校,学生里面有很多外来务工子弟,他们的家长并不是知识阶层。但她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就是非常和谐的。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去做那些老师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越界。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学者,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他在近二十年前说过一句话:教育有问题,但往往不是教育的问题。“家长群”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但这些都是反映在教育上面的社会问题。引发我们的关注,就是因为它恰恰和孩子有关。孩子是所有中国家长的命根子,所以会引发我们的围观,引发我们的热议。但如果我们要去理解、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够单单停留在教育层面上,需要更多地从社会、心理等层面上去分析。
新京报:现在的家长,是否承受了比过去更多的压力?一些人评论现在的老师感觉和过去的老师大不相同。而老师也认为,失去了过去家长对老师的身份尊重。
蔡朝阳:当然,现在的家长比过去承担了更多的压力,但是事实上,在当下,我们每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哪一个不是比以前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压力?木心说“从前慢”,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是太慢的话,它会把你抛在后面。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关系,里面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成年人的社会普遍彼此不太信任。但我们把孩子送去一个普通公立学校,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基本的信任:就是当我们把孩子送去了这个学校,我们需要有一个最起码的对这个学校和孩子老师的基本认同,基本信任。万一在某一件事情上,我们觉得老师处理不当,可以私下里直接地、正面地跟老师沟通,就像有一本书的名字一样《非暴力沟通》。

《非暴力沟通》,[美]马歇尔·卢森堡著,阮胤华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8月版。
不要发生了某一件事情,就认为这个老师“他一定是在针对我,是给我们家孩子吃苦头”,这是一种敌我思维,在家校之间,家长要做一位智慧的家长。老师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正常情感的人类,我们是可以跟他们正面沟通的,这一点需要家长掌握好分寸。 我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叫作《父母:挑战》,和另一本著名的书,鲁道夫·德雷克斯的《孩子:挑战》是同一个系列。作为成年人,我们一旦成为家长,身上的职责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我们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的成年人,我们还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叫作父母。

《父母:挑战》,[美] 鲁道夫•德雷克斯著,花莹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6月版。
父母这个身份带给我们的挑战,每一件、每一样都是新的,都是前所未有的,父母是我们一生的修行,父母也是我们一生的学习。一旦成为父母,你所面临的有关孩子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碰到,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孩子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特殊的,往往是不具有可类比性和可复制性,每一件事情你都要认真对待,都要作为一件个体的事情来对待,所以这就很难。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当父母是很难的。
大概在1919年,我的绍兴老乡鲁迅,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转眼一百年过去了,今天,这位退出“家长群”的家长,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在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挑战下,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回答。江苏家长的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个契机,而不是一个终点。他让我们的社会、学校、家长和老师一起来思考,一起把自己的困境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样充分的讨论,才是达成和解的途径,达成彼此同情、彼此理解的途径。
对话 安柏

安柏,北大硕士、世界500强经理、教育领域自媒体人,海淀小升初、杭州幼升小亲历者。
1
“真正能做出退群的家长,
我还没看到过”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家长群”?作为一名资深“已上岸”家长,可以分享一些你和“家长群”的故事吗?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课,甚至需要去学校打扫卫生,协助老师完成其他的一些工作,这些事情你遇到过吗?
安柏:我加入的“家长群”,除了花生(《上岸》中的主人公)的班级家长群、年级家长群,还有在小升初阶段进过一些小升初群,为了获取一些资源,以及进行信息交流。还有就是课外班的家长群,老师会在群里告诉家长督促孩子做作业、交作业、发资料等。我加入的班级家长群,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的,像批改作业、打扫卫生等情况,在“家长群”里发生的比较少。一般就是需要证明孩子有些事情做完了,最多签个字。
但据我所知(在我的上一本书里也写过),一些更小地方的学校,也许是出于师资力量的原因,会有一些老师要求家长帮忙打扫卫生、批改作业等情况的发生。很多家长也热心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愿意,还是听老师的话),包括开运动会、音乐会时,帮助学校布置礼堂、摆放桌椅等。我个人觉得,老师布置的工作,家长吐槽的并不多。新闻中提到的江苏家长是位爸爸,感觉“家长群”里更多的是妈妈。妈妈在处理这些事情时,可能会比较柔和一些,就好像觉得这些事情是应该做的,会更小心一点儿处理这些事。
另外,从今年疫情以来,“家长群”的事情的确多了。因为那会儿孩子在家里学习,很多事情老师会通过家长布置,包括打作业、交作业、拍照、上传、打卡等,有些孩子非常小,这些事情孩子自己没法处理,家长就会很忙。 这里边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自从疫情孩子在家学习以后,很多家长都意识到,其实在学校里老师还是做了很多事,学校也帮助家长减轻了很多负担。毕竟孩子在学校里,比如早上八点钟开始上学,下午四点钟放学,那段时间家长是很轻松的。

《上岸》,安柏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0月版。
新京报:在你看来,是什么造成了学校和家长之间矛盾的激化呢?为什么“家长群”会引发这位江苏家长的“愤怒”?你是如何处理家长和学校、老师之间关系的呢?
安柏:我觉得家校关系变得紧张,是因为现在孩子的负担重了。比起我们小时候的作业量、学习量,现在几倍,甚至数十倍都有可能。我们那会儿根本就没有什么作业,老师也不用批,家长也不用管,大家都挺开心的,但是现在的学习量、作业量,包括家长自己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可能也是挺高的,就造成了这种压力,不光是对孩子,对家长、对老师的压力也非常大。
作业量布置多了,有些老师一个班有40多个人的作业要批改,可能让家长帮着对对答案,或者让孩子自己去自改,如果孩子不是很自觉,或者家长没有时间,那么作业的质量怎么样,反馈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觉得这也是引起矛盾的一个原因。
当然,现在“家长群”很多消息可能是学校布置的任务,比如之前的疫情,有没有去过疫情暴发的地方,家长需要接龙,还有上周的诺如病毒,这些事家长不得不去做,老师也不得不去管,其实也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
我和老师的沟通是比较主动的,老师布置的任务,我会第一时间完成,如果没有及时看到,老师也会来提醒我。大家互相理解。 新京报:面对这些问题和困扰,家长应该或者说可以“退群”吗? 安柏:我觉得这种情况下,退群可能是一时的气话。真正能够做出“退群”的家长,我还没看到过。在学校里,万一有什么事,倒霉的还不是孩子吗?你可以说孩子在学校里,应该由学校负责,但最终孩子还是自己的呀。
2
只有在合理的期待值下,
孩子才能发挥得最好
新京报:家长和老师,应该如何区分彼此的界限呢?
安柏:家长和老师之间的界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空间上的界限。就是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基本上不应该家长去参与,除非是邀请家长进课堂,或者邀请家长参加运动会、开放日等活动。还有一个界限,就是时间上的界限。孩子在学校里这段时间,全权由老师来管,然后回家以后的时间,由家长负责。但是,学校布置的作业,家长其实也有监督的责任,至于批改作业的责任,我认为主要还是应该在老师身上。
其实不光是陪孩子写作业,批改作业,还有一个令家长苦恼的事儿,就是孩子回家以后没有自主的时间。特别是上了初中以后,因为作业比较多,能用于阅读、运动的时间都比较有限。现在这种这种情况的发生已经越来越早了,就是一二年级的家长,都觉得孩子的时间不够用了。还有一些家长也给孩子加任务,这样,睡觉的时间也越来越晚。我觉得,包括一、二年级的孩子,能够在九点半以前睡觉的应该是凤毛麟角吧。当然,这和家长的焦虑也有关系,比如我在《上岸》里提到的小布丁的故事。这件事情需要家长去做减法,而不是加法,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对待。
新京报:海淀区是家长圈里公认的“牛娃聚集地”之一,而你恰恰是一位“海淀妈妈”,感觉压力大吗?有没有办法减压?
安柏:在某一个阶段,比如升学,可能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重要,升学只是某个阶段的外在体现,但内在的品格、实力,不会因为外在的变化而改变。
在升学过程中,我们付出努力,但是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比如幼升小、小升初没有进入好学校,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得到了成长,这就是进步,他获得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想要减压,需要你对孩子有合理的期待值。这一点我在《上岸》中也提到了,孩子在不过高也不过低的期望值下,才能发挥得最好。这一理论并不是来自于教育,而是员工管理,如果老板对员工的期待值太低,员工不会发挥好,但如果期待值过高,他的压力又会太大。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家长如何合理地看待孩子。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牛蛙”,对标1%的人群。减压的根本在于我们能不能接受如果孩子是普通人,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普通人的最好。家长应该去鼓励他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采写|何安安
编辑|张婷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