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的教堂里,陈丹青一身黑衣,登上了梯子,仔细端详着教堂里的壁画。
几百年来,大家只能仰望教堂里宏大的壁画。绘画本身的魅力被空间的距离所稀释。只有画家本人、壁画修复师和特许的摄影师能够登上梯子,以平视的角度,贴近观赏这些大壁画。
“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奢侈的经验”。陈丹青在《局部》第三季里说。在近距离的凝视中,古老的壁画被唤醒,观众们似乎能听到画家的心跳。

陈丹青
作为一档艺术节目,《局部》与当下流行的那些成体系的、讲述艺术知识、起着艺术教育作用的艺术节目和知识付费内容不同,更像是一位画家个人的观看和叙述。《局部》第一季像是跟观众漫谈,陈丹青讲王希孟,也讲卡帕齐奥;第二季则去到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陈丹青带领观众欣赏陈丹青的“大学”。在《局部》的第三季,陈丹青去到了意大利,专门讲述意大利的湿壁画。
尽管讲述的内容贯穿中西古今,但这三季《局部》一直贯穿着陈丹青的“观看之道”——他拒绝艺术史家整体性的知识讲述,而是以画家的视角挖掘那些被艺术史埋没的天才——在第三季里,他不去凑大家耳熟能详的“文艺复兴三杰”的热闹,而是讲那些被艺术史所隐没的文艺复兴“次要”画家:乔托、马索利诺、科萨、弗朗切斯卡……陈丹青不讲述知识,他主张观看者要忘掉艺术史,要与艺术素面相对。他相信大家拥有直面艺术的感受能力,他只负责将大家领到这些作品面前,做一些撩拨人心、点到即止的讲述。
在信息爆炸时代里,众声喧哗的信息场域一直喧闹不停。知识变得唾手可得,我们的注意力却变得涣散。我们似乎已经丢失了那种宁静的接受艺术的能力。另一方面,工业革命、艺术学院的出现以及媒介的剧烈变迁,也深刻影响了艺术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个时代到底需要怎么样的艺术?这个时代又需要艺术家在社会上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好的艺术教育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何艺术学院培养不出伟大的艺术家?陈丹青对学院的犀利批评也许会引起争议,但这未免不是看待艺术发展的另一种角度。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与陈丹青聊了聊看待艺术的“观看之道”,以及其对艺术教育的看法。

陈丹青将《局部》三季讲稿结集成书,从左到右分别为《局部:陌生的经验》、《局部:我的大学》、《局部:伟大的工匠》,陈丹青著,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采写 | 徐悦东
(实习生吴俊燊对此文亦有贡献)
“忘掉艺术史,才能与艺术素面相对”
新京报:在《局部》第三季,你去意大利讲文艺复兴湿壁画。为何《局部》第三季会讲文艺复兴?你在《局部》第三季里没有讲大家耳熟能详的“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这又是为什么呢?
陈丹青:文艺复兴基本是欧洲绘画的源头。在文艺复兴之前将近一千年的中世纪里,欧洲并没有出现特别重要的绘画。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塑很精美,但也没有出现特别重要的绘画。欧洲的绘画传统差不多是文艺复兴时期开启的。
此外,一百多年前,西方美术知识传入中国。那时,大家介绍西方美术时,都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因此,我们应该弄清楚,中国所接受的西方美术叙述的源头到底是怎么样的。

“文艺复兴三杰”(从左至右: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
我之所以没有讲“文艺复兴三杰”,是因为《局部》不是一档艺术史节目,我不必按照艺术史的排序和重点来讲。其次,“文艺复兴三杰”已经被大家过度谈论了,书写他们的著作数不胜数。大家过度谈论“文艺复兴三杰”,也遮蔽了文艺复兴时期其他二三十位重要画家。这些画家在欧洲都是很知名的,但在中国不太出名。
在拍《局部》第三季前,我走访了意大利的许多地方,考察了三个月。我发现,“文艺复兴三杰”是文艺复兴晚期或盛期的人物。在他们出现之前,意大利已经诞生了很多重要的壁画家。我希望我能讲一些被艺术史忽略的重要人物。

《局部》第三季剧照。
新京报: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文艺复兴三杰”是这些被忽略的文艺复兴画家的“集大成者”?
陈丹青:我有时不太同意“集大成者”这个说法。“文艺复兴三杰”只是处在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成为了最被后世关注的人物。
我们不能说唐朝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大成”;我们也不能说元朝集了唐宋的“大成”。其实,每个阶段都有其最高点。当一个阶段过去之后,艺术的样态就会变成另一种样貌。唐画与宋画之间有传承的脉络,但未必是“集大成”的关系。没有人可以“集大成”。我不太相信艺术史所使用的一些词语。
新京报:你选择讲这些画家似乎跟你在《局部》里会讲一些“次要”的讯息相关。比如,你会选一些“次要画家”,或者著名画家的“次要作品”。而且,你不仅关注作品和创作者本身,你也会关注与作品相关的次要信息,比如,历史、时代、文明。你能给我们讲讲你的“次要主义”吗?这是否能体现出你对正统艺术史观的某种质疑?这可以理解为一种“自由地观看”的态度吗?
陈丹青:当我说某些作品“次要”的时候,并不是在说这些作品真的“次要”,而是说它们被历史叙述中的重要作品遮蔽了。达·芬奇之前的画家远比达·芬奇本身重要。我在《局部》里讲的这些画家,在达·芬奇还在世的时候就比达·芬奇重要。
弗朗切斯卡比达·芬奇老一辈,后人将他遗忘了将近四百年。到了二十世纪,弗朗切斯卡才被人们被“重新发现”。我们不能说弗朗切斯卡是“次要”的。
其实,“重要”和“次要”这两个词语都不对。我主张观看时,我们要忘掉艺术史。艺术史是一种归纳。面对艺术,我们不需要归纳,我们只需要直面艺术本身。而且,我们所接受的艺术史叙事中,通常都是一种带有权力的叙事。这种叙事会选择性忽略掉许多人。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被灌输的概念,都妨碍我们与艺术本身的素面相对。
当然,我们不是不需要了解艺术史。艺术史是一个“账本”,我们需要了解“账本”,但我们不能被“账本”带着走,更不要完全相信“账本”。

《局部》第三季剧照。
新京报:的确,对于许多普通观众来说,他们“看不懂”艺术作品的原因,可能是缺少艺术史的背景信息,也可能是被艺术史的叙述所束缚住了。
陈丹青:自从艺术史这个学科出现后,美术就跟“前艺术史时代”变得不一样了。“前艺术史时代”的美术作品,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具体场所——为了让信徒做礼拜,美术作品会出现在教堂里;为了展现有钱人的财富,美术作品会出现在贵族家里;为了歌功颂德,美术作品会出现在王宫里。艺术品并不会出现在博物馆里,也不会出现在艺术史里。
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完成了艺术民主化的过程。博物馆里的艺术品允许大众参观,贵族的艺术收藏也对大众开放。从这时起,大众开启了一段漫长而尴尬的历程,这个历程直到现在都没有终结。一方面,大众知道这些艺术作品很美;另一方面,大众又怕自己看不懂。所有古代艺术在进入博物馆或艺术史后都被神圣化了。这其实是权力话语夸张出来的效果——这个艺术作品里面有很多学问。当大众看到太复杂高深的东西,自然就会退缩。这些权力话语都应该被去掉。
中国也是如此。以前,平民是看不到皇宫里的艺术品的。进入平民时代后,尤其在传播时代到来后,大众可以通过印刷品或音视频媒介,接触到许多以前看不到的艺术品。但是,大众很难消除在知识面前的自卑和恐惧。《局部》就试图缓解大众的这种紧张感。我假定,我们每个人都能看懂艺术。所谓“看懂”艺术,指我们面对艺术时能“看进去”、能爱上艺术或被艺术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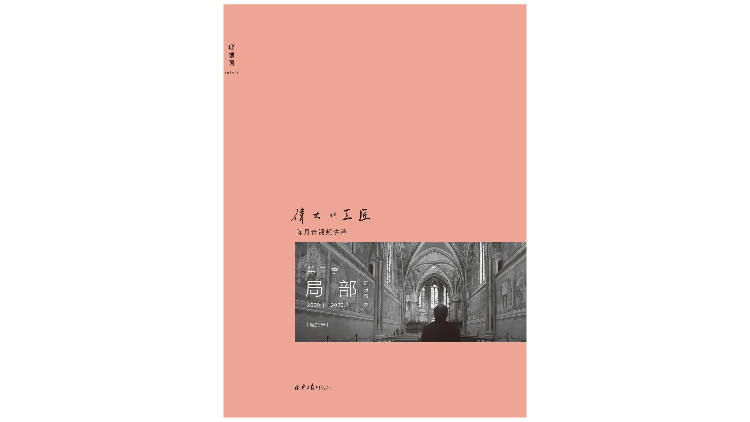
《局部:伟大的工匠》,陈丹青著,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年12月版。
新京报:我发现你的“观看之道”里很强调媒介以及媒介在那个社会中的角色,比如你曾多次将湿壁画比作电影。大众似乎较少从这种角度出发去理解艺术。你为何会做这样的媒介之间的比较?你觉得理解媒介本身对理解艺术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
陈丹青:理解媒介本身对理解艺术的功能有作用。我们现在喜欢笼统地说,艺术是美的。但是,在当时的老百姓看来,他们不会对作品持有我们今天才拥有的概念。他们会崇拜教堂里的画像、会为此迷狂。所以,绘画在那时比现在重要得多。绘画就像最高命令一样,告诉大家某位神的脸就是这样的,观看者也会相信。现在,一切都被祛魅了。
因此,古代的大众不一定会认为,艺术作品是美的。美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概念。在中世纪或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在公共场合所看到的艺术品,一直起着一种教育和被崇拜的作用。美是一个晚近且备受争议的概念,现代的大众容易在这些争议面前忘记如何去直面艺术。
“艺术史家们没有画过画,不懂绘画的痛痒”
新京报:你做《局部》的时候,有参考哪些艺术节目吗?你有什么喜欢的艺术节目?
陈丹青:我做《局部》时没有参考其他的艺术节目。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纽约后,发现有西方学者在电视节目上,向大众讲述西方艺术史。现在BBC和美国的公共电视台还在做类似节目。我也看过中央电视台的一些纪录片,比如《卢浮宫之旅》和《故宫》。我没想到,我有一天也会做这样的节目。
我当时非常崇拜这些艺术节目。但是,我看多这些节目后,就觉得不满足,因为所有讲课者都是艺术史家或理论家——他们没有画过画,不知道绘画的痛痒,没有说出艺术最打动我的地方。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艺术节目都在讲知识——这件作品是哪个年代创作的,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作品,创作者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等。这些节目不会去讲这件作品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因为他们不一定说得出来。所以,我蛮早就不是很相信这些权威讲述。等我自己讲艺术作品的时候,我试着将我画画的经验,融入到我所理解的艺术作品当中去。
实践的经验非常重要。我能看出艺术史家们看不见的东西——虽然我没有那些伟大画家们画得那么好,但我跟他们一样,都是一个要将白布涂满的人。我很清楚,一名画家在画画的过程中会遭遇什么问题、会获得什么快感、会面临什么挑战。

纪录片《卢浮宫之旅》截图。
新京报:你曾说你做《局部》不是讲知识、讲道理,不是教育节目。如今这个时代,知识付费盛行,你是怎么看待像知识付费这样的模式,在艺术普及的领域里的表现的?此外,短视频这种媒介形式的普及,对大众的艺术普及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丹青:我一点都不想获取知识,我想获取感受。感受里面可能包含知识,但知识里面不一定包含感受。我很反对知识付费的说法,这是一种非常功利化的语言。
短视频未必会对艺术普及产生很大的影响。从学问的方面来看,我不认为短视频流行之后,我们会比只通过书本和刊物来获取知识更好。虽然我们能非常及时地在任何地点获取任何知识点,但我们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只会变得越来越少。对于获取知识来说,这是灾难性的。在短视频中,我们能获取趣味,但是不一定能获取知识。知识需要连续性和纵深度,只靠短视频,知识是累积不起来的。
新京报:这也是你第三季每一集的时长比前两季稍微长一点的原因吗?
陈丹青:那倒不是。这是因为《局部》第三季的内容分量重了。我很难在十分钟内把一个教堂的湿壁画讲明白。二十分钟已经很短了。我讲画是有策略的:我不会给观众详细地分析这张画,而是把知识变成故事——故事里肯定蕴含着趣味。我假定,一幅画呈现在观众面前,我只需要做一些围绕性的讲述,观众就能自己欣赏一幅画。这种方法是奏效的。大众只需要一个将他们带到作品面前的中间人,我可能就是那个中间人。

《局部》第三季剧照。
“绘画自由之后,社会就不需要那么多艺术家了”
新京报:你在《局部》第三季里讲到艺术和工匠的关系。文艺复兴大师仍属于工匠传统,但社会发展到后来,工匠传统没落了。现在,其实很多人也从事着类似工匠般职业,做着工匠般的活,大家可能会夸他们很有工匠精神,但是大众不会将他们所做的称为艺术。你是怎么看待这种工匠传统?又是如何看待工匠精神的?工匠能为现代的艺术创作提供什么样的养分?艺术家和工匠有什么样的关系?
陈丹青:工匠传统只存在于手工业时代。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后,手工业没落了。有一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写了1920年左右的一个英国人,回忆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到鞋匠那儿做鞋。后来,制鞋业出现了,他亲眼看着给他做鞋的两个鞋匠被时代淘汰。他能买到很多皮鞋,但是他小时候那种有温度的、有几百年传统的、按照他的脚来定制的皮鞋再也不会出现了。
绘画的变化跟工业革命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联系,但是工业革命促使了印象派的出现。印象派的出现标志着雇主与画家之间的订件关系消亡了——以前,艺术家被有钱人、帝王或贵族所雇佣的。这种雇佣关系消失后,艺术家们画了画,等着别人来买,而工匠开始走向低端。
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到十八九世纪,工匠还在为高端作业做订件。到了二十世纪,工匠只能做一些低端作业。现在意大利的许多工匠在仿制一些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的雕塑。他们的作品质量非常差,因为他们的客户也变“低”了。
今天,我们提倡工匠精神,这反而证明工匠已经没落的事实。在工匠时代,世界上不存在着“工匠精神”这个词——因为工匠们都会遵守相应的工作伦理,让其作品维持在某个水准之上。

《局部》第三季剧照
新京报:你曾多次说过,最伟大的艺术都出自师徒制,自从出现艺术学院之后,绘画的本能和元气渐渐磨灭。这是为什么呢?学院制度的问题在哪?
陈丹青:早期学院就是作坊。作坊非常注重实践,所以才发展出师徒制。学徒们的学习面很窄。文艺复兴的许多工匠早期都是学金匠出身的。金匠只负责打金器,具体牵涉到如何运用材料、如何设计造型等非常具体的手工活。学徒们在学习做这些手工活的时候,他们能学到全方位的技能。
学院的出现是场灾难。18世纪左右,在学院派出现后,此前积累了四五个世纪的艺术传统,开始被人们归纳成法则——造型法则、色彩法则、构图法则等。学院派认为,他们只要在学院里把这些法则教给年轻人,就能培养艺术家。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样是培养不出艺术家来的。自艺术学院诞生以来,世界上就再也没有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了。
当一类艺术被归纳为法则时,这意味着这类艺术差不多走到尽头。20世纪的学院没有培养出一个印象派画家那样的画家来,也没有培养出毕加索。但艺术学院反而从此变得膨胀,因为它释放出一个伪信息——只要到艺术学院来,任何人就能成为一个艺术家。艺术不是法则,对于艺术来说,最重要的是感觉和操作。这些东西只有师徒制才能传授,学院是做不到的。
新京报:可以这样理解吗?通过归纳法则的办法,学院能批量生产一批平庸的艺术家?
陈丹青:平庸的艺术家越来越多。为何会有现代主义?为何会有后现代主义?为何会有当代艺术?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们要不就不是学院培养出来的,要不就是背叛学院的人。今天,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仅靠学历堆积起来,在全世界都有重要影响力的艺术家。

《局部》第三季剧照。
新京报:对于很多人的艺术生涯来说,进入学院本身也相当于一块进入该圈子的敲门砖。如果很多有天分的学生要是考不进学院的话,他们的艺术生涯会更为坎坷吧?
陈丹青:一旦学院在社会上定型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权力机构。权力机构建立在一些它认为不可动摇的规则上。比如说,他们需要招大专生或本科生或博士生,没有这个学历的学生就要出局。
艺术根本就不需要学历。我在《局部》第三季里讲的好几个画家中,有些画家十二岁就进了画家同业公会。在他们十七八岁的时候,他们就单独负责绘制整一个教堂的壁画了。在学院里,这是不可想象的。但问题是,以前这种雇主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消失了,艺术家都变成了自由艺术家。其实,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艺术家。
现代艺术最奇怪的一个悖论在于,当绘画自由以后,需要艺术家的时代过去了。第一代现代主义艺术家是最幸运的——我指从后现代派到毕加索那代人——那时候艺术正处在刚解放的时期。此后,西方艺术界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许多艺术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为了谋生,十之七八的毕业生最后都放弃了艺术。
在文艺复兴时期,直到十七、十八世纪,一名艺术家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到了一个可被雇佣水准。他们能完成一定水准以上的作品,才有机会成为艺术家。
新京报:但艺术学院也是艺术民主化的标志之一。
陈丹青:对,艺术处在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民主化是一个反精英的过程。但我们不得不说,最好的艺术还是精英做出来的。在文艺复兴时代,哪怕艺术家是工匠,他们也是精英。

《局部》第一季剧照。
新京报:想起一个在网上看到的段子:许多艺术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去补习机构教艺考,教下一批人怎么考入艺术学院。这是个奇怪的循环。那你觉得什么样的艺术教育才是最好的艺术教育?师徒制能给我们现代社会的艺术教育什么样的经验?
陈丹青:现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什么是最好的艺术教育”,而是“艺术教育从业者不知道艺术教育的路该怎么继续”。没有人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还需要什么形态的艺术。自由艺术诞生至今百年左右,艺术家什么都能做。但大家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当艺术家什么都可以做时,社会到底需要哪种艺术?
尤其在数码艺术兴起后,我们所需要的艺术早已经不是传统的绘画与雕刻了。我以前总说,今天最好的艺术其实是美剧,因为它的需求量是最高的。假如没人看,投资方就回不了成本。如今,美剧依然维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从剧本到导演再到表演,质量都超过了电影。
此外,时尚业的需求量也很高。任何好的艺术都一定是一种有市场的艺术。今天大部分的自由艺术是没有市场的。他们假定有一小群人要搞收藏,然后再选择几个最惊世骇俗的艺术家。一种没有市场的艺术,一定会在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上首先开始萎缩。
媒介的变迁,为艺术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新京报:你曾多次提到,现在不是绘画的时代。这让我想到有作家偶尔会感叹“文学已死”。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老媒介的相似命运?
陈丹青:这个问题蛮好的。这就是老媒介的命运。手工业时代和初期工业时代过去后,传统的小说和绘画就没落了。现在,电影都快没落了。电影是初期工业时代的产物,现在已经是后工业时代了。后工业时代的新媒体能带来什么样的艺术?现在出现各种各样的数码艺术是目前最重要的艺术。
新京报:是不是这些老媒介最终都走向了自身的“内卷”?虽然大众市场需求量相比以前在减少,但评论家们还能继续在学院里不断生产批评,创作者在形式上继续穷尽突破的可能,尽管这越来越难。在这个时代,这些老媒介所承载的艺术,又该如何获得新生?
陈丹青:是,它们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但还养着一大群人。我的意思是它们现在已经对人类的大历史进程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了。文学和绘画还会一直苟延下去,因为依然还有好多人喜欢读文学、看画,但文学和绘画的受众只会越来越有限。
美剧会一直火下去,因为大众喜欢看故事。我不知道未来美剧会不会成为一种艺术种类。美剧火起来才不到几十年的样子,像Netflix火起来才不到十年,HBO火起来才二十多年。我也不清楚未来美剧会怎么走。

Netflix纪录片《抽象:设计的艺术》第二季截图。
新京报:你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在媒介爆炸的年代里,我们失去了宁静内向接受艺术的过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接受艺术的过程?
陈丹青:我小时候没有博物馆、画册和影像。当然,我小时候跟前媒体时代还是不一样的——真正的前媒体时代连书都没有。人们是需要匮乏的——由于没有什么媒体可看,当发现一个媒体的时候,我们就会全神贯注,并刻骨铭心地接受信息。我们再也不会拥有这样的时刻了。
如今,我们接受知识的速度很快,但据说我们的注意力时长不超过八秒钟。时不时看手机都成了我的一个生理动作。我已经失去了小时候曾有过的那种体验——拿到一本书,就像吞咽一般的阅读,并全部记住书中所写的内容。我们的心都散掉了。
但我相信,这样的媒介环境会孕育出另一种文化——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我很期待另一种小说、电影的出现——即用一种非常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创作出来的。这种艺术得零零后才能创作的出来。因为零零后自两三岁开始,就进入了注意力分散的媒介环境里。人永远都拥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当他们拥有这样的感受力时,相应的艺术才能被创作出来。
新京报:你曾劝青年学生少在画架上作画,你自己会不会也去拥抱新媒介进行创作呢?
陈丹青:《局部》就是我的新媒介作品。我为什么愿意放下我的画,花那么多时间去做《局部》?因为这是一件非常新的事情。我不认为《局部》是艺术品,但它跟艺术有关。《局部》是我晚年做的唯一有价值的事情。对我个人来说,《局部》比我在清华美院教书有价值得多。
我完全没有想到,《局部》居然能影响到小孩。今天有一个八岁的小孩找我要签名,他每一集都看过。此外,还有许多服务员、公务员和农村人都看过《局部》。我很高兴《局部》能够被那么多人同时接受。他们平时都不太看我的画。我自己也不太看我的画,我只是自己喜欢画画。

陈丹青
新京报:有人说你的“画册”系列有一种“绘画的末路感”在背后驱动着你。这也体现出一种媒介变化自觉性和反思性。所以,有人说在这个意义上你自嘲的“退步”也好,“荒废”也好,即使没有逃脱画框,但其实整个行为都挺当代艺术的。你是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陈丹青:我不在乎这是不是当代艺术。我用的媒介还是最传统的媒介——画布和颜料。我画的东西也都是平面的,谈不上有任何新的地方。我只是诚实地面对我们这些画家的处境。实际上,绘画是没有前途的,但还有人像我一样,喜欢自己玩一玩。将来再过一百年,如果依然有人愿意看我的画,那我至少会承认,目前绘画面临的不是绝境,是个困境。
我不会假定我正在做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局部》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许多拍电影的人都很羡慕我,他们说,我卖150块钱的票居然都卖光了,这个票价对于电影来说是很贵的。我在上海放了四场,全都卖光了。这说明大家有需求,即便这个需求量没有那么大。我很高兴。对我来说,办画展没什么成就感,因为画展本身就是一种很老的形式。如果画廊不找我,我不会办展览。

陈丹青的《巴洛克群像之二》布面油画。
“一切深度都在表象里”
新京报:你说你现在画画重视皮相,要透过本质看现象。承载社会意义的深度刻画似乎不再流行。你能详细谈谈你所认为的表象与深度吗?
陈丹青:表象一点都不等于不深刻。如果创作者能创作出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表象,所有深度都在里面了。没有深度的表象,意味着创作者没有抓住表象。一切深度都在表象里。
表象和表层是两回事,但是在物质上是一回事。在绘画里,有一句行话叫“surface”,“surface”指表层。有人夸你“your surface is so good”是在夸你的表层做得很好;我们还有一个行话叫“凝结层”,颜料的堆积、覆盖、凝结形成了绘画的魅力。
如果一名画家能找到好的表象,那他的表层也一定很好看。文学也一样。好的心理刻画,可以从很表层的对话描写和情景描写中着手。好作家能在此展现出非常可怕的深度。我喜欢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描写,他们的作品看起来啰哩啰嗦——他们所写的都是表象,但这些表象给人的感觉非常深刻。二流的小说家才会忍不住站出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
我的画也谈不上什么社会表达。我从来不认为我的画为社会提供了什么。《局部》倒可以为社会提供一点东西。
新京报:你觉得绘画中的现实主义还有未来吗?
陈丹青:现实主义早就过去了,因为绘画能承载现实的能力太有限了。电影出现后,绘画还玩什么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离不开叙事。一幅画在叙事上怎么玩的过电影和连续剧?这句话我也在《局部》里面讲过。
但是,有一个导演对一个放弃绘画去学电影的学生说,博物馆还是要去的。绘画不会说话,也不会动,但绘画更长久。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不太能想象五十年后还有人想看《后翼弃兵》和《国土安全》。但是,几十年后甚至上百年后,可能还会有人愿意看画。这是另外一个很诡谲的话题。

陈丹青
新京报:你是如何看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你如何看待这两个角色在你身上的结合?
陈丹青:今天艺术家对社会几乎没什么影响,除了做影像的,比如做电影和连续剧的艺术家是例外。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中国可有十几亿人。知识分子对社会也没什么影响力。过去十年来,大家有过静下心来听知识分子讲话的时刻吗?没有。
新京报:比如,你讲话大家还是会关注的。
陈丹青:那只有很少人在关注。我一点也不夸张,我过去社会批评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如果我也有影响力的话,那么我应该承认,社会上至少还有一百名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其实这些知识分子合起来的影响力都非常有限。
在良性的社会里面,知识分子的确应该要有影响力。但是即便在美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差。知识分子跟乔布斯、比尔·盖茨的影响力根本没法比。
新京报:今年是充满变动的一年,你今年过得如何?你在今年疫情期间是如何度过的?
陈丹青:我在疫情期间在做《局部》这套书。我跟大家一样,在疫情期间也动弹不得。但是,跟年轻人相比,我并不觉得今年很糟糕,因为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今年对年轻人来说,也是个警告:好日子过久了,年轻人都觉得世界就该是这样子的,疫情忽然就来了。我当然希望明年疫情赶紧过去,人类总会想出办法的,现在疫苗就快出来了。
新京报: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陈丹青:不要问老人这种问题。老人没有未来。老人的未来就是坟墓。我差不多有资格这么说了。
采写 | 徐悦东
编辑 | 王青
校对 |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