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英] 迈克尔·阿克斯沃西
摘编 | 徐悦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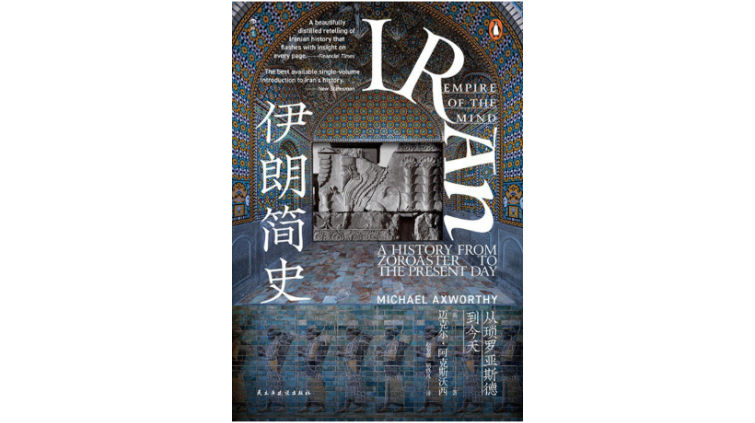
《伊朗简史》,作者: [英] 迈克尔·阿克斯沃西,赵象察/胡轶凡译,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列王纪》给了伊朗人以身份认同感
从一开始,波斯诗歌的宏伟主题就是爱情。这是一片充满爱意的大陆——性爱、神圣之爱、同性之爱、不求回报之爱、无望之爱与有望之爱。这是对于遗忘、结合、慰藉和绝望之爱的渴求,通常会同时包含以上两种之爱或更多。它们相互交融,通过隐喻进行模糊的暗示。而在其他时代,爱甚至不会被提及,尽管如此,爱还是会通过其他的隐喻加以呈现,尤其是通过另一个伟大的诗歌主题——酒。
可能,这一时期的波斯诗歌从失落的萨珊王朝宫廷诗歌——爱情诗歌与英雄诗歌——传统中继承了思想和模式,例如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就来自广为人知的波斯诸王的传统故事。但大部分的诗文形式都直接沿用了之前的爱情主题,源自之前的阿拉伯诗歌传统,并且反映了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在征服战争多年之后,在语言和文化材料方面的交流。而这些诗歌的片段在早先的时代就为人所知,最初, 大量的诗歌来自塔希德王朝时期的著名诗人。但第一个被称为伟大诗人的人——鲁达基,来自萨曼王朝的宫廷:
你的心从未有残酷之意,凝视我时,你的双目未曾有泪水柔情。
奇怪的是,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的灵魂,因为你对我的伤害超过敌人的千军万马。
鲁达基(在940年左右去世)和另一些诸如沙希德·巴尔希、达吉基·图西的诗人一样,都从萨曼王朝宫廷刻意的波斯化政策中受益。萨曼王朝为诗人提供赞助和庇护,并且总体上鼓励他们使用波斯语而不是阿拉伯语。

鲁基达
菲尔多西(约935—1020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出生在萨曼王朝统治时期,但后来当萨曼王朝的统治崩溃了以后,他处在源自突厥人的伽色尼王朝统治之下。他的《列王纪》(这一史诗由萨曼王朝的达吉基开始,他续写并将之完成),可以被视作合理地实践了萨曼王朝的文化政策——避免使用阿拉伯语,赞颂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诸王,超出了非伊斯兰的立场,明确支持马兹达教。
《列王纪》结尾处的一些语句,仿佛恰好在萨珊王朝军队于卡迪西亚战败和伊斯兰教来临之前说的,呼应了大流士在比索通的最早的马兹达教碑铭。这在11世纪的伊斯兰背景下令人震惊(第一句就提到“敏拜尔”——一个凸起的平台,类似教堂里的讲经台,在清真寺里就是从此处引导祈祷者的):
他们将讲经台置于与王座等高的位置,将他们的孩子取名奥马尔和奥斯曼。随后,我们辛苦的劳作将化为乌有。哦,漫长的衰落从此起始 ……
…… 此后,人们会打破自己同真理的联系,而歪曲和谎言会被人看重。
因此,当后来菲尔多西的巨作完成之时,伽色尼王朝的统治王公对此不甚热衷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的观点更为正统。关于这位诗人历经几个世纪流传下来的故事是不可靠的,但其中一些至少反映了真实事件的一些方面。
一个关于《列王纪》的故事说,伽色尼王朝的苏丹希望不同人物的篇幅都短一些,只给了菲尔多西很少的赏赐。诗人十分不快,将钱分发给了一个当地卖酒的商人和一个浴室侍者。苏丹最终阅读到了《列王纪》中一段尤其精彩的篇章,意识到了其伟大的影响,想要送给菲尔多西一份丰厚的礼物,但太晚了——当载着赐给菲尔多西财宝的牲畜从一座城门进入他所居住的城镇时,他的尸体已经从另一座门抬出去埋葬。
《列王纪》的伟大主题是英雄在马背上以长枪弓箭所建立的功绩;他们内心忠于良知还是君主的冲突;他们与活泼女性之间的风流韵事,这些女子亭亭如柏树,明艳如皓月;充满争斗与享乐的王家宫廷——“战歌宴舞”。从中不难读出一个来自小土地所有者的士绅阶层/德赫坎的思乡之情,他们是官僚和学者,并且为萨珊王朝的军队提供了引以为豪的骑兵。他们以笔为剑,目睹阿拉伯人和突厥人进行战争与政治的宏大游戏。
《列王纪》在波斯文化中有其重要意义,可与英国的莎士比亚或者路德翻译的德语版《圣经》相比,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已经成为教育和许多家庭的核心文献,其次才是《古兰经》和14世纪伟大的诗人哈菲兹。《列王纪》对修正和统一语言起到过作用,为道德和举止提供了模范,并且为伊朗人提供了身份认同感——回溯到了伊斯兰征服之前,否则这种认同感可能会随着萨珊王朝的终结一并消散。

《列王纪全集》,[伊朗]菲尔多西著,张鸿年 / 宋丕方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版
《列王纪》中的诗歌及其关于马背上的英雄、爱、忠诚与背叛的主题,与中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这种思想的碰撞首先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几十年就已经小有影响,将西方的欧洲和地中海东岸土地之间的联系提升了一个层次。也有一种理论认为,游吟诗人的传统,以及成果丰硕的中世纪欧洲宫廷爱情的比喻,至少有一部分源自阿拉伯统治时期西班牙的苏菲派。但也可能只是一种平行发展的情况。
苏菲派对波斯诗歌的影响
11世纪见证了独一无二的神秘主义运动高潮——苏菲派,奥马尔·海亚姆使用了苏菲派诗歌中常见的术语,并且作为关键概念加以使用,往往具有隐喻性质。例如,“mey-e moghaneh”意为魔力之酒——琐罗亚斯德教的禁酒;“rend”意为一个狂野的年轻人、流氓或者浪子;“Kharabat”是房子的废墟、 酒馆;“saqi”是侍酒的男童,同时也是同性情欲的对象。
尽管一些评论者声称奥马尔·海亚姆是一个苏菲主义者,毫无疑问他对苏菲主义抱有同情,但他更多的是为自己发声,这种声音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归入任何宗教范畴中。并且,他的怀疑主义太过强烈。
苏菲主义是一个庞杂的现象,从11世纪的小亚细亚、北非到现代的巴基斯坦及其之外的地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着非常不同的各个侧面。它的起源并不明确,但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保有神秘的元素——正如其所示,一些人可能会说,能追溯到麦加之外的旷野中,《古兰经》昭示于穆罕默德之时。苏菲主义的本质是寻求一种对个人精神境遇的确切追求,在神的面前放弃自我和一切世俗的自我 主义。

苏菲派的旋转舞
但无论是在现实还是想象中,苏菲派在伊斯兰征服后的几个世纪,也参与到了宗教动乱之中,反映了前伊斯兰时代广受欢迎的思想和影响,包括带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新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主义运动。这些影响伴随谨慎的无政府主义和唯信仰主义的倾向,使得苏菲派从一开始就与那些基于文本、学院派带有城市传统的乌理玛关系紧张,后者只是阅读和重释《古兰经》与《圣训》,宣称重新定义了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
紧张与冲突并存,并且一些苏菲派或者神秘主义的思想者被乌理玛谴责为异端,例如哈拉智和苏瑞瓦尔迪被处死(分别在922年和1191年)。苏菲派在11-12世纪的重新崛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斯兰实践和伊斯兰研究逐渐集中于学院,直接处在乌理玛的视野之下,这种情况在此段时期发生了。
这一时期,苏菲派在伊斯兰土地上的重要性有时被忽略了,但实际上它是无处不在的。在波斯,其文化影响从波斯语诗歌中显露出来,同时存在于所有存有苏菲派“扎维叶”的土地上。“扎维叶”是苏菲派云游修行者的住所,也为当地民众宗教集会所用。在更大的城镇,可能有为不同的苏菲派团体而建的“扎维叶”,还有集市行会和其他与苏菲派有联系的组织。
甚至,小村庄也可能有“扎维叶”。这与中世纪欧洲为男修士设立的托钵修会团体有相似之处。和修士一样,苏菲派密切卷入了普通民众的宗教生活,并且参与了波斯国境内外的传教活动。鉴于当时低下的读写水平、绝大多数民众居住在农村这样一些事实,苏菲派主要在城镇和城市之外进行扩展就显得顺理成章。他们活动的中心在波斯,尤其是呼罗珊,但他们可能是将波斯文化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传播到德里及其之外的地区,并巩固和产生广泛影响的主要中间人。
许多苏菲主义者,尤其是许多苏菲派诗人,公然蔑视乌理玛,认为其自视甚高。苏菲主义者对他们进行挑战和攻击,认为他们被教条所困,被虚荣的自尊所蒙蔽,忘记了真正所需的无我精神。这就不难见到为什么一些正统的穆斯林(尤其是瓦哈比派以及18世纪以来他们的同情者)将苏菲派革除教门,并加以迫害。
但在我们正讨论的这个时代,云游的苏菲主义者(亦被称为苦行僧)的传教活动是十分重要的,可能对于新皈依的穆斯林是最为关键的。在像塔巴里斯坦这样偏远的乡村地区,情况确实如此。在那里,正统的伊斯兰教渗透得十分缓慢。在像安纳托利亚这样新征服的土地,以及东北部偏远地带(突厥人的中亚故土),情况尤其如此。
苏菲主义的第一个大理论家是加扎利(1058—1111 年),他是呼罗珊图斯城的一位当地人士(尽管苏菲派的重要人物所属的时代要早很多,例如在约910年去世的朱奈德)。正统的逊尼派和苏菲派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而且加扎利最初属于正统逊尼派的沙斐仪学派,他曾写作品攻击穆尔泰齐赖和阿维森纳,并且引入了希腊哲学的观点。但他也写了一部有影响力的苏菲派作品——《幸福的炼金术》。总体而言,他试图消除正统派与苏菲派之间的障碍,使后者成为前者的一个合法派别。在苏菲派发展的最初几百年,较之逊尼派,什叶派对苏菲派修行者的敌意更甚。
萨纳伊是第一个明确忠于苏菲派的伟大诗人,一些人将他的文学风格与加扎利相提并论。萨纳伊的长诗《真理之园》(于1131年完成)是一首经典的苏菲派诗歌,但他在此之外还有大量诗作。在这些作品中,可以很容易察觉出传统的爱情诗与神秘主义悸动的融合:
自从我的心被爱情的罗网所俘获,我的灵魂成为爱情杯盏中的美酒,啊,我通过爱情体察到了痛苦。自从我像一只雄鹰,落入了爱情的罗网!
困于光阴之中,我成了一个酒徒,沉醉于令人心动、滤去渣滓的爱情杯盏。惧怕爱情带来的强烈苦恼,我不敢表达爱情之名; 而更惊奇的是,我看到大地上的一切生灵都与爱和谐共处。
这里,酒再次成了爱的隐喻,将这一意象带入了另一个复杂的维度。对此,正统的穆斯林可能倾向依据宗教法律而节欲,而萨纳伊所说超出了法律,进入了背弃信仰的境地——留下自己贪婪、淫荡的灵魂,苏菲主义者找到了另一条通往神的道路。
这一观点就是爱情与酒都会成为人忘却自我的途径。这些是自我感改变或泯灭了之后熟悉的体验。这样的体验可以使人感受到(也因此提供了一种隐喻)面对神时那种失去自我的神秘体验——失去自我是必要的真实宗教体验,对它的渴求如同恋爱中的人渴求被爱一样。
塞尔柱时期产生了大量诗人,我们不可能对他们一视同仁。但尼扎米·甘贾维在 1180 年和 1188 年分别创作了《霍斯劳与席琳》(Khosraw va Shirin)和《莱拉与玛吉努》(Layla va Majnoun),这两部作品十分重要,因而他值得我们关注。这两首长诗都在复述更久远时期的故事——前者是来自萨珊宫廷的故事,后者源出阿拉伯人。
他还写了其他许多作品。这两首长诗写的都是爱情故事,广受欢迎,但它们有更深层次的回响,反映了尼扎米的宗教信仰。莱拉与玛吉努坠入了爱河,但随后他们分离了,玛吉努就疯了(Majnoun 意为“疯狂的”),在旷野里游荡。他成了一名诗人,以第三人的身份向莱拉写信:
哦,我爱,在你如同茉莉的怀抱中!爱着你,我的生命凋谢了,我的嘴唇枯萎了,我的眼中饱含泪水。你无法想象我对你有多么“疯狂”,我失去了自我。但那条路只有那些忘记了自我的人去走。在爱情中,忠实必须用心中的热血来回报;否则他们的爱情就不值一颗黑麦粒。所以你指引着我,揭示对爱情真正的信仰,即便你的信仰会永久隐藏。
对他的爱情失去希望之后(莱拉的父亲不让他们成婚),玛吉努就将爱情精神化了。进入荒漠,在疯狂中失去了自我,越出了寻常的礼教,并且写作诗歌,他实际上成了一名苏菲主义者。所以,即使是这样一个公然亵渎神灵的故事,其精神维度也不是一眼就能望见的。但要具备精神力量,它所传递的隐喻和精神信息首先需要我们对恋人们的困境抱有同情之心。这首诗歌不仅是关于苏菲主义者是如何接近神的,还是一个爱情故事,其中包含人类的诉求。在伊斯兰世界中,这首诗歌几乎被翻译成了每一种语言;在伊斯兰世界之外,它也已被译成多种语言。
爱情的使徒阿塔尔,确立了“爱的宗教”
法里德丁·阿塔尔在约1158-1221年(或1158-1229年)生活在尼沙普尔,在其一生中写作了4.5万行诗。确立了“爱的宗教”的基本要素,阿塔尔对后来所有的苏菲派诗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发展了“卡兰达尔”(qalandar)的观念,即旷野之人、世外之人,唯一指引他们的是宗教伦理:
那些坚定朝向爱情迈步的人,将会超越伊斯兰和无信仰的境界。
阿塔尔的经典诗歌是《百鸟朝凤》,这是最为家喻户晓的波斯诗歌之一。它讲述了众鸟寻求神秘凤凰(即神鸟斯摩夫)的故事,引人入胜。它也是关于谢赫萨南的故事,以极其逻辑化的方式,揭示苏菲主义的全部含义。在伊斯兰的语境中这个故事颇为挑衅,令人震惊,对苏菲派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谢赫萨南是个博学且备受敬重的圣贤,他总是做正确的事情。他曾经前往麦加朝圣50次,斋戒祈祷,授教400名门徒。他对宗教法律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得到众人钦佩。但他经常陷入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梦中他居住在罗姆(这可能是意指安纳托利亚属于基督教的那一部分或者是君士坦丁堡,而非罗马本身),并且在那里的基督教堂内礼拜。这令人不安,他的结论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他必须前往基督徒的领地。他出发了,不久之后他遇到了一个基督徒女孩——“在美丽的庄园里,她如同太阳……”
她的双眼向那些身处爱情之中的人诉说着希望,柳眉在上,弯曲如月,风情万种, 柳眉一瞥,秋波暗送,填满她爱人的心房。
并且,正如时有发生的那样,这个老头坠入了爱河:
“我失去了信仰,”他哭喊道,“我献出的心现已无用;我成了这个基督徒的奴隶。”
谢赫萨南的同伴试图使他恢复理智,但他的回复更为震惊,更具有破坏力。他们让他祈祷,他同意了——但并不是像穆斯林那样朝向麦加的方向,他反而询问她的脸庞在何处,那将是他祈祷的方向。另一人问他是否后悔背弃伊斯兰教,他回答,只后悔之前自己愚昧,后悔自己之前不曾沉醉于爱情。另一人说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他说是的,还有自己的名望——随它们而来的还有欺诈和恐惧。另一人劝他在神面前忏悔自己的可耻行径,他回道:“是神自己点亮了这一火焰。”

法里德丁·阿塔尔墓
谢赫在他所爱之人门前的街道上居留了一个月,与狗和尘土为伴,最终病倒了。他向她乞求,希望得到一些怜悯、一丝爱,但她嘲弄他,说他已经年老——他应该找寻一件寿衣,而不是爱情。他再次乞求,她说他必须做四件事以赢得她的信任——焚烧《古兰经》、饮酒、封印住信仰之眼,还有向圣像顶礼膜拜。谢赫犹豫了一会儿,但随后就答应了。他受邀入内饮酒,还喝醉了:
他喝醉了,完全遗失了自己的灵魂。酒和他的爱融合在了一起——她的笑声似乎在挑动他去获取梦寐以求的极乐。
他同意了女孩要求的一切,但这还不够,她还要黄金和白银,而他很穷。最终,她对他有所怜悯,不再看重金银,但条件是他愿意 当一年猪倌照看猪群。他同意了。
从其极端的程度来看,稍后这个故事有了一个更合乎传统的转折,如果此书不想被禁和销毁,这样做也是有必要的。因而出现了如下场景:先知介入,谢赫回归了信仰,女孩后悔自己对待谢赫的行为,成了一名穆斯林,随后死去。但这并不能消除隐含在故事第一部分中的刺痛感,因为传统的符合习俗的虔敬不够充分,这可能会在实际中导向错误的道路,并且依然表示解除传统的束缚、在爱情中失去自我是通往更高精神境界的唯一途径。正如阿塔尔在开头介绍这个故事时所写的:
当亵渎和信仰都不再留存时, 躯体与自我都被杀死; 道路将会问求刚猛的勇气, 你的所有,及你自身是否能胜任我们的任务。 毫无畏惧地开始旅程;保持镇定; 忘记什么是伊斯兰,什么不是 ……
从整体上看,这个故事显得模糊不清,但它包含了对于当时的宗教习俗惊人的挑战。
爱情使徒阿塔尔死于13世纪20年代的某个时刻——在蒙古人入侵呼罗珊和波斯时,和尼沙普尔的大多数民众一起被屠杀了。蒙古人的入侵给伊朗的土地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劫难。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对那些土地相对比较熟悉,他们是有所克制的征服者,而蒙古人既是异域之人又格外残酷。
原作者 | [英] 迈克尔·阿克斯沃西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