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民生前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与欧洲学家。解读欧洲文明进程的轨迹,并把这种对异域文明的观察最终落到对本土文明的省察,是陈氏文明史书写的独特思想路径。

陈乐民(1930-2008),著名学者,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欧洲学会前会长。主要著作有《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的进程》《莱布尼茨读本》《徜徉集》《启蒙札记》《对话欧洲》等。
撰文丨夏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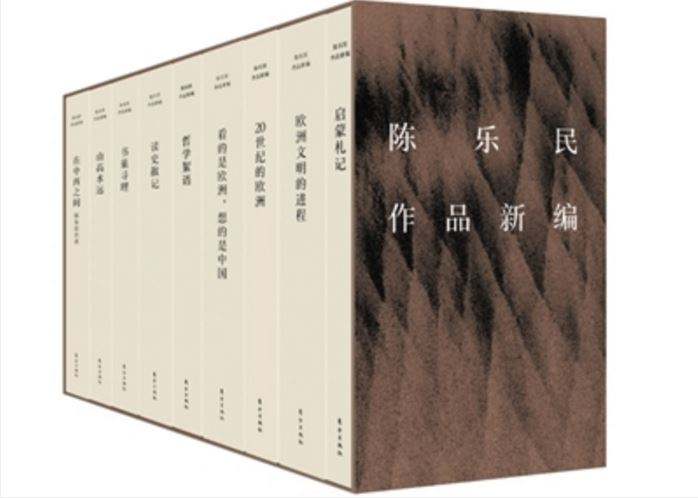
《20世纪的欧洲》等“陈乐民作品新编”九卷本,陈乐民 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10月。
在欧洲边缘化之时,欧洲还剩下什么?
“从另一个星球上带回一块石头”。
这是陈乐民先生对他的研究和著述工作的比喻。“欧洲文明”就是他试图从异域搬运回来的石头,运载的工程极为浩大,需要旷日持久的时日。自1955年被派往维也纳长驻工作之时,在欧洲国家的生活、旅行、访学之际就是寻找和勘察“欧洲文明”之始,到1980年代再度外访,足迹延伸至欧美,是他更深入体察中西文明之核心的时刻。现在他的运载工作完成,《启蒙札记》《欧洲文明的进程》《20世纪的欧洲》《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山高水远》《在中西之间》等九部书新编结集出版,它们排列在一起如城砖般结实。
当陈乐民先生的九卷本著作新编摆在眼前时,我想的是从哪里进入。无疑,这是视野恢弘的观照,作者的目光所及,从欧洲文明之源开始,梳理古希腊的精神和智慧,辨析罗马帝国的兴衰,透视基督教的传播和罗马帝国的瓦解。进入中世纪的历史云烟,检阅欧洲封建制及其历史意义,中世纪的商业文明与商业扩张,封建制的衰落与君主制的兴起;从欧洲观念,到思想解放,启蒙运动与理性之光,这些著作构成一个智识者的思想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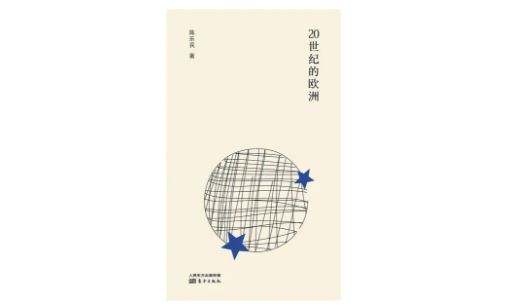
《20世纪的欧洲》,陈乐民 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10月。
当今之世,欧洲还有文明存在么?或者欧洲的文明还重要么?这样的问题或许会萦绕在时人心头。近年人们通过视听媒介频繁看到欧洲的坏消息:巴黎恐怖袭击、巴黎圣母院的冲天大火以及燃烧过的灰烬、伦敦的爆炸、西班牙马德里3·11恐怖袭击、弥漫全球的瘟疫至今不见消退,在疫灾中死亡的人数百万之巨。西方世界被恐怖的阴影笼罩,不同宗教之间的征战,民粹主义狂袭,经济衰退,被人们笃信的欧洲大陆陷于困境,欧洲文明沉暗。频繁的枪击事件、因种族歧视而导致的大规模抗议使美国陷于持续的骚乱,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信仰崩溃时期。秩序错乱的年代,文明的光芒还存在么?世界秩序是否会被新崛起的威权重新塑造?这些问题都使当今世界面临严峻的考验。
然而世界的动荡再次为我们认识人类命运提供了参照背景。透过全球的变幻风云深入察看普世文明的精神与核心。人类不会重回蒙昧时代,也因此“我们从哪里来,此刻何在,以及往哪里去”,这样的哲学命题不会过时。在欧洲边缘化之时,也要有识者告诉我们“欧洲还剩下什么?”有益的阅读是扩展我们认知经验的有效方式,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增强人的生活定力,我愿意将这九卷的《陈乐民作品新编》收藏阅读。
聚焦欧洲文明史的著作置于案头,是我们认识欧洲文明的思想工具,也是对比中西文明的镜像。“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欧洲。欧洲的历史代表的是一个古老而又有创新的、十分成熟的文明。廓清欧洲社会史怎样进入近代的,欧洲是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起经过漫长的嬗变过来的。”陈乐民在《我们眼中的欧洲文明》里阐释思想和写作的缘起时写道:“欧洲无与伦比的、独特的宝藏是它的历史文化,是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传至今日,永世不衰的哲学、文学、美学、历史学、法学等等,以及由此散发的或精致、或壮美的文化品位。”

1990年,陈乐民在戴高乐家乡。
关于欧洲文明史的书写繁多,因此写作者的观念、智识和学术品格更为重要。
以自己的眼睛看明白欧洲文明进程的那条轨迹,一切都必须经过自己的大脑,这是陈乐民的治学原则。他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岁月时自言:“最可慰藉的是,因为终于懂得了用自己的头脑去思想。”用自己的头脑思想构成陈氏文明史书写的独特思想气质。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对异域文明思考最终落到本土文明省察,这是其思想路径。
“我要写的是自己悟出来的看法,我要自己从古到今走上一趟,亲自品味这沿途的风景,得出我自己的印象。”陈乐民自述个人的治学之道:“别人写的书,他们的见解,对于我是必不可少的参考和滋养,无论是外国人写的,还是中国人写的,我必须读。但必须经过自己的咀嚼和消化,成为我的,以助于形成我自己的思想和认识。”
康德思想指引研究方向
在浩渺的书海里,人与书的相遇需要缘分,也需要介质。
阅读《启蒙札记》的结果,是我从卧室外的客厅书架的高处找出曼弗雷德·库恩所著的《康德传》仔细阅读。我是被陈乐民的启蒙所引导,循着指引进入一位启蒙时代的哲学巨匠的生命故事与历史云烟,见识康德的思想生活如何扎根并回应他的时代,西方世界发生最重要变化的十八世纪,一位捍卫启蒙的文明世界的伟大思想家。
对康德的阅读是我找到的陈氏文明史书写的思想路标。他在“科尼斯堡的圣人”一节,表达了对康德的敬意:“康德有一颗伟大的良心,他的墓碑上刻着《实践理性批判》结论的第一句话:有两件事,令人敬且畏之,久而弥新:在上是宇宙星空,在心底是道德法则。”
早年陈乐民看到康德的一本书《永久和平论:一个哲学方案》。这部书写作于1795年,这本书表现了康德“老年时代的精力和清新的头脑。”1980年代,陈乐民正在研究欧洲历史,那时没有中译本,他看的是1917年伦敦印的英译本。发现这本小册子大喜过望,他会反复读。在1980年代,康德占据了陈乐民的思想核心,经由康德的思想指引,他将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的社会作为学术研究方向。对康德的阅读影响了陈乐民的治学之路,使他拓展研究国际问题的幅度,迈进更广阔的人类文明史的研究。
“启蒙的前提是充分运用理性的自由,要开启民智就必须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这是陈乐民在《启蒙札记》里对康德的论述。二十四篇文章以“何谓启蒙”为题,讲述十八世纪以前的历史,以英国为例讲述启蒙的进程,英国启蒙在近代的意义;以启蒙思想家为题,讲述一代哲人与启蒙的关系,以启蒙与中国为题,讲述启蒙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以西方文明杂谈为题,讲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英法文明的区别。这些文章是陈乐民临终前的著述,是启蒙的普及读本,然而也是他没有来得及实施的新工程的思想准备。
在陈乐民的中西文明书系里,启蒙一词是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启蒙,就是开启民智。民智不开,什么都不好办。民智一开,蒙在公众头上的阴云驱散,柏拉图笔下的洞穴人见到了太阳光芒,康德所说的人从自己的不成熟或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光的力量,启蒙的力量是何等奇伟。设想,一个相当大的比例的公众处于愚昧或半愚昧的社会,怎能称得上是一个文明的、公正的、现代化的社会。”

《启蒙札记》,陈乐民 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10月。
康德说:“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唤作启蒙。”启蒙作为一个历史社会意义(包括人类精神)的名词,始自康德。在十八世纪晚期,有人问康德,德国是不是已经启蒙了?康德说:“还不能说已经启蒙了,但无疑是处在启蒙时代中。”陈乐民的《启蒙札记》是对启蒙的普适性阐释,他为读者提供启蒙的真义,梳理它的历史渊源和文明史的意义。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在“何谓启蒙”的诘问下,陈乐民展开的是他对启蒙思想家与所在时代的变革的勘察和解析,同时也是对中国文明史的比较观察和思考。他写道:“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源泉。古希腊学派林立,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即追求光明、崇尚知识、摆脱黑暗。在古希腊以后,欧洲曾经有过大约500年的黑暗时期。”
《启蒙札记》里讲述了在欧洲文明史上灿若星辰,驱散欧洲中世纪黑暗的哲学家,如康德、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大卫·休谟、弗朗西斯·培根,他们带给民众思想的觉醒,引领并开启他们的心智,成为启蒙时代的理性之光。陈乐民在《敬畏思想家》写出思想者在文明史的意义:“恺撒、亚历山大、铁木真、克伦威尔等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而诲人的话,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斗室中的世界主义者
生命的最后时刻,陈乐民自称是斗室中的“世界主义者”。然而在这时他已经坐了轮椅,几乎站不起来。
阅读陈乐民“文明史”书系,我惊讶的是,在作者身患重症之时依然执笔不辍。
1991年陈乐民病倒。医生确诊为弥漫性肾衰竭中期。需要治疗和休息。然而次年10月,他还是出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中法讨论会和去日内瓦大学做演讲。征得医生同意前去赴会,到巴黎就病倒。发现大量血尿,长时间止不住。中途折返巴黎。从巴黎回国到协和医院检查,已致慢性肾衰竭的中晚期,再进一步就是尿毒症。
1997年底病情急剧恶化,协和医院的医生开了住院单,做血液透析。在等床位的两个月里,陈乐民为《欧洲文明扩张史》举办书稿论证会,提出“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的命题。他想要做的是“把西欧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启蒙时代讲清讲透,作为我们的一面镜子。”
陈乐民多半生工作听从组织安排,研究也遵守组织指令。“昨夜星辰昨夜风”,陈乐民用如此诗意化的句子形容自己过往岁月。过去的都过去,幸好有些值得一记的东西,还可在记忆中寻觅到。

1991年,陈乐民在美国威尔逊中心。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意识形态。肉身的遭际和境遇也是检测文明的标尺。
《在中西之间:陈乐民自述》里追忆了在时代变迁中的个人历史。
陈乐民出生于北京城南一条叫銮庆胡同的小胡同,当时的门牌号数是三十四号。这是一个大家族,家境殷实,子嗣满堂。然而很快随着日本占领北京沦陷,家道中落。
在国破山河碎的年代,人们必经的是战乱和离散,必经的是困苦和动荡。然而学业并没有中断,1950年陈乐民就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在世外桃源的清华园接受教育,也见识一代学者的风范: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梁思成、林徽因、钱钟书和杨绛。大学毕业之后,陈乐民被组织分配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这使他得以接触中外交流工作。1955年陈乐民被派往维也纳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陈乐民在回顾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时说:“彼时青年人凡追求进步……我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我常说要立志做党的不松动的螺丝钉。”
这是最早的对外交流经历。在维也纳之后,乌兰巴托、布拉格、莫斯科、东柏林、西柏林、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等成为他最早游历过的城市,彼时国际间“冷战”气息正浓。
从1955年到1959年,陈乐民长驻维也纳工作,这座他生活了四年的欧洲城市是他认识的第一座欧洲城市,也被他视为第二故乡。“在这里,我见过缓缓流淌的多瑙河,享受过诗意的维也纳森林的静谧,金色大厅的辉煌、歌剧院的华丽、仙境般的美丽之泉、琉璃绿顶的查理教堂……印象最深的州立公园中的施特劳斯雕像,风流潇洒;勃拉姆斯的半身塑像,凝重沉思。”然而也是在长驻维也纳期间,陈乐民亲历国际风云激荡,亲见国际共运史变幻。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消息最早是《纽约时报》刊登,当时中国派到西方国家的人员很少,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陈乐民和他的工作同伴看到相关报道,迅速将消息传回国内。
1959年,从维也纳回国的陈乐民接到组织安排到农村锻炼。随着政治局势之变,陈乐民在五十岁时离开位于台基厂大院的“对外友协”。
上世纪80年代后,国门打开,对外活动有所开展。申请进入外交部所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随两个不同性质的代表团出访,像是一场长梦初醒走进一个久违的世界。
陈乐民追忆当时的情态:“每每有一种时不再来的紧迫感,觉得五十岁以前的二三十年浪费了相当多的光阴,老老实实做了许多无益之事,二三十年几乎没有自我,对于学术研究,首要的原则,必须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排除一切非学术性的干扰。”
在七十岁的时候,陈乐民庆幸自己不再浑浑噩噩,而是有了“自我”。
“在迈向现代化的大时代里,我的祖国、人民背负着何等沉重而复杂的负担,许多问题甚至是世纪性的。一个巨人在沉睡中睁开眼睛,发现已被时代甩得那么远;巨人由于沉睡得太久,只是认清世界和自己,也需要足够的清醒和勇气。”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在中国有一些老人,他们从旧时代走来,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解放天性,活跃在公共空间。他们正直、勇敢而睿智,坚持独立思想,坚持良知。这些老人活跃在人文艺术领域,在他们身上蕴藏着文化基因,文明基因,他们成为国家真正的智识财富。
陈乐民是众多的老人之一。他自称是“斗室里的世界主义者”,在阐述“启蒙何以成为自己的终极关怀”时他说:“我个人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大浪淘沙,我什么也不是,何苦费这个劲?然而人来到这个世界,又念了一些书,懂得了些知识和道理,起码应该有良知,有一种对人世和社会的天然责任感,即使是一粒沙子,也该是一粒有灵性的沙子。”
“我个人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大浪淘沙,我什么也不是,何苦费这个劲?然而人来到这个世界,又念了一些书,懂得了些知识和道理,起码应该有良知,有一种对人世和社会的天然责任感,即使是一粒沙子,也该是一粒有灵性的沙子。”
——陈乐民
历史的书写是留给时间的文献。文明不灭,文献长存。
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文化,赖知识分子以传,知识分子的状况更为重要。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陈乐民写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像西方那样沿着学识的道路心无旁骛、不求仕进的知识分子不多。西方知识分子也要屈服于非知识领域的东西,例如神和君主。这个传统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比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墨法,对统治者的从属性要少得多。中国就出不了苏格拉底。伏尔泰把对神的态度划给信仰,而把求真理划归人的认识。给信仰和理性分了工。”
“不见人间宠辱惊”是陈乐民读《顾准文集》的感言,此说也适合他。为了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知识分子必得有此求真知而忘荣辱的胸怀,才能超脱于时代的重压而时发独立而超前之想,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他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埋首中外史籍,抱病写出《希腊城邦制度》这样的力作,读至痛切处扼腕而叹道:“在我国这种屈大夫、太史公类的知识分子,自不止顾准一人,许多人或因所治非关热点问题而为时潮所淹,或者因无人发现遂尔湮没不闻。”
陈乐民的座右铭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他的读书、思考、写作与功名利禄无关,与谏言、智库无涉,因此耐得住寂寞。媒介泛娱乐化,乃至娱乐至死推动的大众狂欢潮流构成另一极社会景观。时下出版界的实况是出版生意化,出版人追逐明星和名流,追逐网络红人。严肃的书籍在出版后大多湮没于喧嚣的商业炒作中。我猜想这套九卷集的“陈乐民作品新编”或许也会被印刷品湮没,难被世人识别。这是文化的命运,也是文明的境遇。所幸在这社会大潮之下,存有潜流。尊崇思想力、尊崇优质的智识,尊崇独立意识,这使得一些具有思想力的书籍可以行世。对文明的珍存是对人类智识之火种的守护和收藏。
行文至此,我想起史学家司马光的轶事。据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殚思竭虑,改了又改,斟酌又斟酌。他的夫人说:“你这样反复地改,也没有人看到,你何必为难自己?”
司马光说:“千秋万代的人都会看到,我怎么能不认真写作。”
在此向致力于中西文明史书写的陈乐民先生致敬。
作者 | 夏榆
编辑 | 李永博 罗东
校对 |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