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文学评论的写作者,张定浩不满足于当下流行的评论方式——将文学与具体现实问题紧紧捆绑在一起,他想找一个机会,在谈论文学的同时,探索在文学深处看似抽象无形却更为恒久坚实的领域。于是,便有了《无形之物》一书。
在《无形之物》一书的开头,张定浩引用了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一句诗:“我不过是无形之物的一名秘书。”那么,“无形之物”到底指什么?在张定浩看来,“无形之物”有如梅洛·庞蒂的“不可见之物”(《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包括意义、观念、原理、体验等,而这些无形之物构成了可见之物的深处,并支撑着各种可见之物。

张定浩,1976年生于安徽,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笔名waits,写诗和文章,现居上海。
一场关于无形之物的书写,旨在探讨构成文学的内部元素。这本书的基础,是张定浩在2017年为《小说评论》所写的六篇专栏稿——“重力”、“离心”、“笑声”、“尽头”、“重复”和“名物”。此外,还有六个章节,例如“算法”落脚于特德·姜的小说,“能力”是他对詹姆斯·伍德的致敬。而“上海”则写于2012年,带着张定浩年轻时的印记,这篇文章被他放在了最后,“是想表明一个城市和回忆也是无形之物”。
我们还和他聊了聊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些现象与问题,作为一个处在当代文学发生现场的人,他会如何看待长久以来的地域性写作,以及对于“东北文艺复兴”和“小镇青年故事”有怎样的观察。而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对他而言,文学批评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样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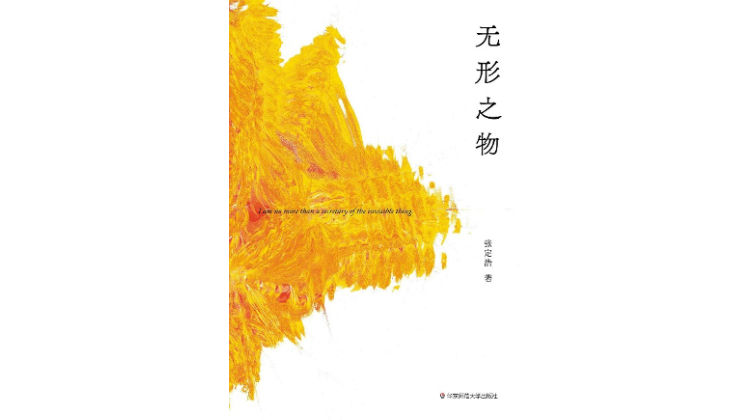
《无形之物》,作者:张定浩,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1.过于强调地域对人的影响,会生产出概念意义上的人
新京报:在《重力》一章中,你探讨了中国文学史长久以来的地域性写作传统,而你认为梁鸿的《神圣家族》超越了这一意义。那么你认为,在写作中,小说人物与地域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张定浩:人当然总是身处于某个地域,受这个地域的影响,但他同时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和地域的关系,有点像一个多变量函数和其中某个变量的关系。地域影响可以很轻松地解释为什么上海人不同于河南人,但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个上海人不同于那个上海人(或许是因为这两个上海人的父母出生地域不同?)在小说中过于强调地域对人的影响,和过于强调其他任何一种概念性的身份认知一样(比如强调一个人是诗人、或是商人、农民),会生产出一种平均意义上的、概率意义上的人,而这种平均和概率意义上的人,恰恰是生活和小说都要抵制的。再进一步讲,地域本身就不是一个僵化固定的概念,地域在影响人,人也在不断影响和改变他所身处的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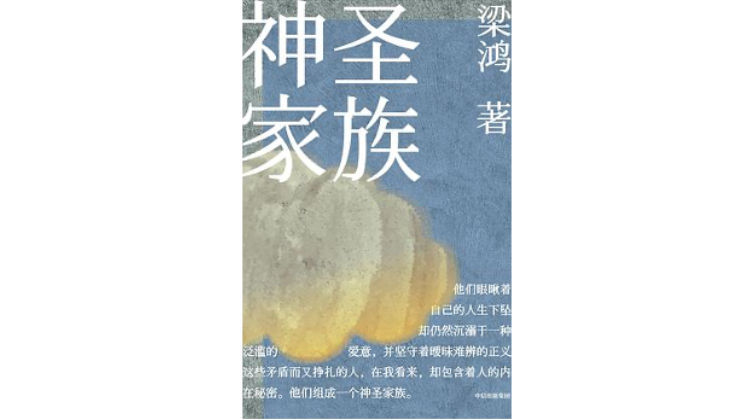
《神圣家族》梁鸿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出版
新京报:近年来出现的“东北文艺复兴”和“小镇青年故事”,你怎么看这样的地域书写,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作家和老一辈作家的地域书写有什么异同?
张定浩:我觉得从作家的角度来讲,写他们所生长的地域,写自己的青年时代,这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至于为什么“东北”和“小镇”作为两个关键词,在最近几年被凸显出来,我觉得是要到文学之外去寻找原因,而不是在所谓文学传统内部追根溯源。至于异同,就你提到的这两种典型来讲,我觉得和之前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要说现在年轻作家在地域书写方面有什么真正新鲜独特的东西,我倒是觉得王占黑值得注意,她笔下的老社区空间就不再是那种供人感伤、赏玩或做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封闭橱窗,她的小说特别注意不去固化某个地名,因为她知道空间都是属人的,人在哪里,那个空间就在哪里,每个人都携带着自己的空间,不断地和他人的空间交融在一起。

王占黑
新京报:有人认为“东北文艺复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当下流行的被划分到“东北文艺复兴”的小说,大多是在讲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故事,而东北在整个二十世纪丰富的民族性(闯关东、伪满洲国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兴起、共和国长子)似乎被遮蔽了,你怎么看呢?
张定浩:如果说这是一个伪命题,那它的伪,并不在于其题材所涉及的历史时间段的宽窄,而在于,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所谓“文艺复兴”。是文艺人才突然的丰富涌现和丰富中蕴藏的差异性?是对古典文明理解的深度和在这种深度理解中引发的新开端?还是说,就是因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些被文学史称为“东北作家群”的文学青年,然后现在又忽然出现几个写作风格、题材相互有些接近的沈阳铁西区青年作家? 进而,我们又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东北”?东三省是完全一体化的吗?在文学界很多类似的命题都只是源自一种外部的粗糙的观察,类似于广告语,听听就行,经不起也不值得仔细推敲。
新京报:有一些文学上的偏见认为,凡是涉及东北的小说似乎都带有某种严肃性,而一旦写上海就被人认为小资、“布尔乔亚”,你觉得这样一种偏见从何而来?是因为上海更难去书写吗?另一方面,你期待着如何书写上海?
张定浩:这种偏见,我想是来自一种粗糙的、投机主义的新左思维。这种思维看起来在追求平等和正义,其实是追求个人的独断专行。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说,“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可以说也是在讽刺这种思维。假如我们投身到一个地域内部,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地域是容易书写的,就像假如我们真的了解人,就会发现没有一个人仅仅只是他表面呈现的样子。现代小说就是通过致力书写出这种复杂性,来对抗意识形态的粗暴简单。如果说期待,我可能会期待有人不是刻意要写上海而最终写出一个看不见的上海,就像布尔加科夫也没有特意写莫斯科,但某个时代的莫斯科就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之中。
新京报:《无形之物》很大程度上是在探讨小说的书写,而有学者观察到当下的写作很难去把握中国复杂的现实,怎么看待这样一种文学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错位?或者用西川的话说:“当代中国制造了那么多奇观,而你的语言如何与当下对称?”
张定浩:现实从来就没有简单过。我们看近处一个小阴沟会觉得纤毫毕现、漆黑瘆人,而远山在我们眼里可能只是一抹淡影,这里面的错位不是阴沟和远山的混乱,是我们自身的混乱。
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录、追随或所谓的对称关系。我们使用的每一个汉字,其生命都比我们长久,也比我们所生存的那个所谓现实长久。因此,每一次对于语言端正美好的(而非逐臭式的)使用,就是在暗暗地改变我们所生活的大气层。假如在某个阶段,生活确实是糟糕的,人已经习惯于奇观,那么就要让这糟糕的生活和在奇观世界中长大的人去重新学习效仿那个生机勃勃的文学世界,而非相反。
2.“例外”是把个人扔回具体生活中去
新京报:在“事件”一章中,你也指出“短篇小说是生成一个事件”,这种“事件”是否就像阿兰·巴迪欧对“事件”概念的重提,或者是后期拉康不再讨论象征界、想象界,而更多去讨论实在界,他们重新试图创造一个现代文明、现代权力、现代统治所不能完全镇压的覆盖的区域,在那里寻找希望和可能?
张定浩:我说的“事件”,确实来自于当代欧陆哲学中的“事件”概念。事件,不同于情节,故事,它是一次性的,并且和某个具体的引发我们关心的人有关。在小说中强调事件的生成,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警惕各种套路式的写作。此外,“事件”,乃至文学中所谓的创造,我觉得也非常类似于普里戈金和后来约翰·霍兰所说的“涌现”,这种“涌现”帮助科学家去理解和认识生命体的发生,同样,假如短篇小说也是一个小小的生命体,那么它只有在这样的“涌现”中才能成其为真生命。
我对拉康不怎么熟悉,但我觉得小说确实并非仅仅是象征界和想象界的事,它本来就关乎实在界,或者说,小说就充当着拉康三界之间的那些个扭结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拉康之前就一直存在于小说当中。

阿兰·巴迪欧
新京报:你在“能力”一章中借伍德的话说——“小说是演绎例外的大师:它永远要摆脱那些扔在它周围的规则”,而对这种例外的追寻,就像拉康后期对实在界的探讨,是否代表了某种追寻:一些不可能的东西对个人而言成为了唯一可能的东西,或者说实在界,这个拒绝被编码的,这个巨大的沉重的在我们认知之外的东西,也可能蕴含着很多动能?
张定浩:规则,如果用拉康的术语来讲,是属于象征界,那么例外,可以说就是多多少少碰触到了实在界。对例外的追寻,我觉得它不是一种刻意的、为了获得某种常人认知之外的东西而展开的追寻。例外,就是具体,是把一个案例中的当事人扔回到他具体的生活中去,这个人从此就不再只是一个案例,他在这个案例之外依旧有丰富自由的生命呈现。
新京报:在你看来,“无形之物”究竟指代着什么?可以和阿兰·巴迪欧的《追寻消失的真实》相呼应吗?还是有别的更多的意涵?
张定浩:梅洛·庞蒂临终前有一部书稿,叫做《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我说的“无形之物”,可能就接近于他说的“不可见的”,包括意义、观念、原理、体验等,而这些不可见的和可见的之间,并不是一个对立关系,相反,正如庞蒂所言,这些不可见之物构成了可见之物的深处,并支撑着各种可见之物。如果再打一个简单的比喻,这种“无形之物”就相当于“元素”,元素构成物质,但我们看不见元素本身,只能看见由各种元素构成的物。我可能是想在这本书中探讨一下文学中某些我感兴趣的元素。

梅洛·庞蒂
巴迪欧说的“真实”,或者说“实在”,当然也是这众多不可见之物中的一种。但在巴迪欧那里,始终还有一种激进左派的观念,要强调打破一切、推倒重来,要宣告各种不可能。拿一个花瓶为例,在他的理论中,这个花瓶的“真实/实在”是在于它内部的空,而要获得那个空,就必须打破这个花瓶。可能对我而言,并不需要如此激烈,我甚至觉得这种激烈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想象力的缺乏,或者说是对于想象力的轻视。当然他最后提出一种与二十世纪种种否定辩证法相对立的“肯定辩证法”,引用帕索里尼的诗句,“在真实中把握真实”,我倒是蛮认同的。
3.从事文学批评的写作者应意识到自身的责任
新京报:《无形之物》在探讨小说、文学,同时也在探讨文学批评,你认为文学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么看“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这句话?
张定浩:詹姆斯·伍德有一个说法,他说文学批评是在谈论文学,但同时也是在穿过文学去写作(writing through),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关于文学的写作(writing about)。文学批评与其他领域的理论批评(比如音乐批评或绘画批评)不同之处在于,文学批评与它所描述的对象共享同一种媒介,那就是文字。对文学之外的诸多领域而言,文字只是工具,不是对象,但对于文学而言,文字既是工具也是对象,既是因也是果,既通向一切自然和精神的实在领域,又收束在文本的虚构空间中。文学批评的这种被伍德称之为“独一无二的伟大特权”,也恰恰构成一种不可能性,敦促每一个文学批评写作者找到文学自己的语言去和文学对话。

詹姆斯·伍德
新京报: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客观性”重要吗?还是说,“客观性”只是一个伪命题,很多时候不过是文学圈子相互吹捧的遮羞布?
张定浩:我不太想用“客观性”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默认了某种主客观对立的二元论思想,默认了一个独立于主体存在的世界和一个隔绝在世界之外的主体。我可能更倾向用的词,是“准确”,是“如其所是”。我们很多时候夸奖一个文学批评比较客观,也就是想说它是准确和如其所是的,想说它虽然出自批评者个人,却反映出某种普遍性的意见。
新京报:“话语权”对于文学批评又意味着什么呢?
张定浩:要区分是话语的权力,还是权力的话语。后者和文学批评没什么关系,和政治关系更大;前者则提请每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写作者意识到言语自身的力量,以及为自己所说话语承担责任的决心。
新京报:对于文学批评,直观的体验,或者如梅洛·庞蒂所言“知觉的世界”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此间,理论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直觉的体验与理论的运用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张定浩:直观体验到的东西,也分为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比如我们不用把花瓶打碎就能体验到花瓶中间的不可见的空,又比如我们能体验另一个人隐藏的悲伤,体验时间的流逝。进而,这些体验到的可见与不可见之物,又可以分为能够表述的和难以表述的。在梅洛·庞蒂的“知觉世界”里,知觉,又不单单是一个直观体验,而是将人的体验放到世界中去,让世界在和我们的接触中呈现为世界。这个知觉到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物的总体,也是一个文化世界。所有我上面说到的这些不可见之物、难以表述之物、文化世界,都需要理论来帮助我们去更好地体验,简单来说,你知道的越多,你获得的体验就越深刻。
进而,所有的理论,一定首先要具体到是谁的理论,由此我们就会意识到,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他者在表达他的观念,这也是庞蒂所说的,帮助我们“从外部看人”。因此,理论也正是一个帮助我体会到他人的体验的过程。
新京报: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你觉得在当下这个时代——大家都可以对一本书评论的时代,一种认真的、细微的、具有见地的文学批评还有些什么意义?
张定浩:大家都可以评论一本书,并不意味着大家都会乐意选择接受一种最低劣的评论,平等并不就一定意味着反智。一个人愿意在公共媒体平台上评论一本书,他其实也是在渴望一种有意义的交流,而不会只满足于一种自我宣泄。好的文学批评,就是在促成这样的交流。
作者|吴俊燊
编辑|张进
校对|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