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黎璇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
亚当·斯密在1723年生于苏格兰,于1790年去世,他的生平绝大多数时间对应中国的清朝雍正、乾隆年代。在中国值闭关锁国之际,欧洲大陆在经历了工业化之后,迎来倡导回归理性的启蒙运动。亚当·斯密作为其中重要的思想家,撰写了《国富论》。直至今天,在一个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代,亚当·斯密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朱嘉明教授认为,亚当·斯密处在一个焦虑时代。1789年,也就是亚当·斯密死的前一年,法国发生了大革命。在此之前,大西洋彼岸发生了美国独立战争。革命和战争都是社会焦虑的极端反应。在这样的状态下,才会有在18世纪下半叶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本质是提倡理性,就是研究人应当如何摆脱精神桎梏,用理性解决焦虑时代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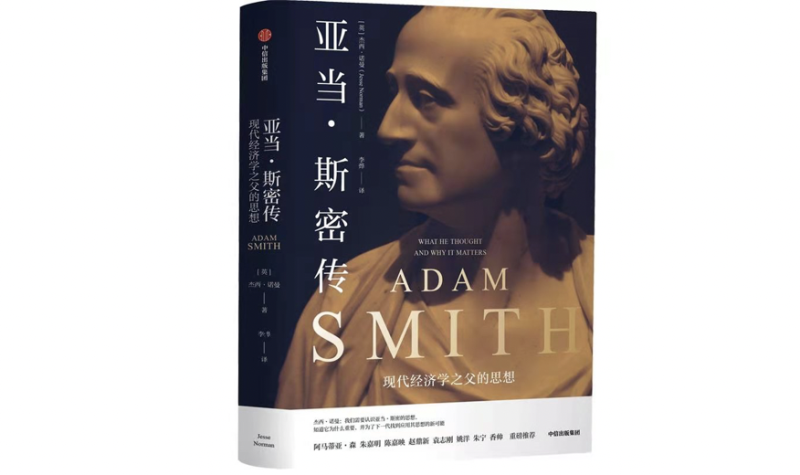
《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杰西·诺曼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2月
因此,亚当·斯密实际上是以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的身份,撰写《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他的经济学思想和对伦理道德的思想,都未摆脱他作为理性主义者的立场。《国富论》中认为市场是非理性的,“看不见的手”是非理性的,但利用市场经济的思想是理性的。尽管《国富论》因市场经济思想为人熟知,但这本书实际上是以国家和民族作为基本单位探讨财富的特征和起源。
何怀宏教授则补充,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法国的启蒙运动是有差异的。18世纪初的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当时激烈的战争与社会动荡很少,经济贸易发展得很好,知识分子的交流很密切。在平静安宁的社会里,诞生了亚当·斯密、休谟、哈奇森、弗格森这样的学者。他们通过出版著作获得了财富,处在一个充满希望而单纯的时代里。
《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
“看不见的手”有赖于“援助之手”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家为人熟知,但少有人知道他的思想成果横跨了经济、哲学、法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国富论》作为经济学著作倡导私利与自由,《道德情操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布朗在雨果·扬的纪念演讲中宣称:“我和亚当·斯密一样来自柯科迪,我已经认识到他的《国富论》是以他的《道德情操论》为基础的,他的‘看不见的手’有赖于援助之手的存在。”
何怀宏教授认为,尽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一个倡导利己一个倡导利他,但二者的思想并不冲突。比如“看不见的手”这一思想,《国富论》从生产的角度讨论手艺人以谋生为目的为客户生产商品。《道德情操论》则从消费的角度讨论消费者的奢华生活也为生产者带来了利益。而《国富论》也不仅仅倡导“自由放任”,它本质上提倡通过分工和交换来创造物质财富,实现整个社会的共赢。

朱嘉明。
朱嘉明教授表示他与何怀宏教授有分歧,他认为二者的思想不仅不冲突,而且还有交叉的空间。他讲述了亚当·斯密如何在《道德情操论》中讨论经济问题,在《国富论》里面怎样讨论道德情操的问题。
《道德情操论》的出发点是批判曼德维尔所写的《蜜蜂的寓言》,曼德维尔在该书中讨论一种恶德是否可以被视为公益。书中描绘了一个全员恶人的蜜蜂王国,王国里所有人都贪婪、自私、卑鄙无耻,每个人都在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利益,蜜蜂王国繁荣昌盛。直至有一天国王认为要反对恶德,提倡节俭和道德,要求所有人压抑贪婪。而结果是蜜蜂王国的崩溃,它从繁荣走向萧条,再走向衰落。这个寓言在英国激起了一个问题的讨论,即恶德是否能带来公益的结果。
朱嘉明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否定的。他认为公益如果要基于贪婪、无耻、自私来实现客观上的繁荣,这样的成本不是大多数人能承受,因为大多数人都要遵循恶德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因此社会道德应当有标准。而亚当·斯密对所有问题的讨论都基于他对恶德的否定,他不承认恶德的相互作用会导致一个正义和公益的后果。
基于此,他对市场和政府的看法也基于理性。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体系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因此经济需要被一个更大的社会形态控制,而形态的底色就是道德。当人执行经济行为的时候,不能超越良知的底线,利益不是在损人的基础上实现的。恶德在经济行为中必须被扼制,所以市场不应该是放任的。这样的理性也体现在《国富论》最后一部分中。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大篇幅地讲述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对贫民的教育将使整个社会受益,并倡导国家、公益社会与公共产品——这些在今天看来与“放任自由”对立的存在。
亚当·斯密老年写了《论嫌贫爱富、贵尊贱卑的倾向所导致的道德情操之腐败》——探讨如何应对贫富差距,穷人如何改变自身境遇。因此朱嘉明教授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是被后人庸俗化和绝对地放大了的。真实的亚当·斯密视野更辽阔、更多关注理性与道德。

活动现场。
回归理性精神,
有助于缓解普遍焦虑情绪
朱嘉明教授认为,亚当·斯密时代的焦虑,是关乎生存的焦虑。工业革命进行时,重商主义时代里发生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伦敦遍地都是垃圾和污水,泰晤士河肮脏不堪,城市被雾霾充斥着——那并不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田园时代。道德沦丧、礼崩乐坏,所有大资产阶级正在形成过程中,资本正在影响整个英国的走向。因此亚当·斯密首先撰写《道德情操论》,呼吁人们重视同情心。接着他试图用道德解释经济问题,于是他撰写了《国富论》,讨论如何建立道德的基础和秩序,而非放任自由。
而当下正处于一个后工业向数字经济和信息化转型的时代,人们的焦虑与食不果腹无关。朱嘉明教授认为这个时代有三个特征,一是不确定性;二是资讯爆炸,所有人都被信息包围、垄断和控制;三是焦虑本身和克服焦虑具有蔓延性,会通过人际交往传播。
朱嘉明教授认为,这样一个时代不能依靠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应当呼唤理性的回归。而理性就是诉诸新秩序,是相信通过回归人性解决当下的问题,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互相信任。除了理性以外,要提倡科学的方式,以及倡导人文主义关怀。
而对于眼下的性别不平等和“996”工作制,亚当·斯密在数百年前也曾有过解答,是对那个时代的启蒙和回答。对性别问题,他说:“为什么女性因为不忠受到的惩罚比男性更严厉呢?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在这方面制定法律的是男性,因此他们一般会倾向于尽可能遏制女性,而更多倾向自己。”对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尽管我们通常听到的都是工人团结在一起,而不是雇主的联合。但是谁若真的相信雇主之间不会联合的话,他对劳工问题,对这个世界就太无知了。”
而何怀宏教授认为,仅仅依靠已有的启蒙思想成果,解决不了当下的问题。一是物欲和体欲的问题,是人们不断碰撞的欲望。而市场经济,相对于管制经济或者计划经济来说,是最能实现这种致富愿望的手段。启蒙学者认为当物质欲望得到满足,社会会自然而然地向更高级别的社会过渡。但实际上欲望随着资本积累越发膨胀,当人的欲望不断增长,人永远都会感受到物质稀缺的。未来经济学应当去解释,如何节制欲望,如何解决物质稀缺的感受。

何怀宏。
二是国际社会上的合作与团结的问题。发端于欧洲世界的启蒙思想对当下这个全球化折戟沉沙、各地区分裂对抗愈演愈烈的国际社会并不适用。三是启蒙思想自身具有局限性。用康德的话来说,“启蒙”的内涵就是“公开而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但当下的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盛行,恰恰印证了盛行于美国18世纪、19世纪的进步主义方向过于单一。我们在20世纪尝到了单一方向的进步主义的激进后果。现在也依然在承受这种单一的进步主义的缓进。
最后,两位教授都表示,在焦虑的时代,单靠一本书或单靠书籍,都解决不了人们普遍性、蔓延性的焦虑。而《亚当·斯密传》这本书的意义在于让人们重新认识亚当·斯密这个巨大的历史符号,认识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人性,从历史的脉络里去认知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
撰文|黎璇
编辑|李永博
校对|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