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随着信息收集、分析和计算机运算能力的发展,统计数据已经成为人们论证观点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时候,它甚至被认为最客观、最真实。换句话说,统计数据不只是统计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人们需要了解不同社会、不同群体的差异时,即便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个动态也可能使用有利于论证本人观点的数据。
数字确实可能传递了一种客观真实和事实确凿的力量,在人们所熟悉的表达中就有“百分比”,以一个群体的收入类比于另一个群体。而像这样的比较还有更多。但是受制于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局限,数字却未必能反映真实的情况,而纵然数字是正确的,描述这些数字所衡量的内容的词语也可能存在差错、谬误。

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美国种族简史》《歧视与不平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等作品。
享誉当今学术界的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认为最重要的,倒不是这些数字或描述性词语有何种缺陷,而是数字背后经常隐藏着需要反思的、存在根本性错误的假设,最终因为遗漏关键性因素而产生认知错误。揭示歧视、不平等现象的数字的确具有一种巨大的感召力,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有着追求包容、平等社会的朴素愿望,可遗憾的是,恰恰也因此容易被误导,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所有声称发现了歧视或不平等现象的数据。在索威尔看来,在202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戴维·卡德(David Card)等三人,其统计数据也同样存在谬误。
下文经中信出版社授权节选自《歧视与不平等》一书,内容有删节,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文中提到的“Ⅰ类歧视”和“Ⅱ类歧视”为索威尔区分的两种歧视类型。前者是基于个人品质差异的歧视,后者是出于对种族、性别、地域等身份的群体性歧视。
原文作者 | 托马斯·索威尔
摘编 | 罗东

《歧视与不平等》,[美]托马斯·索威尔 著,刘军 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8月。
在21世纪初一场漫长而激烈的政治和媒体运动中,有人声称,对黑人住房抵押贷款申请者存在着明显的歧视,各种来源的数据被反复引用。相关数据显示,最理想的抵押贷款的黑人申请者,比条件相同的抵押贷款的白人申请者被拒绝的次数要多得多。

电影《激辩风云》(The Great Debaters 2007)剧照。
例如,在2000年,美国民权委员会的数据显示,44.6%的黑人申请者被这类抵押贷款拒绝,而只有22.3%的白人申请者被拒绝。这些以及其他来源的类似统计数据,引发了对抵押贷款机构的广泛谴责,人们要求政府“有所作为”以制止抵押贷款机构中猖獗的种族歧视。美国民权委员会的同一份报告显示,黑人申请传统抵押贷款被拒之门外的概率是白人的两倍。但报告包含的其他统计数据显示,白人被同样的抵押贷款拒之门外的概率几乎是“亚裔美国人和夏威夷原住民”的两倍。
白人申请者的被拒率为22.3%,亚裔美国人和夏威夷原住民的被拒率为12.4%。但这样的数据很少(如果存在)见诸大多数报纸或电视新闻节目,因为黑人和白人的差异足以让记者相信,种族偏见正是根源所在。
这个结论符合现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显然不需要去验证它是否符合事实。这一重大遗漏,使得盛行的偏见在政治、媒体和许多学术界的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亚特兰大宪法报》是少数几家曾经考虑对黑人和白人统计差异做出其他解释的媒体之一。该报的相关报道显示,52%的黑人的信用评分太低,以致他们只有资格获得不太受欢迎的次级抵押贷款,16%的白人也是如此。因此,在《亚特兰大宪法报》引用的数据中,49%的黑人最终获得了次级抵押贷款,13%的白人和10%的亚洲人也获得了次级抵押贷款。简而言之,这三个群体在他们可以获得的抵押贷款种类方面的排名与他们各自的平均信用评级排名相符。
但是这样的统计数据,对盛行的先入为主的观念——群体间的结果差异揭示出种族偏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而,大多数大众媒体几乎从未提到过这些数据。与信用评级一样,统计数据与这样一类歧视(即将每个申请人作为个体进行判断)是一致的,但媒体、政治和学术界则将其作为另一类歧视(对整个群体存在任意的偏见)的证据进行了报道。

电影《绿皮书》(Green Book 2018)剧照。
虽然遗漏的统计数据会使白人贷款审查者对黑人申请者存在偏见这一普遍误解破灭,但这种误解至少看起来是合理的,即使它经不起更严密的审视。但是,认为白人贷款审查者会歧视白人申请者而青睐亚裔申请者的想法,听上去就是不合理的。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黑人拥有的银行也歧视黑人申请者。但事实是,黑人拥有的银行比白人拥有的银行利率更高,导致黑人住房抵押贷款申请者拒绝了它们。
在讨论收入差距时,另一个经常被忽略或扭曲的重要因素是时间维度。最底层20%的人,经常被称为“穷人”。如果这些人的收入在几年内没有太大的变化,就可以说“穷人”的收入停滞不前。但是,绝大多数最初处于底层的20%的人并没有原地踏步。一个谈不上神秘的事实是,大多数人都是以较低的职位开启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在获得了更多的经验、技能和成熟度,以及可以用来评判他们更长的履历之后,他们的收入比最初几年的收入要高得多。
密歇根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在1975年至1991年跟踪了一组给定的美国工薪阶层人士,研究发现,最底层的20%的人中的95%在那段时期结束后已经不在最底层了。此外,最初处于最底层那20%的人中有29%一路上升到最顶层的20%,而只有5%的人仍然处于最底层20%的位置。
由于20%的5%等于1%,因此在整个研究期间,只有1%的抽样人口构成了“穷人”。关于“穷人”在此期间的收入状况的说法,只适用于这1%的人。

电视剧《破产姐妹》(Broke Girls Season)第一季(2011)剧照。
若在讨论高收入阶层的人时忽略时间维度,现实也会发生类似的扭曲。他们经常被视为永久的富人,而不是在这一阶层中昙花一现的人,就像低收入阶层中的“穷人”一样。因此,《纽约时报》2017年的一篇文章称,“处于收入分配最顶层的20%的富人”,“自1979年以来”比其他人获得了多得多的收入。
考虑到1975年到1991年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率,同一批人在1979年到2017年这段更长的时间里仍然处于前20%的隐含假设,就更令人震惊了。当然,流动率这一概念被忽略了。另一项规模相对较小的统计研究,只跟踪了一组给定的美国人长达数年的时间。研究发现,现实与媒体、政治或学术界通常描绘的截然不同:“在25岁到60岁之间的某个时候,超过3/4的人发现自己处于收入分配前20%的高收入阶层。”
对其他阶层的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嫉妒或憎恨处于前20%的人,就意味着嫉妒或憎恨多年之后的自己。《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有所谓“偏爱的20%”,实际上就是全体美国人中的绝大多数。此外,令人怀疑的是,3/4的美国人把他们的工作当作一种爱好而不是谋生的手段。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 2006)剧照。
将特定收入阶层的人称为“穷人”或“富人”,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是这些阶层的永久成员,而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不会在20年间停留在同一阶层。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英国和新西兰的研究,也发现了低收入人群中的这种暂留模式。
最高收入阶层的流动率,甚至比一般阶层的流动率更高。在1996年被广泛讨论的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人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在2005年仍然停留在最高阶层。虽然最高收入阶层的人堪称“百里挑一”,但这种说法只在给定的瞬间是正确的。在人的一生中,这个比例是1/9,因为11%的美国人在他们一生的某个阶段会处于这一阶层。最富有的1%的人的流动率甚至更高,而全美收入最高的400人的流动率是最高的。
在试图找出黑人和白人之间经济和社会差异的原因时,一些观察人士将这些差异主要归因于黑人社区以外的人采取的政策和做法,而其他观察人士则将这些差异归因于美国黑人和白人行为模式的内部差异。

电影《激辩风云》(The Great Debaters 2007)剧照。
在寻求解决这个问题时,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主要依靠民意调查的统计数据。根据威尔逊教授的说法,这些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贫民区居民,无论是否有工作,都支持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在一项调查中,“来自贫民区贫困人口普查区的黑人受访者中,只有不到3%的人否认努力工作对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重要性,66%的人则表示努力工作非常重要”。
尽管威尔逊教授承认“调查不是了解根本态度和价值观的最佳方式”,他还是对“媒体对市中心贫民区‘底层阶层’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错误看法”进行了反驳,表明了“市中心贫民区的居民,实际上是支持而不是破坏了美国提倡的个人奋斗的基本价值观”。
尽管威尔逊教授依靠民意调查驳斥了贫民区居民与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的说法,但人们的言和行并不存在必然的相关性。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低收入人群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9%的人认为赊购商品是个坏主意。尽管如此,“大多数家庭在购买主要耐用品时还是选择了信用贷款”。
经济学家倾向于依赖“显示性偏好”而不是口头陈述。也就是说,人们的所作所为,能比他们的口头陈述更好地揭示他们的价值观。即使人们给出诚实的答案,表达了他们真诚的信念,也无济于事。例如,一些人对努力工作的概念,未必与另一些人的相同,即使两者使用了相同的词语。
富裕的夏克海茨地区的黑人学生,在功课上比他们的白人高中同学花费了更少的时间,他们花费了更多的时间看电视,这就是他们的显示性偏好。其他来源的数据显示,美国黑人和亚裔美国人在高中时花在学业上的时间差异更大。这种差异并非黑人或美国所特有。例如,在澳大利亚,华裔学生花在功课上的时间是白人学生的两倍多。
在澳大利亚、英国或美国等以白人为主的社会里,亚裔学生总体上在学业上比白人学生表现得更好,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吗?在世界各个国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学生学习非常努力,他们在国际竞赛中取得的成绩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学生。
根据人们的口头陈述编制的统计数据,可能会贻害无穷,如果这些统计数据导致人们相信其中的数据是真实的,人们就可能以此对社会政策做出严肃的决策。
顺便说一句,不同群体在教育上投入的精力和教育成果的质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与遗传决定论的观点是相悖的。我们如果发现一些种族的学生花在学业上的时间和精力比其他种族的学生少,但教育结果却优于其他种族勤奋学习的学生,就能将其作为支持遗传决定论的证据。但是,这样的证据似乎并不存在。
当试图从统计数据中确定群体间的收入差异是否涉及Ⅱ类歧视时,收益的一个常见错误会使这种比较变得不可靠,那就是将个人与所谓“相同”的教育或其他资格进行比较,而这些资格在实际意义上是不一样的。比较具有“相同”教育年限的黑人和白人,显然不能等同于对20世纪早期大部分时间里接受相同教育的黑人和白人进行比较。
在那个时代,大多数黑人集中在南方各州,他们的种族隔离学校通常学制较短,还有其他的不平等存在。那个时代的一项研究显示:“一个在学校学习了6年的黑人学生,每年上学3个月,最多只能完成白人学生6年课业的一半,因为白人学生每年上学6个月。”然而,从统计上看,他们的教育年限“相同”。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 2006)剧照。
很明显,这种情况存在Ⅱ类歧视,但不能通过统计数据的搜集地点来确定歧视发生的地点。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相同”的黑人和白人工人获得不同的工资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源于雇主的偏见与歧视,这与黑人工人接受雇主的工作之前在学校体系中存在多年的偏见与歧视是不同的。
同样,在后来的时代,当学校在法律上不再被种族隔离之后,黑人高中毕业生的教育考试成绩仍然低于比他们年轻几岁的白人学生。在这种情景下,雇主没有向黑人工人支付与“同等”教育程度的白人工人一样的工资,并不一定是因为工作场所存在Ⅱ类歧视,即使统计数据是在工作场所搜集的。但是,当对心理测试结果相同的个人进行比较时,黑人和白人的收入是相当的。
统计数据往往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比较那些真正具有可比性的个人。一个非常相似的问题会影响总的来说具有“相同”资格的男女工人的比较。但是,如果女性兼职比例较高且连续工作年限较少(由于花时间照顾年幼的孩子),或者她们拥有大学学位但是所学专业没有为她们从事高薪职业做好准备,那么总的来说,将具有“相同”资格的女性和男性做比较,就是拿苹果和橘子做比较。
在可以获得更广泛的工作资格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比较来自不同群体真正具有可比性的个人。此时,收入差距往往会缩小,接近消失,有时甚至不平等现象会逆转。例如,早在1972—1973学年,白人教员的收入就高于黑人教员。但是,当我们将这些来自相同领域,来自各自学科排名相似的院系,以及发表文章数量相似的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员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黑人教员的收入高于白人教员。同样,男性教员的收入高于女性教员。但是,在同样资格的教员中,从未结过婚的女性比从未结过婚的男性收入更高。

电影《保姆日记》(The Nanny Diaries 2007)剧照。
经济学和其他领域对复杂统计分析的强调——在许多情况下,无论这种统计分析多么有价值,甚至至关重要——仍然可能导致人们忽略简单但基本的问题,即这些复杂分析所依赖的统计数据实际上是否起到了或声称起到了测量数据的作用。将年薪和多年资本收益汇总在一起的“收入”统计数据,只是许多统计数据中的一组,这些统计数据可以在这一基本层面经受住更严格的审视,特别是当影响数百万人的法律和政策基于统计结论时。
即使不能说令人痛苦,至少也是令人不安的,那些简单而明显的谬误在知识界得到普遍认可,甚至似乎推动了所谓“社会正义”的流行愿景。当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大型国际统计研究,尽管哈佛大学斯蒂芬·平克教授指出了其中明显且根本性的错误陈述,但是这项研究还是在许多国家获得了好评:托马斯·皮凯蒂2014年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在由不平等引发的轩然大波中成为一个护身符。他写道:“如今,较贫穷的一半人口和过去一样贫穷,2010年他们的财富仅占总财富的5%,与1910年时一样。”但是,今天的总财富比1910年要多得多,所以,如果贫穷的那一半拥有同样比例的财富,他们会更富有,而不是“如此贫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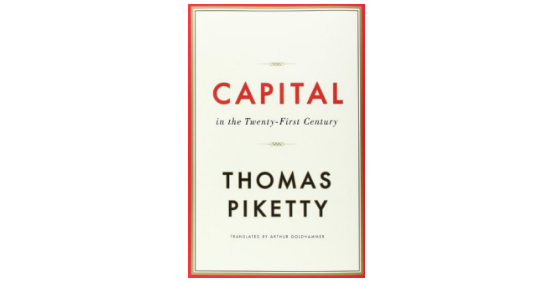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书封。
除了谈到百分比——就好像百分比代表了一个世纪以来一定数量的收入或财富一样,皮凯蒂教授还做出这样的断言,即在收入方面,“前10%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事实上,超过一半的美国人会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一刻处于前10%。当皮凯蒂声称最富有的1%的人处在“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结构”的顶端时,他再次在口头上将变化的人群组合,特别是收入阶层,转变为一个固定的结构,而不是视其为一个流动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美国人不会在10年中保持在同一阶层。

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 1987)剧照。
这些错误陈述是对同一基本误解的不同表达。正如一项对400名最富有的美国人进行的实证研究指出的那样,皮凯蒂教授“天真地假设是同一批人变得越来越富有了”。但400名最富有的美国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奋斗一生才获得如此巨额财富的,而不是过去400名最富有的人的继承人。
这种误解并不是皮凯蒂教授特有的,也不是他的统计数据存在的唯一问题。但是,这种简单而明显的错误陈述仍然获得了知识界的认可,这才是远远超出托马斯·皮凯蒂的问题和危险。收入差异无论是在税前还是税后进行衡量,都可以改变不平等的程度。如果在税后和政府调节税费之后再衡量不平等,无论是在金钱还是在商品和服务方面,这种不平等都能被显著缓解。因为高收入的人缴纳了更高的税收,低收入的人则获得政府调节的大部分税收。当税率变化被描述为“增税3000亿美元”或“减税3000亿美元”时,关于税率本身的统计数据可能极具误导性。在现实中,政府能做的就是改变税率。国家能获得多少税收,取决于人们的反应。有过高税率带来低税收的时候,就有过低税率带来高税收的时候,也有过税率和税收同步增长或减少的时候。
原文作者 | 托马斯·索威尔
摘编 | 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 | 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