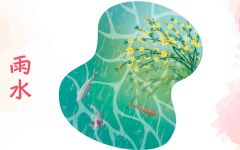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明代 居节《山水册·江南新雨》。
蹒跚学步的孩童,就听着老一辈呢喃念叨着“春雨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年年岁岁的成长,随着四时轮转,看枯枝生出嫩绿,看春花一夜盛放,看夏雨倾盆而至,听木叶萧萧落下,听秋虫唧唧作声,听冬雪纷扬,大音希声。童谣里的呢喃,正变成眼中可见的风物变幻。
孩子的眼睛毕竟澄澈,总能从节气的微妙推移中发现种种不同。他们能发现第一片从土中钻出的绿草,第一只飞回屋檐下的小燕,第一只喳喳聒噪的鸣蝉,他们能尝到雨水里的甘甜——也许未来也会尝出里面的苦涩,也能从窗户结出的霜花上看到莽莽苍苍的雪山寒林。赤日下逐渐融化的雪人,会在渐渐凋零的童年记忆中,看着他们在二十四节气的轮回又轮回中长高、长大。
年纪渐长,对周遭的节气移转早已司空见惯,奔走于水泥丛林交织切割的苍穹之下,或许只有冷暖雨雪才能提醒自己被单调的生活牢笼的迟钝感官,毕竟又是一个节气了。然而,或许在某个时刻,当春日和煦的阳光抚摸着疲惫的肩膀,当遍洒大地的雪花掩盖了奔走的足迹,儿时对节气敏锐的知觉,会在那一刻重返心头。
节气是人类为时序变化划分的刻度,就像表盘上的指针,提醒着人们时光的流逝。但它不是水泥丛林中数字化的时间,也不是数字变化的电子表。就像已经到来的立春,《群芳谱》中所谓“立,始建也。春气始而建立也。”立春是开始,而这个开始,并不是在立春这一天刚交子时的那一刻开始的,而是一个长久而细微的酝酿过程,是冰雪悄无声息地消融,是春风挟着暖阳吹开封冻的河面,是路边不知何时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绿色,是一层青色的薄纱在不经意间渐渐铺满了大地。
即将到来的雨水,也如同唐人韩愈诗中所言的一般,乃是: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春雨不会像钟表一样有节奏地滴答作响,而是迷迷蒙蒙的朦胧感,就像韩愈所写的那样,它是“润如酥”的。这个比喻之绝妙在于,它与农谚中所谓“春雨贵如油”恰可般配。这句俗语常常被认为是春雨稀少,因此像油一样珍贵。但事实上,它最早的来源是北宋《景德传灯录》中的一句禅语“春雨一滴滑如油”。明人《清平山堂话本》有小说《解学士诗》一则,讲述明初才子解缙也曾作过一首春雨诗:“春雨滑似油,下得满街流。跌倒解学士,笑杀一群牛。”清人李光庭《乡言解颐》也写道:“春雨贵如油,膏雨也。”
膏者,即是油脂,与酥同类。像油脂一样的毛毛细雨,落在地上,地皮只是薄薄地洇湿了一层,表层的泥土被雨水润泽,变得像脂膏一样,走在地上,便觉得滑滑的,但遥看草色,却又像是大地涂上了一层脂粉油彩。雨水,就在这片彩妆脂粉的润泽下,滑滑跌跌着脚步走来了。
二十四节气,就这样如立春消融的冰雪,如雨水润泽的草色,无声无息地走入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它是人类与天地之间订立的文字契约。天行有常,地载万物,人居其中,节气周而复始,万物生生不息。
天
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见龙。
祭鱼盈浦屿,归雁迴山峰。
云色轻还重,风光淡又浓。
向看入二月,花色影重重。
尘封千年的古卷,在世人面前徐徐展开。虽然岁月已经不知经历了多少节气的轮转,但这卷《咏廿四气诗》(P.2624)依然墨色如新,仿佛它在敦煌藏经洞中成功逃过了世间的寒暑。这首诗便是其中咏雨水节气的《咏雨水正月中》。

元程棨摹南宋楼璹《耕织图》展现春雨时至,农人耕作的场景。
虽然这卷诗被寄名于晚唐著名诗人元稹名下,但它的辞句却并没有元稹那般雅致迤逦,而是清新俗语,对唐人来说,它将节气的特征如平常话头一般徐徐道来:“云色轻还重,风光淡又浓。向看入二月,花色影重重”,这样的如小儿语般的田园文字,即使在今人看来,也并不难以理解。但其中却有一句话,在今人看来有若天书一般:
“平田已见龙。”
难道雨水这天可以在平阔的田野里看到神龙出没吗?有些解读者引用《诗经·郑风·山有扶苏》中“山有乔木,隰有游龙”一句,认为这里的“龙”当作“茏”,乃是“红草也”,也称为马蓼。在田野中看到马蓼草,确实是春意盎然的状貌。但在古代,人们看到“平田已见龙”这句话,脑海中最先反映出来的,却是《易经》中“见龙在田”这句话。
《易经》如今被认为是一部占卜命理之书,仿佛参透了这本书便可以窥破天机,预测人生的旦夕祸福。从某种程度上说,《易经》确实窥破了一些“天机”,但人事却并非几句卦语可以预测祸福。“见龙在田”这句话的含义,并非如字面意思所述,是田野中出现了一条龙,而是一种天文现象:立春时节,苍龙七宿的角、亢、氐、房、心会先后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预示着春天已至。

自太古时代,苍龙七宿的出现就在中国先民的心目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载,一年四季可以用天空中北斗的斗柄指示的位置来确定。当斗柄指向东方时,天下就是春季。沿着斗柄的方向延长30度左右,将会看到一颗非常亮的星,这颗星被称为“大角”,顾名思义,它在古代被认为是苍龙星宿头上的那只利角(古人角宿从大角算起)。沿着大角再向前30度,就会看到角宿。斗柄指东,角宿开始上升,春季因此到来。所谓的“龙”也就渐渐出现在田野之上。
中国的先民发现,当龙宿从田野上昂然上升时,气候也开始转暖,凛冬的寒雪,随之转为春季的绵绵细雨。龙在古人的心目中,本就与水有关,《左传》作为“龙,水物也。”随春风润泽万物的雨水,也就被认为是东方升起的这条苍龙的恩泽。
二十四节气的创生也是如此,《尔雅·释天》注云:
“岁取星行一次,年取禾更一熟,时有春夏秋冬四序,而每序各分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五日一候,三候一气,六气一时,四时一岁,故一岁二十四气。”
听起来玄之又玄,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先民对天文的观测与体察总结出的一种表述方式。虽然中国古代的先民尚未意识到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也不知道地球运行的轨道其实是椭圆形,但他们通过对日出日落的观测,却能发现每年在特定的日期会出现昼夜等分和昼最长、夜最长的现象。
于是这四个特定日期就被定为二分二至,按照顺序排列也就是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先民为太阳的运行轨迹设想了一条圆形的轨道,也就是所谓的黄道,划分为360°。二分二至之间相隔刚好为90°。再通过观察天空中北斗斗柄指示的方向,划定春夏秋冬四季。二分二至恰好又在四季的正中。
顺理成章地,四季又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呢?比如春天的起始,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放在冬至与春分之间,也就是45°的位置上。如此一来,先民就得到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在这八个节气中,每个节气之间再进行细分,均分为三,最终形成了二十四个节气。至于它们的命名,则又系之于当时的天气状况。就像雨水,是因为大致在此期间,春雨时至的缘故。

三月春耕,《贝利公爵的豪华时祷书》,约1415年。
以天象划定农时,并非中国古代先民独特的发明。就在中国的先民仰观天文划定节气的同时,古希腊的先哲也同样利用天象来确定耕作的农时,公元前八世纪的古希腊哲人赫西俄德,在他的劝农哲思著作《田功农时》中,如此写道:
“宙斯结束了太阳回归后的寒冷的六十天,牧夫座第一次于黄昏时分光彩夺目地从神圣的大洋河上升起,潘迪翁的尖声悲悼的女儿——燕子继之飞进了人类的视野,春季便降临人间。要在她到来之前修建葡萄藤。”
“太阳回归”指的即是冬至日。冬至日之后的六十天,刚好就是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立春前后。牧夫座的α星,正是中国先民眼中象征东方苍龙七宿利角的大角星。
西洋的牧夫座与中国的苍龙七宿在东方的天空中升起,春天就这样降临在了北半球的大地上。雨水也随时而至,无远弗届地滋润着期待春天的每一片土地。
地
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
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
烽烟笼罩的金陵城中,玉殿朱梁堂皇依旧,月光透过垂下的罗幕,洒下词人的一片闲愁。城墙外已是修罗世界,但节气却依然会翩然降临在这王气黯淡的故国旧城之中。在城门洞开的前一刻,他感到了春光正在离去,也带走了他心爱的樱桃。

南宋佚名《樱桃黄鹂图》。
南唐后主李煜的《临江仙》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即使是他在金陵城破前夜匆匆写下的草稿,在一个半世纪后的北宋末年,仍然被视若拱璧,小心宝藏。而其中最让人舌华生津的一句,便是那一句“樱桃落尽春归去。”
樱桃这种小巧而朱红色的水果,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1973年,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河北藁城台西村的一处商代墓葬中,发掘出两颗毛樱桃的种子,这种红色的果实,或许也曾被盛在装饰着饕餮纹的青铜器里,由奴隶小心翼翼地捧着奉献给意得志满欣赏人牲的商王口中。战国时代的《礼记》则记载,“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樱桃)先荐寝庙”——樱桃是奉祀给祖先神灵的高贵的食物。后梁宣帝萧詧在《樱桃赋》中写道:
“惟樱桃之为树,先百果而含荣。既离离而春就,乍苒苒而冬迎。”
经过了春光拂拭,雨水滋润,樱桃在古人心目中是最先成熟的果实,也凝结了一个春天的精华。李煜在春光将尽之时想起落尽的樱桃,个中滋味,恐怕不仅仅是数十载宫廷甘腴年华的凋零殆尽,更是他已经再握不住随樱桃一并落尽的金陵春梦了。
二十四节气虽名为“节气”,但节气何时来,何时去,最直接的表现,却并非是日历上的几行文字,而是大地上自然万物生息的提醒。如立春时节的花木作为征候,便提醒着世人春日已至,雨水将临:
“立春一候,金盏贴地;立春二候,银眼遍条;立春三候,早梅馥郁。雨水一候,菟葵动摇;雨水二候,岁兰影瘦;雨水三候,黄连色骄。”
一如樱桃提示着春季已逝,仲夏将近。春日的到来,也最先在大地上留下深深浅浅的足印,提醒着世人,她来过了。
所谓“立春一日,百草回芽”,遥看大地的一片青青,便是春走过的痕迹。万物萌生的立春,大地上的勃然生机,惹得人类也忍不住想沾染一二。唐代诗人杜甫在《立春》中就如此写道:
“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
春盘,就是立春日食用的蔬菜,唐人《四时宝镜》所谓“立春日春饼生菜,号春盘。”孙思邈《齐人月令》更是讲述了吃春饼生菜的意义:“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春盘中的生菜,自然是立春大地萌生的最能代表春意盎然的蔬菜。最能代表春天的蔬菜,当数韭菜。
韭菜实在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国菜。中国最早的农书《夏小正》就写道,正月,“囿有见韭”。《南史》记载南齐高士周颢居家节俭,一日文惠太子召见,问他蔬食何物为最,他的回答成了后世脍炙人口的典故:
“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韭菜诚然是立春节气大地为人类奉上的隽品,它的青色恰好与中国先民所认为的万物萌发生长之色相合,而韭菜作为植物,生命力又顽强得不可思议,屡遭割刈,一场雨水过后,又萌芽涌出地面,屡再长成。东汉《说文解字》云韭,“一种而久生,故谓之韭。一岁三四割,其根不伤,至冬壅培之,先春复生,信乎久生者也”。

明嘉靖刊本《救荒本草》中的野韭图。
一茬又一茬的韭菜,前割后继,连绵不绝,也难怪汉末民谣有言“发如韭,剪复生”。韭菜所蕴含的割而复生的生机,最符合古代中国人心中生生不息之道,因此也被荐入春盘,供人大嚼,也就毫不奇怪了。
东汉名士郭林宗,为招待好友范逵,“冒雨剪韭,作汤饼以供之”,传为友谊深厚的佳话。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化用此典故,“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虽然清寒,但立春雨水,韭芬情长,自不待言。
南宋时代,立春节气,福建有所谓“青韭供盘饼面圆”,临安则是“羊脂韭饼”,这也是今天家喻户晓的韭菜合子的前身。至于韭菜合子的最终成型,于今日也有三百余年的光阴了。清代以老饕名垂后世的诗人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就记载了韭菜合子的做法,当时称之为“韭合”:
“韭合,韭菜切末拌肉,加作料,面皮包之,入油灼之,面内加酥更妙。”
与今天人们开怀大嚼、声动十里的韭菜合子别无二致。也许吃过之后,牙齿上还会留下韭菜青青的颜色。
但也请不必担心,这是立春节气,雨水滋润,大地为人类涂上的一点色彩。

韭菜合子,与三百年前的做法并无不同。
人
暮江平不动,春花开正满。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春江花月夜。单是这五个字放在一起,就美得令人心动。加上书名号几乎像是对它的亵渎。隋炀帝歌咏这首诗时,以他的心高气傲,或许也会意识到这将是他流传后世的寥寥数篇诗文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尤为千古名句。

传南宋赵令穰《船月图》,图中天上月,水中月。可惜水映天上月,不见天映水中舟。
闭目想来,这本是自然现象,翻滚的江潮吞吐着空中的月光,漫天星斗也在江面上洒下波光粼粼。然而唯有人类,方能开动自己的想象力,将天地万物结合在一起,诉之以笔墨,使千载之下的后世,仍能透过他的文字,去“看”到那个美得不可方物的春江花月夜。
二十四节气与人类的关系亦复如是,节气为中国先民所划定,所阐释,又成为感知四时的刻度,农业耕作的提醒,文人歌咏的对象。人们也因此附会以风俗。
就像东晋《拾遗记》所记载的“天穿节”:“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缕系煎饼置屋上,曰补天穿。”虽然在民俗传说中,这与女娲补天相关,但仔细查考,就会发现这一天临近节气中的雨水。女娲补天,其目的在于治水,换言之,是民众渴盼雨水,又期望不要阴雨霏霏、如天穿一般倾盆而至,反倒让贵如油的春雨,成了毁伤庄稼的灾害。
诚然,天行有常,四时运行,并不因人类的好恶而加以改变。就像酷爱春天的隋炀帝,为了能在寒秋凛冬留住春光,令宫人修剪繒彩为花,遍插宫苑,然而终于是留春不稳,空销尘土,只余雷塘数亩田而已。但顺应节气者,天地亦会还报于他。立春时节鞭打土牛以摧耕,雨水前后的插秧栽树。“春来有雨庄稼好,大春小春一片宝”“雨水节,皆柑橘”。农谚中所体现的乐观与积极,既是天地以节气为人类奉上的馈赠,也是人类以辛劳对天地馈赠的报偿。

《剪彩为花》,出自明代彩绘本《帝鉴图说》。
岁月流转,节气轮回,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就在这篇文字读罢之时,时序又向着新的节气悄无声息地迈进了一步。它的足印藏在萌芽的草木之间,藏在飞来的流莺身上,在春日的阳光下铺就青色的影子,也在濛濛烟雨中漫步在小巷的石板路上。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作者 | 王逸之
编辑 | 宫照华 李阳
校对 |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