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携手世纪文景,共同推出“去溯时、去现场:历史的凝视与书写”主题活动。
当滞塞的时间重启,我们以“历史”为方法,重新定位自己。5场线上活动,12位知名嘉宾,跨越史事与故事、田野与文本、艺术与考古。
6月18日(周六)系列活动最后一场,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做客直播间,共谈“美术考古与考古美术”,探究美术史与考古学的学科分野与交叉。
扫描二维码,关注视频号
收看直播回放
关注日后精彩直播

“美术考古”一词的源流始于何处?“考古美术”与“美术考古”两大概念,是否有明确区别?美术史和考古学两大学科,如何实现交融互动的可能?
郑岩溯源至德国考古学家阿道夫·米海利斯(Adolf Michaelis,又译作亚多尔夫·米海里司)、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与中国学者郭沫若,详细梳理“美术考古”概念的历史。
巫鸿指出,“考古美术”不同于“美术考古”,二者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就像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将基本概念辨析清晰,才能确证考古学和美术史不同的学科特性,以便后续研究深入展开。
“考古美术”与“美术考古”虽有所区别,却并非彼此隔绝。巫鸿认为:“区分概念,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加法,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就像这场讨论,不是为了划定学科圈层,而是为了帮助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学者打开更加多元的、跨界的视角,让学科间持续互动,产生更加丰富、细致的新东西。
01
概念溯源
“美术考古”一词从何而来?
郑岩对“美术考古”概念的思考,源于对自己的疑惑。“我本来是学考古的,毕业后在博物馆工作,后来调到中央美院教书。我个人也常常疑惑,自己的研究究竟属于考古学还是美术史?”
在学术历史中探寻,“美术考古”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考古学者阿道夫·米海利斯所著的《美术考古一世纪》一书中。郑岩对比不同版本译本发现,1906年该书第一版出版时书名为《19世纪考古学的发现》,1908年再版才改成现在的名字。所谓“美术考古”,在德文版里叫“Kunstarchäologie”,翻译成英文是“art archaeology”。米海利斯说“Kunstarchäologie”在这本书里相当于“考古学”,由于他讲的这些考古发现主要是艺术品,所以在前面加了一个表示限制的“kunst”(德语,艺术)。
1929年,郭沫若流亡日本,听闻国内开始发掘殷墟,非常兴奋,迫切地想要了解考古学。他去拜见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看到米海利斯这本书的日译本,主要介绍19世纪的考古学发现。郭沫若边看边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沿用了滨田耕作日译本的翻译方法,在书中使用了“美术考古”一词,该词由此在中国首次出现。

1998年出版的由郭沫若翻译的《美术考古一世纪》
郭沫若以这本书为起点,了解什么是“锄头考古学”,也就是常说的田野考古学,开始走向殷墟的甲骨文研究。翻译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推动古文字学和史学研究,但因为郭沫若影响力太大,这本书的书名流传太广,“美术考古”一词从此应用开来。
1959年,《考古》杂志第7期开始刊登《全国主要报刊考古论文资料索引》,其中专门列出“美术考古”一类。这大概是比较早的对这个词的文字记录,这里强调的重点是使用考古学方法,特别是地层学、类型学方法来研究田野考古发现的艺术品。
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考古学家夏鼐、王仲殊在“考古学”词条里,把“美术考古学”列为一个考古学门类,这是考古学家历来认同的定义。五年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出版,考古学家杨泓又专门写了一个“美术考古”词条。该词条与“美术考古学”定义一致,但因为“美术考古”收录在美术卷里,很多研究美术史、美术理论甚至美学的学者就开始讨论“美术考古”究竟应该归属哪个学科。有人认同它属于考古学的分支,有人认同它属于美术史、美术理论的分支,甚至还有观点认为它不属于某一分支,而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郑岩提到,杨泓很喜欢米海利斯书中的一句话,“禾黍割了,应该有束禾的人来做他的谦卑的任务。” 郑岩认为,这句话也是杨泓对自己的定位,他的研究非常节制,“美术考古”的工作只做到这一步,其他的工作留给美术史研究者进一步开展。
郑岩溯源“美术考古”的背景,并非为了维护或者推翻一个学科。“我觉得这个词是一个概念工具,大家在使用这个工具之前,还是应该搞清楚使用它的出发点、背景、目的,研究者也需要一个更明晰的自我认定。”
02
概念区分
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加法
在西方学术界,并无“美术考古”一词,近似的概念或许是“古典美术史”,主要研究古典时期希腊、罗马、埃及的美术品和艺术史,但材料范围明显比国内“美术考古”的定义窄。
巫鸿指出,随着美术史和考古学学科概念的细化,各自应用的材料对象、方法手段、知识概念都会得到扩展,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也更加频繁。
例如,考古学从田野考古、史前考古、历史考古拓展到城市考古、农业考古,如今随着技术进步,还产生水下考古、空间考古等新的分支。美术史最初按照中国美术史、日本美术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等比较传统的形式来进行分类,近年来兴起的新研究方向包括全球美术史等,希望摆脱简单的以民族、国家进行区分的方式,注重各地区、各类别间的联系,更符合现代的研究需要。
巫鸿提到,敦煌、故宫早先已开始用数码技术发掘、研究艺术品,但数码美术史这一概念近年才出现。“在细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特殊性格。”中国的墓葬美术延续几千年,现在还在持续发掘中,这是中国美术史的独特之处,很难按照西方对美术史和考古学的大体分类进行概括。
考虑到中国美术的材料和中国美术史的特性,巫鸿认为“考古美术”应当作为美术史里很重要的分支,有自己的研究材料、研究方法,以及和其他领域的互动。
巫鸿提醒,“考古美术”不同于前文提及的“美术考古”。
从词语结构看,“美术考古”里考古是重心,这个词也被夏鼐等考古学界前辈列为考古学门类,因此归入考古学分支更为恰当。考古学家宿白1962年受邀在敦煌研究所做过《敦煌七讲》学术报告,写过《中国石窟寺研究》《白沙宋墓》等名作,结合考古学框架,对美术史、图像学展开观察,足见“美术考古”学术传统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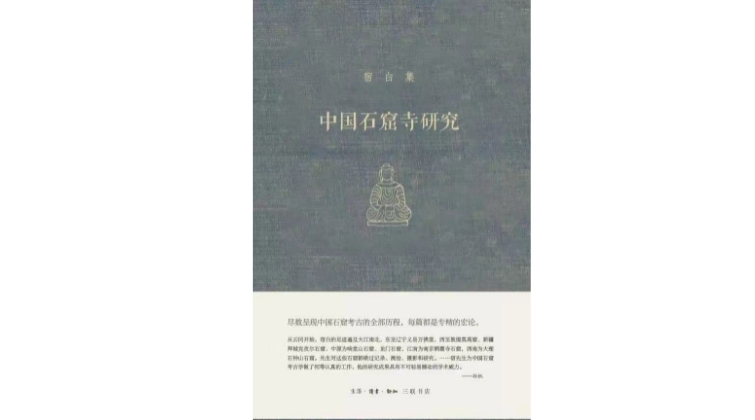
宿白所著《中国石窟寺研究》,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考古美术”则更强调美术史,考古学家俞伟超曾提及这一概念,巫鸿本人去年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也曾做过“考古美术中的山水”系列讲座,内容将集结成《天人之际——考古美术中的山水》一书在近日出版。
巫鸿认为,“考古美术”有两个方法论层面的基本含义。首先“考古美术”研究的材料由考古发掘而来,包含墓葬品、沉船打捞品、地面的建筑遗址等,也包括传世的实物和文献,因而与其他门类的美术史研究有所交叉。其次,“考古美术”对材料的分析、解读大体遵循美术史的学科框架,研究重点在于图像和作品,关注视觉表现的题材、媒材、原境、源流等美术史学科概念。
将“考古美术”和“美术考古”进行区分,目的并非彼此隔绝、划分圈层。巫鸿认为,如果基本概念、定位不清晰,接下来的研究很难顺利开展。“如二者都研究陵墓,但理念和角度有所区分。这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加法,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让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都更加丰富、细致,彼此互动、启发、共享,产生更有意思的新东西。”
两个领域中的学者身份也可以实现跨界。如张光直本身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同时也对图像研究很有兴趣,曾撰文分析铜器上的纹饰,详述从动物震慑人到人征服动物的历史。金维诺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学科主要创建人,同时也很留意考古学发现,北齐娄叡墓刚刚发现时,他很快注意到墓中壁画上的人物脸型特殊,联想到北齐著名画家杨子华的作品《北齐校书图》,使美术史研究与考古学研究得以融合。郑岩写过《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书中采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前半部分主要从考古学视角出发,运用诸如分区、模式等考古学概念;后半部分则进行个案分析,每个个案代表一种特殊的艺术现象,从体裁内容、图像程序、绘画方式等角度入手进行分析。可见“考古美术”和“美术考古”并非泾渭分明,不同学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入手,进行融合、提升,找到自己的叙事方式。

郑岩所著《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03
考古学与美术史研究的未来
学科间的“切割”应当转向“突围”
考古学家柴尔德曾谈到考古学与美术史研究的区别。比如同样是研究腓尼基人和埃及人的陶瓶,考古学者关注陶瓶的所有特征,包括形态、纹样、题材等等,从而进行断代研究,区分两个族群在陶器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差别,辨别不同文化的整体面貌。美术史学者则对笔法、图式、风格等方面更敏感,可以此入手,鉴定陶瓶上的图案究竟出自哪位画家。
郑岩发现,近年来考古学和美术史之间关系的冷热变化,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郑岩的老师、考古学家刘敦愿是美术专业出身,1972年在山东大学创立考古学专业。当时,考古学框架尚未完全建立,考古专业归属历史系,“美术考古”在学术圈中亦处于边缘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如北京大学研究先秦考古及中国古汉语的研究者李零所言,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切割”,也许有其合理的一面。
然而近二十年来,考古学发展的瓶颈越来越明显,不少年轻学者开始产生类似焦虑,“宿白先生的石窟寺研究做得极好,我们却有些绝望,好像只能再做一些边缘的、小型的、查漏补缺的工作。”此外,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和博物馆、美术馆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对艺术产生兴趣。这时,学科间的“切割”不再是第一位的,“突围”开始具备热度,突破原有框架、和其他学科构建联系,被很多学者提上日程。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霍巍一再呼吁,要建立清晰的历史考古学框架,首先必须借助很多其他学科的支持。在他的带动下,很多年轻的考古学者陆续响应,在考古学研究过程中融入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巫鸿对此表示认同。随着时代和实际情况的发展,原本的学术定位会变得僵化,最初带有启发性的方法会慢慢变得程式化。这时就需要引入新的思想,做出新的“突围”。
巫鸿本人的学术背景可说是“突围”的实例。他最初是美术史专业出身,后来分到故宫做文物研究,更多地接触考古内容。到了1970年代,考古发现频出,展览不断,整个社会对此投射很多关注,受此风潮影响,巫鸿前往哈佛大学,选择历史人类学作为新的研究领域。但巫鸿对传统人类学中的大数据分析和体质人类学(通过对人类群体体质特征和结构的剖析——如骨骼特征——来研究人类的起源、分布与发展)兴趣不大,他还是对文化、艺术、美术更感兴趣,想要回到中间地带。张光直先生通过一番努力成立了一个特殊委员会(不隶属于任何系),巫鸿可以在这里学习,但学习的课程增加了一倍,内容跨越人类学、美术史和思想史。毕业后巫鸿留任哈佛大学,在美术史系任教。回顾自己跨越多学科的研究学习经历,巫鸿认可郑岩提到的学科之间的“切割”有时候或许不可避免,但学科之间若能不断创新、实验、融合,可能会受益更多。
若想实现学科间的融合,巫鸿认为在现存的学科机制和结构之外,应当探索一种软性的结构,便于学者们主动沟通,形成持续性的探讨。
2009年,巫鸿、郑岩以及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共同组织了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每次集结二十来位学者,涉猎考古学、美术史、历史等不同学科背景,来自中、英、美、加、日、韩等多个国家地区,共同研讨古代墓葬美术。
这类会议组织并非一个固定的机构,也没有固定的参与人选,但会慢慢形成一种机构性的体系,大家共同研究、出版、发行。这与现存的学术机构之间,产生了互补关系,讨论更加自由。通过讨论,考古学和美术史不再泾渭分明,无论“考古美术”,还是“美术考古”,都围绕“墓葬”这一核心进行。
巫鸿提醒学生和年轻学者们,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学习特别重要,若要实现新的研究突破,“第一步是做好学科的专业训练,以便发现问题,有所联想;第二步是关注新的渠道、新的材料,在交叉互动中,实现思想和学问的突破。”
| 延伸阅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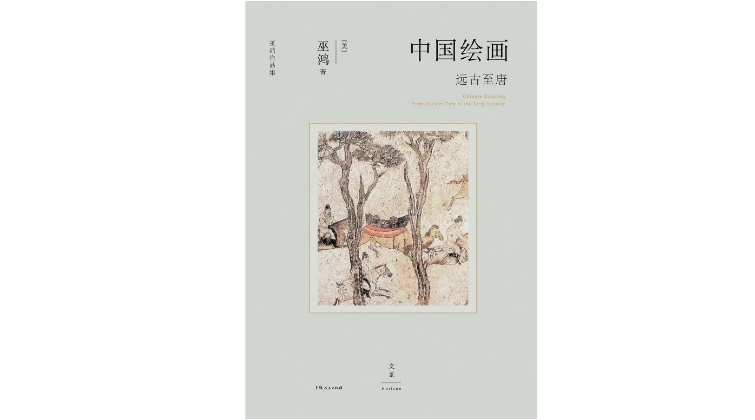
《中国绘画》
作者:巫鸿
出版社: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文整理/段雅馨
本文编辑/吕婉婷
海报设计/刘晓斐
本文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