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捷克发表演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7年索邦大学的演讲相呼应。他对欧盟的未来提出了新的愿景与希望,他认为欧盟应当扩张到西巴尔干国家,并改变曾经的一致同意原则,转变为多数赞同制。舒尔茨的演讲被视作欧盟对外政策的转向:由昔日对主权的模糊处理,向立场鲜明的“欧洲主权”进行转变。这意味着欧盟在外交与防务问题上独立于北约,并且经济上主动出击,不再依赖单一的能源和出口市场。舒尔茨的宣言被媒体视作欧盟的主动转向,力图成为世界政治版图的一极。然而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与现实,尤其是作为欧洲地理枢纽与欧盟决策核心的德国在战后欧洲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就会发现,舒尔茨的雄心壮志来自于欧盟理念所支撑的美好愿景。但是现实往往需要更加审慎的评估与回溯历史的视野。
德国历史学者明克勒在《执中之权》中,对战后德国主导建立的欧洲格局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与展望。在他看来,欧盟的核心问题都来自于德国对自身历史作用的定位。无论是希腊债务危机,还是难民问题,以及当下欧洲迫在眉睫的能源危机。然而现实政治中的德国却常常显得左支右绌,欧盟普遍性的价值追求呼吁着德国进行更多投入以及超越主权视角去介入欧洲政治,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以及国内政治的掣肘却经常使得德国领导人在欧盟问题上心口不一。这种窘境与德国在19世纪崛起后特殊的发展道路有关,更取决于二十世纪德国对战争责任与欧盟理念的认知。作为一个不情不愿的领导者,德国的尴尬不仅源自于对自身政治角色的困惑,还来自于作为后发的大国,德国政治精英怎么理解民族国家与欧盟这两种不同的概念。
然而,曾经作为人类政治史上的一次伟大实验的欧盟,是否会在地缘政治危机不断加深的今天,以更积极的角捍卫和平,使二十世纪的灾难与战争永久地成为过去?这不仅需要政治家们重振自己的理想与志业,更需要一种尊重历史的审慎与超越主权的视野和责任感去再次重申那些撼动人类历史与心灵的原则。这场考验也许才刚刚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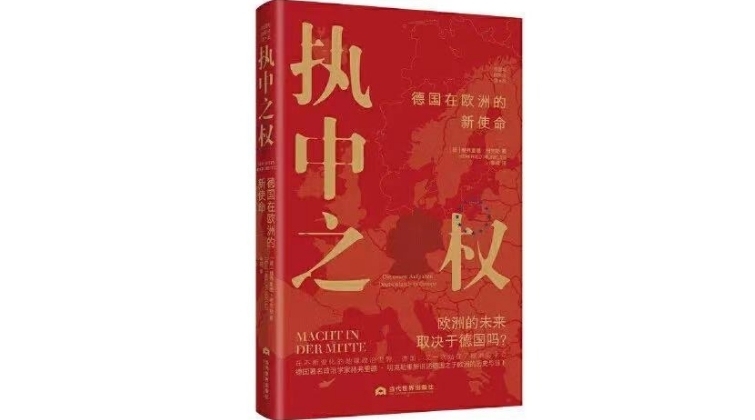
《执中之权》作者:(德)赫弗里德·明克勒 译者:李柯 版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年5月
从2010年希腊引燃了欧元债务问题的危机以来,欧洲在过去十二年中事实上经历了三次重大危机:由欧债危机引发的欧元区财政责任与经济政策危机;由难民危机引发的欧盟边界管理与政治认同危机;由地缘政治恶化引发的欧盟外交政策与安全危机。
这三大危机都被视为可能让欧盟和欧元区走向终结的重大事件。欧债危机重燃了所谓“北欧集团”与“南欧集团”之间的争端,在财政紧缩、严格的赤字债务纪律和强调自由主义经济的北欧、低地和英德阵营与财政扩张、以庞大的国家公共开支和举债维持福利的地中海国家中,围绕着欧元究竟是富裕国家被迫为相对贫穷的国家纾困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被迫接受富裕国家所制定的货币政策引发了争论。而在一些观点中,这场争论甚至同曾经分裂了南北欧洲的“新教伦理”和“天主教伦理”联系起来,从而隐隐照应出欧洲的历史性裂痕。难民危机直指欧盟的政治身份认同问题:欧盟究竟是一个后民族国家的、以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观为基石的政治联盟,还是一个必须始终紧抱欧洲基督教文明身份认同的共同体。至于俄乌矛盾而引发的外交纠葛,就更折射出欧洲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困境:面对边缘的强大邻国,欧洲是选择对抗,还是选择接纳?

在政治学家赫弗里德·明克勒的政论作品《执中之权:德国在欧洲的新使命》看来,这三场危机之所以对欧盟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欧盟自身的战略定位和认同没能脱离持续数百年的“欧洲问题”所遗留的裂痕影响。而也正因为此,德国的地位才在欧盟中至关重要;德国的决定才在欧盟决策中举足轻重;德国的选择才与欧盟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在三场危机中,德国都扮演着无法绕开的核心角色:是德国强迫希腊接受紧缩政策,也是德国同意和IMF合作为希腊提供纾困贷款;是德国不能赞同让欧盟无限制地接受难民,也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几乎是U型转折的政策让百万难民进入欧盟;在俄乌困境中,是德国联合法国斡旋了明斯克协议,是德国继续坚持北溪二号管道项目,也是德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投入了欧洲二战后最大的国家防卫资金充实防务。

事实是明显的:一方面,欧盟的整合和危机化解都离不开德国的参与。另一方面,德国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暧昧不清、犹豫不决的形象。对欧盟的其他国家而言,同样的悖论也存在:一方面,德国被视为一个欧盟的支配者,一个利用经济资源和欧盟机制扩充其影响力并将自身的经济模式强加在其他欧洲盟国之上的“霸主”;另一方面,德国被视为一个对欧盟事业三心二意,缺乏政治领导力和决断力的“弱势领导者”。
德国曾经数度追求对欧洲的领导权。对一个“欧洲中心”的想象,对一个“霸权中欧”的设想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引燃战火的动力之一。在欧盟东扩之后,德国似乎又一次成为一个潜在的“欧洲中心”,这次德国却回避这一地位所背负的责任和义务。是地缘政治和欧洲现实格局注定要将德国推到这样的位置上,还是一个“第四帝国”正在挣脱战争责任而寻求另类的复活,抑或是欧盟的政治结构导致了“执中之权”的自相矛盾?
从中心到边缘:无需执中的欧罗巴
欧洲曾经是作为边缘而非中心存在。在古罗马文明时期,真正的文明中心属于三洲交界之地的地中海。正因为此,欧洲的历史边界是一个和欧盟的身份认同相伴而行的争议话题:易北河、顿河和乌拉尔山,到底哪里才能算作是欧洲的东部尽头。这个问题似乎随着欧洲自身的兴衰而起伏:当东罗马帝国存在的时候,欧洲似乎只是亚平宁半岛西北的一隅;当奥斯曼帝国强盛时,维也纳似乎就是欧洲边界的最东尽头。而当欧洲随着经济增长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成为世界的中心时,被视为欧洲文明一部分的俄罗斯帝国也就被纳入欧洲的版图。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似乎只有当欧洲作为一个足够庞大的政治板块时,“执中之权”才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文明或政治板块的分界线就在欧洲的心脏地带,一个足够小的欧洲就要么落入到帝国的支配中,要么塌陷为一个局限的文明区域。如果没有足够庞大而多元的空间,中间位置将难以生存:加洛林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三个法兰克王国,然而,以亚琛、科隆等地为中心的中法兰克王国却没有能力延续自己的支配地位。两翼的实力太强又太过紧凑,中间反而成为被蚕食和瓜分的对象:中法兰克王国正是因此被驱逐到亚平宁半岛,成为一个南部的“边缘势力”。

相反,当欧洲的版图变得更加庞大时,“中间”便会成为一个认真值得考量的严肃问题。在19世纪的后半叶之前,欧洲确实变得更加强大,但是一个政治上的中心却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四分五裂而变得衰弱。哈布斯堡王朝在多瑙河流域建立了多民族的大君主国,却没有能力对中欧和西北欧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法国曾经将影响力深入莱茵,但却有着磨灭不掉的大西洋印记,而无法在中东欧产生作用。
然而,德国的统一第一次将所谓的“中心问题”带回到欧洲。长期以来,欧洲的格局是被两翼宰割的:无论是哈布斯堡和波旁家族的对垒,还是英俄的大博弈,概莫如是。对前者而言,神圣罗马帝国的中欧地带是两大家族斗争的战场。对后者而言,欧洲被分割为东西两个阵营:法国依附于英国,而普鲁士和奥地利则依附于俄国。断裂线从中欧延伸开来,也就是说,中欧反而成为两翼的从属。英国和俄国在远东、在中亚、在近东对抗,欧洲只是大博弈的战场之一而已。
然而,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数百年来欧洲的地缘政治。一方面是随着欧洲成为世界工业经济的中心,一方面是一个庞大的中欧被支配在同一个政权之中。相比英国和法国,这个统一的中心属于同一个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而且人口规模要更加庞大;相比俄国,虽然其人口规模有所不足,但更加发达的工业生产力和经济总量却呈现出碾压的态势。在德奥同盟确立之后,西巴尔干和中东欧的庞大土地也成为德国资本和政治影响力可以发挥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新生的德国拥有越发强大的对外投资能力,这导致巴尔干国家乃至奥斯曼帝国不可避免地成为愿意接纳德国投资的市场,也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德国在经济上的“实质势力范围”。欧洲头一次产生了一个强大的中心,而这个中心立刻展现出了对边缘国家的致命威胁。

欧洲近代的战争和悲剧归根结底是因为无法处理这个中心问题。法国和俄罗斯都不能接受在地理和势力范围上受到中心的支配,而长期以来通过离岸平衡维持欧洲大陆分裂的英国也不能容许一个具有潜在威胁的欧洲政治中心。俾斯麦通过将德国的野心局限在欧洲大陆,甚至是局限在中欧来规避其与大英帝国的摩擦。然而,随着这个强势的中心在政治和经济实力上的发展,“世界战略”取代了俾斯麦的“欧洲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由此展开:虽然世界战略和“阳光下的土地”引发了英德关系的恶化,但这场大战的根本逻辑却仍然是欧洲的支配地位:通过击垮俄国,德国可以全面控制欧洲的心脏地带,而法国则再也无法阻止这个“中心”成为欧洲的掌权者。支持自由主义政策的弗里德里希·瑙曼所提出的“中欧帝国”设想,便是这一轨道的最佳印证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伴随着同样的逻辑展开:在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崩溃后,中东欧形成了庞大的势力真空。被两个庞大帝国支配的东欧心脏地带现在被超过八个国家所继承。支配世界秩序的英法两国无法避免德国控制这个空虚的东欧地区,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线索之一:德国吞并奥地利、控制苏台德、侵入捷克、索取但泽都是在以中心地位向这个虚弱的心脏地带伸出触须,而位在边缘的前协约国们却无法阻止这一切。希特勒建立的仍然不是一个世界帝国的图景,而是一个欧洲帝国的轮廓,其核心则是通过支配欧洲的中心地带来控制整个欧洲。

两次世界大战都以欧洲的中心强化而爆发,其结束则意味着欧洲中心的毁灭。战争废墟摧毁了欧洲的经济,美苏冷战让欧洲成为战场的前沿。两次大战让欧洲的中心成为一个政治包袱,任何中心地位可能都会意味着战争和支配;冷战则让欧洲不再需要一个中心:西欧依附于美国,东欧又依附于苏联。即便是欧共体成立,仅包含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的这一政治实体也足够紧凑,而没有形成需要一个中心权力的松散大联盟。欧洲的“中心问题”由此被冻结了,在经济上互惠合作,在政治上寻求和解,而在安全上寻求美国的庇护,这成为了欧共体得以稳固存在的基础。在冷战结束之前,“执中之权”都再无意义。
失败的扩张:裂痕频出的欧罗巴
欧盟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开始扩张。在明克勒看来,正是欧盟的扩张开始重新将“中心问题”唤回到政治议程之中。法德意荷比卢六国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相近的文化、经济制度和货币政策,但新近加入欧盟的国家却未必如此。北欧国家拥有更加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更加节俭巩固的财政政策,而南欧国家则受困于更高的公共开支和债务问题。所谓“南北欧元”的裂痕问题就此在欧洲上演。以明克勒对欧洲媒体和舆论的观察而言,这种争执裂痕又与天主教和新教的历史分野结合在一起。
1991年冷战的结束也开始让美国逐渐降低了其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存在。两德统一之后,欧洲再次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心。这个中心没有办法限定其边界范围,因为一系列苏东国家在经济繁荣程度上与欧共体国家存在巨大的鸿沟,且政局不稳。欧盟如果希望自身有一个稳定的边界,而不是让邻国成为难民、毒品与混乱的发动机,就必须将其东部边界的邻国囊括到欧盟之中,通过欧盟如同“磁铁”一样的效应稳定其政治、繁荣其经济。这导致欧盟的边界扩张到东部。

这样的一个欧盟就不再只是核心欧洲的简单联盟。北欧有新教的传统,地中海世界则是天主教文化,而新囊括进欧盟版图的东欧国家有许多信奉东正教。这也不再是历史上基督欧洲的最小边界:在奥地利和捷克以东的东欧巴尔干世界,原属于欧洲和近东文明交界之处,而且它们还在苏联体制下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欧洲国家强调共同市场和稳健货币政策带来的繁荣,而对于后苏东国家而言,自由经济留下的却是休克疗法的伤痛。
于是欧洲分割为多个断裂线。西欧国家将市场化、法治议题视为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并指责东欧的新盟国们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曾经在铁幕下的东欧国家则唤起了对于“庞大帝国”控制“主权内政”的黑暗记忆,指责欧盟如同曾经的苏联一样践踏他们的主权,试图将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强加在弱小的盟国身上。北欧国家指责南欧国家不能够量入为出,而南欧国家则指责北欧国家将自身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强加于人,肆意干涉自身的经济主权。法国和德国认为新生的俄罗斯是一个友好的战略伙伴,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还可以提供廉价的能源,而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则确信巨人邻国仍然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安全威胁,法德绑架欧盟与俄罗斯的合作以牺牲东方伙伴的国家安全顾虑为代价。

与许多欧盟研究者,如蒂莫西·加顿·艾什这样的欧洲主义者不同,明克勒不认为欧共体和欧盟的诞生是基于欧洲和解和联邦主义的理想。欧共体最初只是一个基于经济务实角度的设计,以期通过经济合作化解欧洲邻国间的潜在分歧。这就意味着,欧洲项目原先只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合作,其设计者并未将其作为潜在的政治实体加以规划。在欧共体的逐步发展中,欧洲联盟才作为一个甚至有可能成为超主权实体的存在进入政治家和理论家的视野中。
超主权实体和政治联盟并不以相同的方式运作,困扰欧洲政坛数十年的“民主赤字”问题正源于此。通过叠床架屋地增加合作范围,欧共体和随后的欧盟囊括的政策领域日渐增加,并进而从单纯的互惠贸易上升到政策管制和转移支付。无论是共同农业政策(CAP)给法国的超庞大补贴,还是欧洲央行的建立,都意味着欧洲的政策开始让一部分国家受益,而令另一部分国家受损。对主权国家而言,向同胞提供的转移支付是同为一个民族的应尽之义。不会有太多法国人抗议给予他们南部农村同胞的农业补贴,也不会有太多前西德公民反对在两德统一的过程中超额补贴其前东德的同胞。

然而,民族国家的联盟就大不相同。在一个领域的损失,必须要通过另一个领域的收益加以弥补。这一逻辑事实上是双向的:对于付出成本的一国而言,他们的政治家必须以超额收益来说服选民,以使得每一次让步事实上都增加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以利而合者,利尽而散。维持欧盟这一共同体本身的存在并不被选民视为一种身份利益,这预示了一个条件:当支持欧洲的成本高于潜在收益时,放弃欧洲项目才成为理性选择。欧盟支柱国家的国民因此将欧盟的存废变成一个数字游戏,并时刻考虑着何时应当放弃这个负担。另一方面,受惠国也并不会因此感谢联盟的维系者。因为潜在的逻辑表明施惠国一定在其他领域能够寻求更大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是从受惠国身上索取的。因此,如果法国愿意利用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来提高欧盟整体在联合国的话语权,那一定是因为法国需要借助欧盟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来谋求其国家战略;如果德国愿意接受额外的财政支出来救济困于债务危机的南欧盟国,也一定是因为通过欧元机制,德国可以系统性地获益。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需要支出的偿付难道不是已经在德国那几乎称得上惊世骇俗的经常项目盈余中得到体现了吗?
于是,没有任何一方从欧盟项目中感受到荣辱与共。只要欧盟还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而无法成为超主权实体,民主赤字问题就仍会扩大。正如明克勒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政治家们越是在布鲁塞尔做出让步,推进欧盟的整合,他们在国内就越是可能强调这一行动带来的利益,并因此在其他国家激起波澜。2005年的欧盟宪法公投在荷兰和法国的意外失败中断了欧盟超主权化的道路,而与欧盟宪法差异不大的《里斯本条约》却再不敢诉诸全民公决。将欧盟作为超民族国家项目寻求公众支持的尝试从这一刻起就彻底失败了。也许一个“小欧洲”,一个没有经历过数轮扩张的欧共体能够建立起成为超主权国家的基础,但现在的欧盟似乎已失去了向这一方向急进的可能。于是,在一个撕裂的欧洲中,“执中之权”似乎又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
泥潭中的联盟:执中之权与欧罗巴
执中之权对欧洲而言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其部分原因在于德国的历史责任。对于记忆犹在眼前的一代欧洲人而言,德国的中心地位是同战争和压迫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德国的邻国都可以让历史责任成为德国施展政治影响力的包袱。即便对于德国人而言,承担欧洲政治的中心地位也可能成为额外的负担和压力。因而,即便是作为欧盟的坚定支持者,德国至少仍在成为欧洲项目的中心力量上不情不愿。
在欧洲的裂痕没有凸显时,德国实则已然通过其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影响力以“幕后操纵”的方式影响欧洲的政治。在经济议题上,德国常常利用英国和北欧国家的财政节俭意愿来牵制南欧国家的举债行为。而在政治和安全议题上,德国又常常借助所谓的“法德轴心”地位来发挥影响。在针对欧盟政策的英法对立中,德国的帮助将使得其中一方占据上风,因此无论是欧债危机、俄乌冲突还是英国脱欧事项,德国都在不情不愿中被事实上推上了主要决策者的位置。

英国脱离欧盟进一步将德国放在了焦点之下。欧洲曾经的两个中心——英国和法国,现在仅余其一。法国是欧盟仅剩的联合国常务理事国,使得除了德国享有的庞大经济资源和市场规模,没有第二个欧盟国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和法国类似的作用。法国的公共开支比例和债务结构都更接近南欧而非北欧国家,在亲近市场的埃马努埃尔·马克龙总统当选之前,法国对国家、市场和自由贸易持有与德国完全不同的态度。一部分西欧政治家和欧盟主义者试图将亲欧的马克龙视为欧盟的潜在领导者,但与普遍支持欧盟的德国不同,马克龙在国内面对的政治环境要更加险恶:他面对一个疑欧的极左翼联盟和一个虽在修辞上变得缓和却仍然宣称要选择性执行“欧盟条约”的极右翼政党,而亲欧的中间派联盟只享有不足半数的支持率,仅仅是依靠法国特殊的选举制度才得以维系其地位。法国身处西欧使得东欧国家相对更不信任他们野心勃勃的总统,而所谓的“节俭国家”(荷兰、丹麦、瑞典、奥地利)也有理由怀疑法国正试图将欧洲的共同赤字强加于他们遵守纪律的财政预算中。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试图领导一个北海-波罗的海的自由贸易联盟,维谢格拉德集团早已成为中东欧国家的俱乐部,而意大利的马里奥·德拉吉也试图重振这个欧共体创始大国的政治影响力。重拾“德法轴心”反而可能激起欧盟其他小国的警惕情绪,即便德国没有主观意愿,在脱欧完成之后,他已经事实上被推向了掌握“执中之权”的宝座。
无论德国政坛和民众的政治意愿是否强烈,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已经成为欧盟中不可或缺的调停者。以几乎撕裂欧盟的波匈法制问题危机为例:西欧和北欧国家认为匈牙利的青民盟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政权事实上破坏了欧盟的“民主法制”原则,利用掌握政权的便利打击反对党、阻挠司法公正,并指责这些民粹主义的疑欧党派一面获得欧盟的拨款来巩固其执政地位,一面对欧盟一体化的政策推三阻四。而匈牙利和波兰的右翼民粹主义执政党将欧盟的干涉和历史上帝国主义强权对东欧地区的干涉联系起来,以煽动疑欧的民粹主义倾向。矛盾时常变得激烈,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曾因价值观议题宣称匈牙利已无法属于欧盟,但青民盟却能在国内选举中击败所有反对派的联盟,赢得前所未有的胜利。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执政党青民盟属于欧洲议会的“欧洲人民党”(EPP)党团,而默克尔的基民盟同样也是这一党团的成员,并在党团中事实上起到领导地位。这一形象自然可以成为对抗双方之间的润滑剂。波兰总统杜达同西欧国家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但也更愿意听从默克尔的居中调停。这种折中地位固然是因为默克尔的执政以中道温和为主,但也与德国在地缘、意识形态、经济和外交上所处的中心地位紧密相关。

从结构、意识形态和现实优势的角度,如果欧盟希望存续,德国就不仅必须在实质上,而且必须积极、主动、有意识地承担执中之权。在欧盟的结构上,德国贡献了最大的财政资源,又拥有最多的人口,因此必然对欧盟的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德国位在中欧,既不会被完全置于西欧阵营,又同东欧保持着距离,既在财政和经济实力上与北欧有相近之处,又愿意对南欧国家做出妥协和接济。在欧盟的意识形态中,德国既属于相对温和的阵营,常常以一个中左翼和中右翼的大联盟执政,又坚持欧盟所固有的价值观和立场,可以在疑欧民粹主义和亲欧中左翼进步势力之间做出调和。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所有的大型联盟都同样要面对一个“中心”危机,那就是担心一个过于强势的中心会威胁边缘的地位,从而将一个联邦式的联盟体转化为中心霸权支配下的政治实体。然而,德国的历史包袱正好可以抵消这种担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事实上对所有的欧洲邻国犯下战争罪行,这使得德国在欧洲经济影响力的扩张都被称作所谓“第四帝国”加以批驳。即便德国能够通过其有利地位掌握“执中之权”,这一权力也必然是受到限制的。“弱势的掌权者”是明克勒给德国地位提供的恰当定义。德国不得不一方面克服其选民不愿意承担欧洲政治责任的惰性,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作为一个拥有足够砝码的调停者来弥合欧盟盟国之间的矛盾。欧盟仍陷在泥潭之中,而在这样的沼泽地里踽踽前行,却唯有依靠这样一种弱势的“执中之权”。
欧洲项目是否仍然是一个潜在的超主权实验?在民粹主义和极化政治席卷欧洲各国的当下,超越民族主义的理念精神是否仍能在欧洲维系?不同的政治理论家给出的答案大相径庭。对于那些希望欧洲能够代表某种超越性理念的人而言,仅仅接受一个实用主义妥协而产生的欧盟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主权仍受到许多人的珍视,将一切都让渡给一个看起来缺乏民主决策机制的欧洲,又像是理想主义者盲目自大、好高骛远的策略。

2018年,雄心勃勃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展开了对欧盟愿景的长篇讲话。无独有偶,就在其讲话前两年,大批欧洲知识分子联合发布了一个保守派欧洲愿景的宣言《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的欧洲》。一者是渴望欧洲整合的自由联邦主义者,一者是以主权和基督教文化为理由捍卫民族主义的中东欧民粹主义者,二者既有断然相悖的理念图景,也享有微妙的共同之处:他们都相信欧洲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间的简单联盟,而意味着某种价值愿景,某种共同观念和身份认同。从这个角度而言,明克勒在《执中之权》中的主张显得过于悲观了:即便是在欧盟宪法失败十余年后,一颗欧洲认同的心脏仍然在欧盟跳动不息。
但大跨步的理想从来容易导致分裂和龃龉。马克龙野心勃勃的计划最终需要通过德国温和的刹车加以实现,东欧国家针对欧盟的激烈对立最终也需要德国策略性地调停加以限制。明克勒至少为欧盟的稳定存续提供了一种策略——欧盟不能仅仅依靠这种策略性的“执中之权”,却断然不能缺少这一策略性的“执中之权”。
作者/王子琛
编辑/袁春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