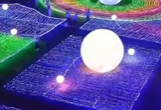【编者按】
此时此刻,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年味儿正浓。
在外游子终于回到家乡,我们也不例外。返乡的行囊中有年货、有思念,还有一双重新认识故乡的眼睛。回到出发的地方,乡音激活记忆,感知时间的流动与地方风貌变迁,这里蕴含着个人的独家记忆,也呈现着中国大地的时光侧影。
为此,新京报评论部联合新京智库,推出“新春调研行”专栏,记录并评述新闻人眼中的新时代乡村实景,品尝各地独特家乡味道,与读者共同感受时代脉搏。

▲农村大集上还有这种老式崩爆米花机器。新京报记者刘昀昀 摄
“嘣!”
集市北头传来一声平地爆炸声,白色烟雾腾起,泥土地上架着一个黑咕隆咚的机器,旁边站着三三两两的人。很快一阵焦甜的香气传来——爆米花熟了,旁边一群小孩围了上来。
我着实没想到,过年回家,居然还能在人山人海的大集上看到这种老式爆米花机。
当年,“80后”“90后”在大街小巷,围着崩爆米花的老头看。那时候街头一声巨响,就有小孩上前捧走新鲜出炉的爆米花,何其满足,又何其风光。那份香甜,不止温暖了一代人。
如今,笨重的爆米花机已经不多见,但“10后”“20后”的小孩们,仍然难逃其诱惑。
热闹、美味,那一声爆响,更是仪式感十足,也是崩爆米花最让人欲罢不能之处。当然,这也是农村大集最吸引游子之处。

▲大集上卖春节对联的小摊,年味浓郁。新京报记者刘昀昀 摄
大集是鲜活的乡村侧影
对于村庄而言,大集是一段逃不掉的集体记忆,更是一场热闹的乡土生活。
我们村在鲁东沿海的一个县城深处,但离海边仍有近一小时车程,因此无法靠海吃海,种地收粮乃最基础的盈利方式。
附近十里八乡五个村组成一个“集市圈”,每村一日,五天一个循环。我的故乡——孟戈庄被分配在第五天。被安排在最后一天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孟戈庄大集开始得最晚。对于地道的农民来说,大集是最主要的购物渠道,而赶集同时也是一次社交活动。
那时,我已读了几年小学,忽一日,母亲告知,我们村要有集了。就像一个从小偏爱逛商场的购物狂,忽而听闻家门口要开一个综合商场,幼年之时,我也为大集将开兴奋得难以自抑。
开集之日,村里连唱了两天大戏,戏台上红袖翩飞、柳腔婉转,东头唱戏西头集,颇为热闹。
有了集,我们这个村庄好似更完整了些。老人说,我们这样一个大村,早就该有个集了。可见,集市对于农村来说,实在重要。
大集,是农村生活一个最鲜活的侧影。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谁也离不开它。在某些时候,赶集也被看作农村独有的特征。正如太阳东升西落般,大集早出午收。赶集是一种消费路径,也标记了农村的生活。
对于尚未成家的孩子来说,赶集有时候并不是为了购买那些生活必需品,这也不是他们该操心的事情,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与童年记忆。
两年前的冬天,有一次与母亲视频聊天时,她说梦见与我一同去李庄赶集。随后几日,我思来念去,很是想家,便告了假,不声不吭地乘坐高铁回了家。
到家时正巧傍晚,父亲开着大门在厨房炒菜,我悄悄进了家门便大喊一声,父亲与母亲的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日一早,母亲就载着我去李庄赶集,买了橘子与鲤鱼。那是鲜活的日子,从幼年到中年,大集标记着我们一家人一段又一段的生活记忆。

▲农村大集仍是人们年前置办年货的地方。新京报记者刘昀昀 摄
人回来了生意也就好了
和小时候相比,如今集市的无可替代性自然是减弱了许多。
以前每次长高,家家户户的小孩都要去大集上选购时兴的衣帽,如今邻居十几岁的妹妹早已抛弃了集上的衣服摊。她们觉得,电商发达,物流触及农村每户人家,要进城也不过是一脚油门的事情。
故而,村里大集难免有些落寞,正如同城市化之下的村落。但在春节的语境中,赶集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家家户户都要去一趟,似乎这才有点置办年货的样子。
春节前两日,我们驱车前往几公里外的刘庄大集,尚未抵达就已听到人声鼎沸,于是只能将车停在了几百米开外。
母亲感慨,“我们小时候赶集都是步行,那时候集上哪有这么多人,东西也少得可怜。你小时候我们骑自行车,偶尔骑摩托车去赶集,现在家家开着车,都没地儿停。”
这倒是实话,从停出老远的车,就能看到大家生活的改善,以及赶集的热情。但因为疫情的缘故,这种“盛况”已经好久不见了。集市上一个卖糖果的大哥说,他刚“复工”没多久。
去年开春以来,我们这个小县城就因疫情停摆了许多次,农村大集自然也“关门闭市”,糖果大哥在家赋闲了许久。
糖果大哥说,前阵子防疫政策调整后,集市上的人也只有三三两两。直到临近春节,人群才又回来了。人回来了,生意就好了。
糖果大哥一边招呼着我们,一边热情地给围在糖果摊前迟迟不肯散去的孩子们介绍五颜六色的糖果。一切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大集上卖糖葫芦的小摊。新京报记者刘昀昀 摄
集市北街扬起的爆米花烟雾,东头飘起的章鱼气球,路口有滋滋的油炸声和糖果香,往西看去,则是林林总总的服装摊,款式还有些时兴。热闹的大集,终究是回来了。
农村人的日子,总是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但也不是一成不变,如同大集也在推陈出新。在农村,一入腊月,人们就在为春节做打算了。故而,过年总是漫长的。今年,又尤为不同,疫情成了最大的变量。
腊月前几日,父亲和母亲感染了新冠,居家了一周有余。母亲说,那段时间村里的集已经恢复了,只是人人戴着口罩,来去匆匆。
疫情给持续几十年的农村大集一个不小的打击。但一切都会过去,农村的烟火气也在回归着。
然而,我总觉得,用烟火气回归来形容农村,不甚准确。烟火气,对于农村来说其实是一个有些陌生,甚至有些高级的词汇。
我的父亲母亲,和那些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街坊邻居们一样,其实并没有担心过集市的变化。在疫情消散的日子里重新回到集上,就像蜗居了一冬的人该出门了,在他们眼里,这不过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这最为朴素踏实的生活,就是烟火气本身。就像相信大集再也不会因为疫情而关闭一样,他们也始终相信,这不紧不慢的日子里那份温暖与安心,就是他们的盼头。
撰稿/新京报评论员 刘昀昀
编辑/徐秋颖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