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至2月20日,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时间的眼睛”在北京观唐艺术区美术馆举办。举办年度阅读盛典,记录时间在出版行业留下的痕迹,是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例行传统,本届已经是第19年。
今年阅读盛典的主题为“时间的眼睛”,为了给读者朋友们带来更具体的解读,我们按照对过去一年出版文化的观察,分成了四大书单——凝视与想象,视野与方法,记忆与留白,对话与回响。搭配这四个主题书单,我们相应举办了四场深度阅读活动。
 2月19日,2022新京报阅读盛典第三场活动“生命的厚度:传记何以可能”,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左一),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刘文飞(左二),作家赵松(右一)在现场。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2月19日,2022新京报阅读盛典第三场活动“生命的厚度:传记何以可能”,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左一),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刘文飞(左二),作家赵松(右一)在现场。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本文为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时间的眼睛”第三场对谈活动的回顾报道,第四场活动的回顾报道也即将刊发,敬请期待!
本场嘉宾|刘文飞、汪民安、赵松、王璞
问答题纲及主持|张进
报道整理|宫子
本场活动嘉宾


艺术能否被生活经验所解释?
这些年传记作品出版得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很多读者也格外喜欢读传记。几位老师都读过,乃至撰写或翻译过传记。从个人阅读体验出发,各位老师认为一部好的传记是怎样的?
汪民安:既然是传记,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尽可能接近真实。很多传记是虚构的。许多年前有一本说是尼采的妹妹写的书,写的是尼采,这本书其实是骗子写的。这本书二十年前在中国卖得很好,但完全是虚构的。所以,既然是传记,我们不能说绝对真实或者完全真实,但是要尽可能真实,不能虚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好看。有可能全部是真实的,写得泥沙俱下、事无巨细,但你看不下去。传记要让我读下去,一晚上读到天亮,这是好的。
刘文飞:一个是要实在,跟民安兄说的真实是一样的。我非常反感那些戏说的东西,比如找一个名人,找一些花边(的那类传记),但这些东西在中国或美国反而是最畅销的。
第二,一本好的传记必须要好读。它要讲故事,讲有趣的故事,或者把无趣的故事讲成有趣的。
第三,一本好的传记,我觉得读完要受用,或者被这个人的成功感动,或者被他经受的苦难感动。另外,有时感动我的不一定是传主,大家读传记的时候最容易忽视作者,我们读一首诗的时候会知道这是李白的诗,但是读传记的时候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作者身上,我说的触动,更多的是要先了解传记的作者,一本传记在多大程度上写的是传主,多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己的阐释,其实很难说。
关于传记,著名诗人布罗茨基的观点非常值得讨论,他认为,"在导致公众精神贫乏的诸多原因中,一种窥淫癖似的传记题材是位居榜首的",并说"传记的基础就是艺术能为生活所解释这一激动人心的假设"。布罗茨基显然是反对这一假设的。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刘文飞:其实布罗茨基说的这两类都是他不喜欢的传记,一个就是窥淫癖式的,如果你是一个威严的国王,我就写你和女性的私通,如果你是非常严肃的作家,我就写你通信中有下流的东西,形成一种反差。在西方有一本普希金的“色情日记”,我们国家还翻译过,但这本书是完全伪造的。这种就是哗众取宠,为了获取商业价值。
布罗茨基这句话中,第二个反对的点很有意思,布罗茨基的反对是把生活等于艺术,艺术等于生活,这和他反对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命题有关——即艺术是生活的反应——他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后来我们发现布罗茨基写了很多散文,都会把自己带进去。他觉得最好的传记一定是自己写出来的。他会用诗的方式写回忆录,让你通过陌生化的语言去理解我对生命的体验,至于我在哪出生,做过什么事情,跟谁相爱过,这个不重要。他跟他的初恋生活在一起,还生了一个孩子,但是你会发现他的传记里一个字没提。别人会认为这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人,而且可以想像没有这个女性布罗茨基未必会写诗,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写。相反,他会写为什么辍学,他说有一天,上七年级的时候,他突然从课堂上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没有动机。他说,出来之后自己走在涅瓦河旁边,河结冰了,他看到结冰的河面反射着夕阳,觉得这就是无穷。相比恋爱,这些东西不重要吗?在某一刹那,你的情感如果串联起来,这可能是你最真实的意识,比你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恋爱还重要,每个人都有生死,但是不一定有这种感受的瞬间。
汪民安:我当然理解布罗茨基的观点,就是不要把生活当做创作的根本性的解释性的起源。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生活和写作的关系非常复杂,生活不是写作的直接的起源,但如果没有生活(也很难写作),两者有一种细微的、有时甚至作家都意识不到的关系。一个作家不可能脱离这个时代。
而且还有一点,一个人的生活哪一部分重要,哪一部分不重要,很难说,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瞬间都很重要,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牵涉到我们的精神世界,哪怕是非常无聊的(经历),失眠,跟一个非常乏味的人待了一个小时,这都是生活,和创作可能都有关联。对我来说,很难说选择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传记中重要的部分,或者剔除掉一部分,我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反而更喜欢看八卦的东西,我看传记,总是能非常敏锐、迅速地找到他们的爱情,我总是喜欢看这些,而且是我记忆最深的东西,我不觉得这个和他们的创作没有关系,这些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比如我印象很深的德里达,他是2004年去世的,不久之前他的传记就出版了,当时我对他的私人生活特别感兴趣,那个书里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他跟他的一个情人的一段往事,我当时看得惊心动魄,他的情人后来跟他还有一个私生子。我可能比较低俗,比较喜欢看这些八卦,福柯这方面的东西就更多了。我觉得有意思,而且这个对他们的哲学思想有一些重要的影响。当然,有一些作家或者传主排斥别人写这些东西,因为活着的时候看到这些对他来说是丑闻。但是死后,生前的丑闻很容易转化成美谈,甚至有时候转化成名人的一种特权,他们享有的对道德、对公理的破坏的特权。
赵松:布罗茨基的尖锐是有道理的,他知道在公众话语的语境里,长期包含着两种冲动,一种是膜拜伟大的、卓越的人物。另外一种是扒光他们的衣服。这两种冲动始终存在,而且可以毫不违和地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这非常可怕,既可以把完全不了解的杰出的人捧上天,也可以扒光衣服扔到泥坑里。
当代就是热搜,你没有听说过捧人可以捧到热搜头条的,这是布罗茨基多年前指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把人的日常一面和杰出一面混为一谈,我可以用这面毁掉你的另一面,我可以用你私德不佳或者某一方面的个人问题毁掉你的全部成绩,这是一种带有毁灭性的价值观,是人类历史上长期都有的东西。
我们回到布罗茨基的语境下谈论文学和艺术。这是极其危险的,文学艺术从来不能用来解读现实,现实也不能用来解读文学和艺术,文学作为艺术是一种重构的状态,是一种创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当然包括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但是不能建立在那样一种简单化的层次上,那样只能毁掉文学和艺术。
王璞:布罗茨基经常会有来势汹汹、非常强势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往往是直击问题、偏激中包含着深刻的。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种暴论,又是天才式的暴论。
要理解他的判断,还是应该考虑他的针对性。我觉得布罗茨基气势汹汹否定这种假定,即一切艺术作品、一切文学作品都可以为其创作者的生平所解释,他的针对性很明确。他针对的是两样在现代人文素养中非常深厚的东西,但确实是值得质疑的,第一就是我称之为作者中心的线索,从浪漫主义开始,从现代独创性个人的形象开始,又到19世纪的历史主义得到加强,最后产生一种主体的天才人物的神话形象,这是一种天才想象,文化英雄的崇拜,是一种伟人模式。我们传统传记中经常有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早已深入到一般的文学阅读、文学欣赏的习惯里,像我们今天如果让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做一个文学作品的小发言,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作家生平,好像介绍作家生平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作品。这就是布罗茨基所说的,我们认为作品可以通过创作者的生活得到理解,这本身是需要质疑的。
第二个线索,我称之为作家的代表性假设,作家的历史精神化身假设。我们认为通过对一个作家生平的了解,可以理解他的作品,可以获得一个时代的代表,一个时代精神的化身,这是历史主义的传统,也非常有说服力。我们今天还是会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看到一个作家,不管是古代的作家,屈原、杜甫,近现代的莎士比亚,或者托尔斯泰、鲁迅,我们都会把他们当做一个时代、一种文学的代表,比如在一个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的大框架里,只有理解鲁迅才能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模式本身是可以质疑的。我们怎么样把一个作家放在那个位置,就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这本身是可以质疑的,而且确实是我们在传记写作和传记阅读中需要反思的。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俄罗斯犹太裔美国人,诗人、散文家,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如何看待传记中
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与布罗茨基不同,另一位大诗人惠特曼则强调,若要评估他的诗,"首先必须深刻地评估当时世界的时代特性和各种现象,以及它们的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传记作者,比如入选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极其广泛地研究传主当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而且认为可以通过这些研究,获得对作品更精确、深刻的理解。关于这种传记写作思路,各位怎么看?
王璞:这个问题正好和前面所说的衔接上。布罗茨基有一个强势的质疑,但并不等于我们就因此要彻底放弃这样的传记模式,要彻底把历史主义扔到窗外,而是说我们是否有一种新的历史主义的可能,新的传记写作的可能。
我翻译的《本雅明传》,弗兰克的多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在重新思考传记的可能性,在实践一种传记写作的新可能性。
当然,惠特曼怎样看待他自己,怎样看待诗人和时代的关系,这和布罗茨基是完全不同的。惠特曼恰恰就处在一个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伟大交点上,又处在美国“和平崛起”的时期,处在一个诗歌声音的爆发点上,他确实是美国某种历史精神的喷泉。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一方面传记是必要的,我们要把一个作家、一个文化英雄、一个重要的思想人物愈发充分地还原到历史之中,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要去神化一个作家的中心位置,不要把历史变成某种历史精神的代表性投射到“一个”作家上面。刚才提到的这些传记,一方面在践行高度的历史还原,但另外一方面,这些传记作者不愿意把历史和作家的对应关系本质化,并不是说惠特曼是美国的一切,也并不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俄罗斯灵魂的全部矛盾,也不是说本雅明就是欧洲现代性的最后的标杆。我们还是要在一个非常丰富的、不断敞开的历史现场和历史细节之中来理解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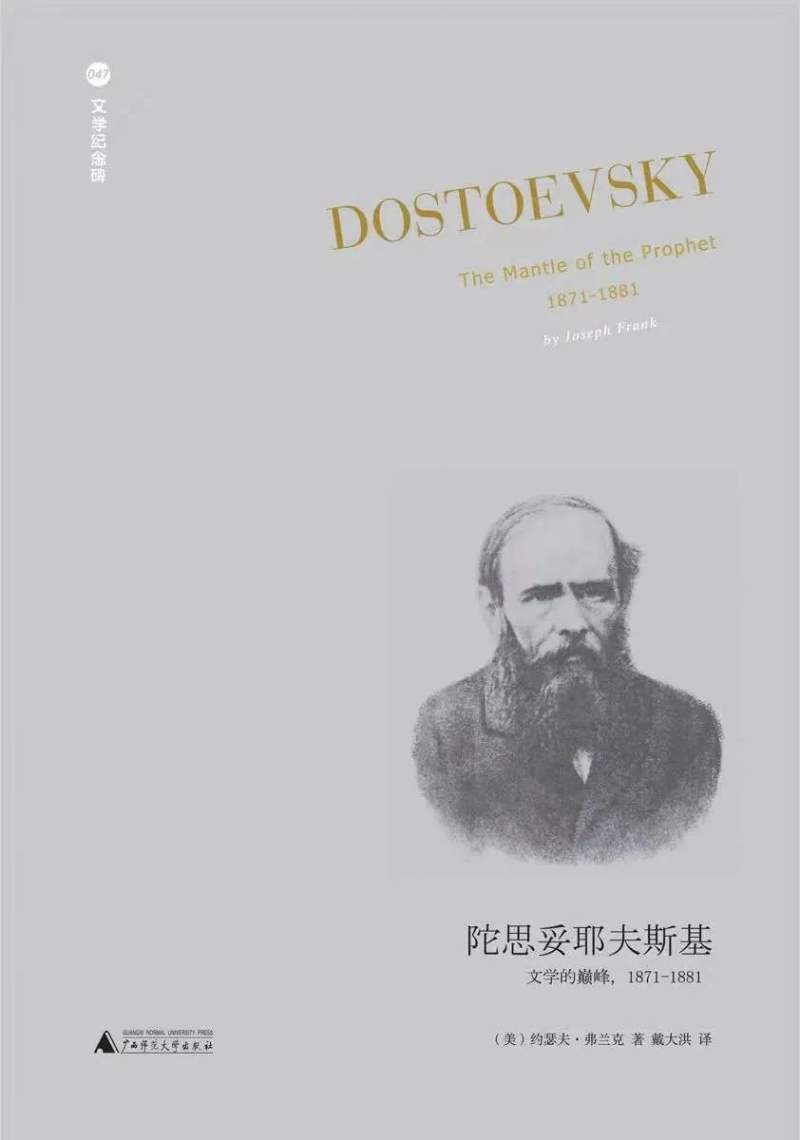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作者:[美]约瑟夫·弗兰克,译者:戴大洪,版本: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3月
刘文飞:弗兰克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们认为的三个主要的传记方式都照顾到了。写生活的细节;又写作品,几乎每个大的章节都是评一个作品;以及19世纪的俄罗斯思想史,思想史就是文化语境。生活、作品、社会语境,三个方面都照顾到了。
在这部传记中可以看到很多生活细节。这部作品好像是百科全书式的传记,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如果我们真说有什么问题,这个优点反而是它的缺点,它太面面俱到了。事无巨细是不是有必要?他的作品越细对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帮助越大。
汪民安:我觉得惠特曼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思想家,跟他的时代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是很值得探究的。
有一种是旁观者,他从时代里摆脱出来,从来不真正植根在人群当中,总是冷眼旁观打量这个时代,本雅明就从来没有进入知识界的主流,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旁观他的时代的,他置身于这个时代,但是又不参与这个时代。塞林格、布朗肖都是这种人。
另有一种人是对抗时代的,跟时代是天然的敌人,像尼采,他跟所有人格格不入,永远都是批评,对这个时代的一切都进行怀疑、质疑。鲁迅也是这种人。
还有一种是和时代共舞,跟这个时代玩游戏,时代转向他也转向,最有意思的是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他跟消费社会玩游戏,消费社会需要什么东西、观众需要什么东西,我就去满足你,我做消费时代的弄潮儿,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还有一种,他们是引导时代往前走的,非常有预见性,像马一样拖着时代往前走,比如梁启超。当然,也有一种是把时代往后拉的,比如钱穆,他们更眷恋以前的社会,新的时代他不适应。这样的分类相对比较粗糙,而且这些人和时代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
文人、知识分子、哲学家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就在于时代在他身上打下了非常深的烙印。我们之所以是普通人,就是因为我们只是时代大潮卷起来的细沙,伟大的文人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有力量跟这个时代发生尖锐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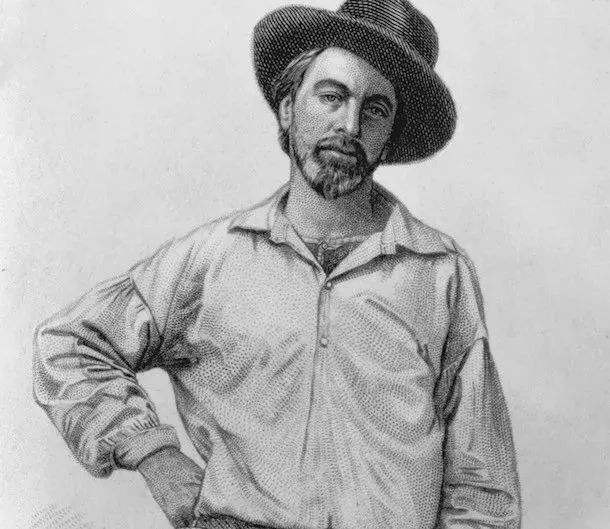
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其《草叶集》是19世纪中期美国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标志着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峰。
很多传记
是一个大作家写另一个大作家
入选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的《本雅明传》里说,本雅明的两大主题:经验和记忆。这也让人想到前些年很受欢迎的一部作品,《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主题也可以说是经验和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传记的主题就是经验和记忆。从这个层面,各位老师如何看待传记写作?
刘文飞:把经验和记忆看成传记主要的内容,这肯定是合理的。不过我们要注意区分经验和记忆本身的不同,比如说在一部传记中,真的经验完全有可能变成伪记忆,反过来可能也一样,但是这个“伪”到底是记错了还是艺术的显现,比如通过另外一个人构思“我”的东西,它就会变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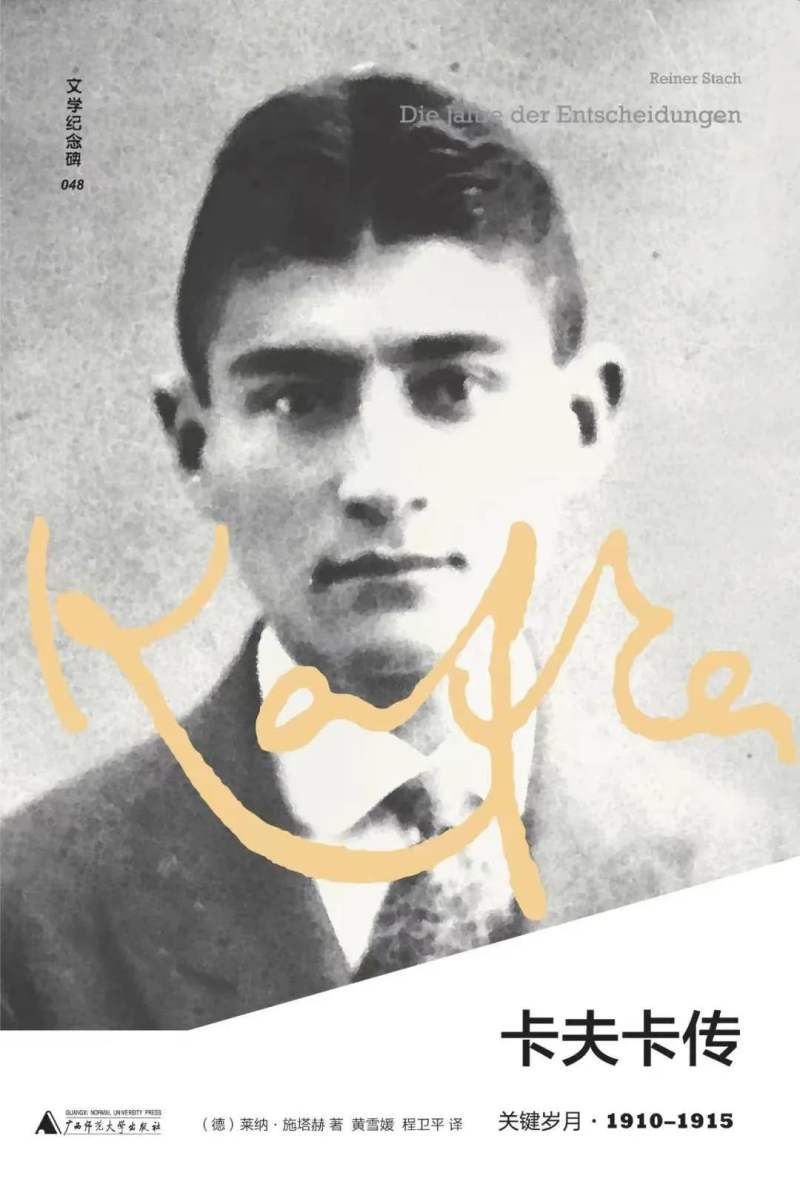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作者:[德]莱纳·施塔赫,译者:黄雪媛 程卫平,版本: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阅读传记时,有一个我们都期待的效果,就是尽可能接近传主的“真实”,但我们也知道,这种真实性是相对的,就像《卡夫卡传》的作者莱纳·施塔赫本人,就对此有所警醒。应如何看待用传记抵达传主的"真实"这一问题?
汪民安:每本传记都是选择的结果,哪怕把所有的材料都搜集到,在编制材料的时候,每个写作者(写出的)也不一样。写传记,除了材料,更重要的是写作者。你想给卡夫卡写一个传记,给福柯写一个传记,一个单纯的记者肯定是不行的。一个真正的、好的传记作家,本身应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知识分子,写传记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很好的传记都是伟大的作家写另外一个大作家、艺术家,例如罗曼·罗兰给贝多芬写传记。两者之间要有一个灵魂的对等。你是一个平庸的人,你能理解卡夫卡吗?首先心智和精神上就无法理解,再多的资料也只是资料的堆积,很难保证灵魂写作。写作者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写传记最核心的。
传记的必要性和意义
传记写作的必要性在哪里?现在的图书种类非常多,读者的选择也非常多,阅读传记可以获得哪些独特的意义?
刘文飞:传记这个题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想还是人类的模仿性,英雄崇拜。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比较关注比他更强更好更成功的人,这是模仿性。
大家还要注意一个细节。从文艺学角度谈,传记可能是人类史上仅次于诗歌的最古老的体裁,《论语》某种意义上就是传记,更不用说《史记》了。还有国外的圣徒传、使徒传。而且传记作为一种体裁,从历史上看,变化非常小,中外作家的写法也几乎大同小异。我们可以从它体裁的恒久性反推它存在的合理性。
汪民安:传记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类的文明史和发展史就是一些人物构成的,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历史,我们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怎么走到今天的——肯定是和这些大人物相关,不能说他们是决定性的,但他们一定是在历史发展方向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观念怎么形成的,我们今天怎么形成的,当然要了解他们是怎么思考的,这是从宏观的角度讲。
第二,更具体一点的,我希望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人物,他们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你读传记的时候,这些艺术家或者文人在非常关键时刻的选择,他们身上的勇气或者他们身上非常特殊的决断,他们对一些事情非常与众不同的看法,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有用的,而且某种程度上真的可以给我们勇气,让我们也充满勇气,这个非常重要。
第三,我们怎么过这一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大文人,他们的人生本身就是艺术品。你看那些跌宕起伏的传记,他们的一生你看下来,会让我们想到,每个人都可能创造出自己的生活,(想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外,在我们既定的、规范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体制所规训的生活和模式之外,还有特定的生存方式或者生存美学,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就喜欢看一个人怎么过完他的一生,可以给我一些启发,一些勇气,甚至让我在很沮丧、很失落的时候想到有一些人是这样做的。人类还是有非常多的可能性的。
王璞:如果要选择传记,读它的意义,还是要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个体在历史时间中的存在,这是永远和我们有共鸣的。我们今天讨论的,都是现代的思想人物,大作家,现代文学中的核心人物,我觉得我们也是有一个回眸,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去个体化的时代,但我们是在回眸在现代性的历程和浩劫中一些可以被我们当做路标,可以被我们当做星座的个体生命,而我们不是把他们当做英雄,而是看到他们在历史时间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洛尔:
在人世间无目的地漂泊
除了传记作品,我们2022年还选择了几本小说,现在聊一下《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和《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的作者拉巴图特,在小说中采用融合虚构与纪实的写法,写了很多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故事。这种虚构+纪实的方式,可以带来对生命之厚度的拓展和深入吗?
赵松:近十几年,欧洲和法国有一些作家都用这种写法写小说,用真人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把小说的虚构性和现实中的具体题材的真实性的界限打破,重新组成一个全新的东西,它仍然是小说,不能说是报告文学,也不能说是纪实性的东西。这样写的小说家通常认为,虚构和纪实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完全取决于作者以什么方式组织和重塑这些材料。
还有一点,我们读这些小说的过程中,即使知道是一个真人,也觉得像纪实性的深度报道,但仍然会被它内在的强大力量所触动,这种力量无法形容,也是小说所拥有的东西。拉巴图特这本小说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震撼力,固然来源于书中人物本身拥有的神秘能量,也确实只有小说这个方式才能把这些能量充分释放。

《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作者:[哥伦比亚]阿尔瓦罗·穆蒂斯,译者:轩乐,版本:大方·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8月
《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的主人公马克洛尔一直在无规则的世界中无目的地漂泊,他的这种存在方式,能够带给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怎样的反思或比照?
赵松:随着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尤其是21世纪的全球化,大家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越来越相似,越来越高度模式化,人也被固化。马克洛尔恰恰带有反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特征。所谓的反现代生活就是,他不追求成功,他不追求财富,对他来讲,个人的自由自在、自处是最大的价值,他为此可以牺牲那些所谓的名声地位,所谓的成功,所谓的金钱财富,他也愿意接受一次次的由此带来的所谓的失败。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于现当代人的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说(马克洛尔的人生)有启发性的话,在于他揭示了一个很真实的存在状态,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你追逐的一切最终都会化为乌有,都会归零,没有什么是在生命离开时可以带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究竟如何自处,以何种方式确定自己的存在、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是最重大的课题。并不是说人人都想要的东西就是属于你的,也并不是说时尚流行东西就是你的,真正属于你的生活是别人所无法想象的,这是最根本的一点。而且为了追求自己的生活,自我的自处状态,也需要敢于舍弃一些东西,不去追逐那些人人都想追逐的东西。我想这是他能够给我们当代人带来的很大的启示。
当然,马克洛尔生存的世界跟当代世界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空子可钻,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模糊的地带,可以被他运用,可以让他活得自在一点,这也是今天身处越来越确定的、没有空间感的社会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存在状态。
分享嘉宾/刘文飞、汪民安、赵松、王璞
题纲及主持/张进
报道整理/宫照华 张进
摄影/王嘉宁
编辑/张进
校对/付春愔
本文图片资料由嘉宾提供,现场图片由新京报摄影记者王嘉宁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