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之致敬阿特伍德”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自2016年创立以来,“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不分国度、不分种族,一年一届致敬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对文学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倾心关注人类的爱、困境、理想的作家。作为2022年第四届“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的致敬作家,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以视频的方式发表了获奖感言,从写作和阅读的不同时空维度,以及身为作家的使命与责任等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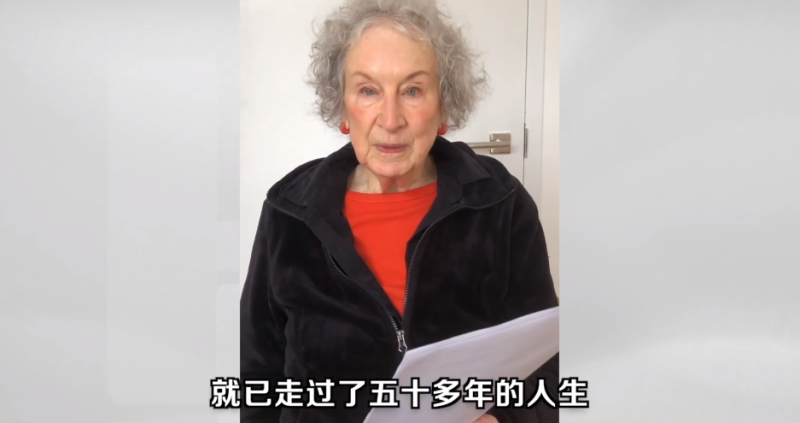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年出生于渥太华,加拿大女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诗歌重要作品有《圆圈游戏》(1966)、《那个国度里的动物》(1968)、《诗选》(1976)等。1985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发表幻想小说《使女的故事》令她一举成名 ,获提名普罗米修斯奖和星云奖,以及英国文坛最高荣誉布克奖,成为20世纪最经典的幻想小说之一。她曾四次提名英国布克奖,2000年终于以小说《盲刺客》摘得这一桂冠。2008年她获得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2017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 ,近年来她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之一。2019年以小说《证言》再度获得布克奖。(视频截图)
身为写作者,我们是各自时代的见证者
阿特伍德的获奖感言原文如下:
能够与你们在此欢聚一堂,接受由我的作家同行们评选出的这一奖项,我深感荣幸——尽管我们的交流只能通过线上的形式来实现。这是一份尤为特别的殊荣,因为它的终审评委是一群年轻的创意写作系的学生。这些年轻的写作者,我在他们出生时就已走过了五十多年的人生——那可是半个世纪。写作就像一艘太空飞船,能够跨越遥远的距离。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写作使我们得以在不同的星球、不同的宇宙间穿行。写作又是一架时光机,从过去抵达现在,又从现在前往未来。我们期待这样的未来,人类仍在其中保有一席之地,而这些未来的人,依然具有阅读的能力。写作如何能够这般跨越时空?唯有通过年轻的后来者——倘若年轻人不再对文学抱有兴趣,作家的作品也将不复存在。但只要我们继续阅读,那些数千年以前的声音就会持续向我们发声,如同他们仍与我们处在同一时空,就像我们的邻人一般。写作也能够从一种语言走向另一种语言。这或许是文学最困难的旅行。这世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语言,它们讲述不同的故事,讲述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谈论听者所不能见的种种。语言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没有这些语言,也就没有身为人类的我们。人类使用的语言是如此丰富多样,有些已经消亡,其余的则不断演变,但每一种语言都承载了一种独特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假设一种语言表述的都是既定的意象,而另一种语言则与之相反,表述的都是尚未成型的流动的意象,我们可以想象,两者之间会有多大的差异。然而,它们描述的都是现实的一个侧面。倘若这世上仅剩一种语言,那会是怎样的悲哀——人类思想与认知的多种可能,以及由此催生的人类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也都将随着其他语言的逝去而消亡。我们,这颗星球的全体居民,正面临着大量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这些危机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气候危机引发了洪水、山火、干旱和歉收,继而又导致了饥荒、战争和其他的惨剧。想要应对这些难题,需要集结我们所有人的智慧。我所说的“所有人”,指的是人类这一整体。我们必须携手应对当下的诸多危机,哪怕我们怀揣的仅是一个良好的愿景。然而,我们要如何挣脱语言的束缚,分享彼此的见解?为此我们必须倚赖于译者。依我之见,他们尚未得到足够的褒奖。他们掌握了多么令人惊叹的技能!他们是语言的魔术师,而我们这些作家,尤其需要向他们表达谢意。正是通过这些翻译家的奇妙译笔,我才得以阅读阎连科先生的作品,并深感钦佩;正是这份基于文学的惺惺相惜,让我在收到他的来信、知悉这一奖项的来龙去脉后,欣然同意参与今天的文学盛典。尤其当我得知他是这个奖项的发起人,便惊喜地接受了这份荣誉。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肺腑的:阎连科先生的书写,以及他的文学创作,借由翻译家的“魔法”,穿越时空,抵达我的所在之处;此刻,我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到这里,与你们——我的同行们——进行交流。那么,身为写作者,我们究竟是在做什么?在人们普遍认为的“真实的”世界上,我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我们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无法左右许多事情的进展。最起码我们都没有亿万身家吧。我们甚至不是科学家或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也许我们仅仅是为读者提供娱乐的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成为预言家,说真话的人。许多可敬之人对我们心存疑虑:对于我们讲述的一切,他们并非总是持欢迎的态度,因为我们的讲述往往与两个主题相关,即人类的情感和人类的行为。而这两个主题之所以让人不安,是因为它们并不总是正向的。于是,身为讲述者的我们,可能引发某些不快。在岁月的长河中,来自不同国度的许多作家都曾为此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当然,并非每个创作者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但为了创作出坚实、有力、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身为写作者的我们必须接受的可能的选择。尽管如此,身为写作者,我们坚持呼告。我们在这世上巡游。我们倾听,我们体察。我们吟唱诗歌,我们叙说故事。我们是各自时代的见证者。今天在场的青年作家,你们都是写作这条路上的年轻旅人,我向你们致以衷心的祝福。我期待阅读你们尚未写就的小说和诗篇。或许它们也能穿越时空,抵达未来的某时某地,来到我的面前。我期望如此。再次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今天的文学盛典,也感谢你们授予我的这份殊荣,这份回忆,我将珍藏于心。谢谢。
组委会对阿特伍德的致敬词中则表示:“阿特伍德女士以非凡的睿智照见人类意识的盲区。她的书写集诗性、批判、反思于一身,深刻洞悉人类的历史,预见世界的未来。她的作品不断拓展着写作的边界,丰富着人类对于女性、暴力、文明等议题的认知。她始终关注人类生存的境况,反抗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与观念所形成的压迫。她超越性的目光,强有力的声音,精妙的叙事,让那些被障蔽的显形,被埋葬的破土,被遗忘的铭记。”
“我写的每个字都是现实,不是未来发生的事情”
活动现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昱宁两位嘉宾以“用想象见证现实:阿特伍德女士和她的写作”进行了对谈分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悦然担任主持。

“用想象见证现实:阿特伍德女士和她的写作”对谈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黄昱宁与阿特伍德的缘分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她所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阿特伍德的作品《可以吃的女人》,这本书给黄昱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盲刺客》获得布克奖以后,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代表的黄昱宁在法兰克福书展现场下定决心,一定要拿到《盲刺客》的引进版权。这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接连出版了许多阿特伍德的作品,包括后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的《使女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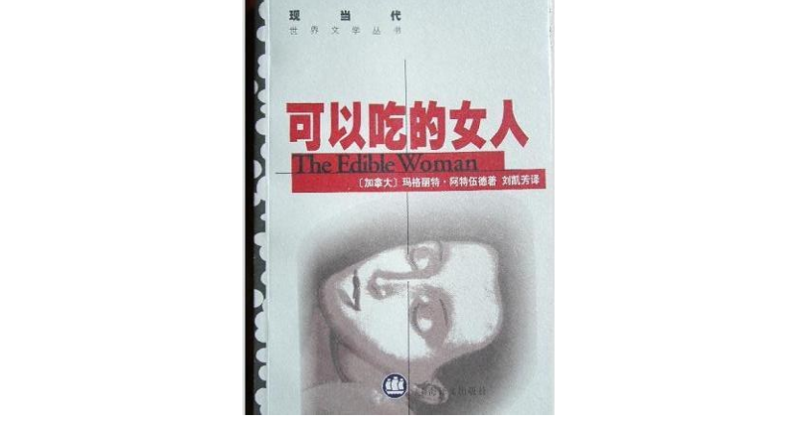
《可以吃的女人》,[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刘凯芳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作为国内重要的女性主义研究学者,张莉阅读到的第一本阿特伍德的作品是《浮现》。书中的女性在和恋人交流的时候,不断地诉说拒绝自己是受害者的身份,她要逃离这种受害者的身份,这对张莉产生了很大触动,这让她意识到,阿特伍德这位作家对世界的理解非常不同。张莉意识到,阿特伍德实际上是加拿大文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重要推动者。《与逝者协商》是对张莉触动很大的另一部作品,在这本演讲集中,给予张莉的是一种作为批评家的触动。
2015年,张莉参加挪威文学节时在餐厅中看见了阿特伍德,还远远拍下了一张照片。作为挪威文学节的主嘉宾,阿特伍德为此准备了一个很长的演讲,她幽默风趣的演讲风格给张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张莉看来,阿特伍德是一位特别愿意和读者交流的人,她和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不同于其他经典作家的在场感,“我就觉得她渴望她的读者,她渴望她的年轻读者,同时,她渴望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她渴望了解,也渴望去探索。”
张莉认为,阿特伍德和其他女作家最为重要的不同,是她关注人类的生存,关注人的生和死,包括整个人类命运的生存。比如说《使女的故事》里面讲到的生育危机,还有环境危机等。在这之中,她使用的女性视角,赋予了她作为作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书写生育困扰时,她的经验优于其他作家。当然,阿特伍德是排斥女性主义标签的,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读阿特伍德,依然可以发现其中有非常多的女性主义视角,这是她作为女性作家的一面。张莉认为,阿特伍德通过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写作,抵达了对人类生存境遇整体的观照。
张悦然认为,《与逝者协商》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思考写作的书,里边非常真诚地谈到了作家的六组关系,包括作家与死者之间的关系,作家与金钱的关系等。与此同时,阿特伍德还认为,写作是一种天赋,一种礼物,接受了它,也要还出一些东西,必须让这些礼物运转起来。这给张悦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对写作,对文学认识的理念,“她可能不是一个小说家……大家可以在她的不同领域,包括她的诗歌(领域)去探索。”
 《与逝者协商: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谈写作》,[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赵俊海 李成文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与逝者协商: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谈写作》,[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赵俊海 李成文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版。回到《使女的故事》和《证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作品中的前瞻性、预言性?它和我们的社会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黄昱宁说,阿特伍德的很多作品被定义成科幻小说,但其实和现实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正如阿特伍德本人所说的那样:“我写的每个字都是现实,不是未来发生的事情。”在阿特伍德看来,拨开事物的表面,女性的困境并没有发生实际性的改变,只不过有时候被包裹上一层层表象,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改善。黄昱宁认为,阿特伍德正是要用貌似发生在未来的故事,书写她认为的身边的现实。

《使女的故事》,[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陈小慰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5月版。
《使女的故事》书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当时也曾引发比较多的争议和关注,但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部书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是被遗忘的,当时更受关注的可能是《盲刺客》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使女的故事》在当下又会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呢?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广泛的共鸣?在黄昱宁看来,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需要这种简单的、冲击力强的东西来呐喊。
在张莉看来,优秀的作家每部作品都有预见性。判断作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文学的敏感性或者对时代问题的敏感性。阿特伍德思考的生育权的问题其实就是现实,只不过用未来进行了包裹,进而拥有了预言性。包括《证言》,都是用预言的方式来书写现实。张莉认为,这正是阿特伍德非常独特的表现手法,“看她的很多故事,故事本身没有那么吸引你,但是她的表现手法或者她的讲述方式,赋予了她的心意和震惊感……1985年的一个作品,二十年后再重新返回我们这个时代,也恰恰说明她当时的前瞻性。”
记者/何安安
编辑/商重明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