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听说过“人造肉”。如果是十几年前,有人提这个概念,我们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开玩笑,“人造肉嘛,谁没吃过?小卖部的‘唐僧肉’!”
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实物了。
前不久,荷兰科学博物馆展览了一颗由澳大利亚公司制作的肉丸——从灭绝猛犸象DNA培养出的“人造肉”。近日在国内,也有企业接受媒体采访称“研发出中国首块100%细胞肉”。在美国,包括肯德基、麦当劳等餐饮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人造肉”引入到餐厅。
一个可见的趋势是,“人造肉”正在成为食品行业最大的投资热点(比尔·盖茨也高调加入了这个领域的创投)。不过也有国家对此持否定意见,比如意大利农业部门就表示拟禁止“人造肉”进入市场。
目前的“人造肉”有植物肉和细胞肉两大种类,这其中又以细胞肉最受关注,原因是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肉,在口感上也最接近真实的饲养肉。不同的是,当我们在餐盘上夹起一片肉,细嚼慢咽之时,为这块肉贡献了细胞的动物,此刻可能还在某个地方活着,吃着草。或许未来,影响我们能吃什么肉的,以及吃上何种质量肉的,将不是农夫、饲养员,也不是农贸公司,而是实验室的科学家和企业的投资人。
实际上,实验室培养动物组织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转向食品不过十年。2013年,马克波斯特的莫萨肉类生产出了全球第一块细胞培养肉汉堡。当时这个汉堡的成本是33万美元。
“人造肉”之所以被许多消费者接受,一个重要伦理基础是动物权利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抗。“人造肉”许诺将免除动物被宰杀的痛苦命运。而这也是盘踞在我们内心的一个道德拷问,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上,是以驯服并且饲养动物为根基的,利用它们补给能量,而随着文明的进程,一种罪恶感也若隐若现。人与动物的关系被要求重造。这种罪恶感甚至能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试想,家长看着孩子跟买回家的鱼虾开心玩耍,甚至从校门口买来鸡崽喂养,如何向他们解释这些可可爱爱的生命,其终点是在厨房和餐桌?何其残忍。即便是通晓食物链,并且已经接受这条链的人,某天听到牛羊猪还有鸡鸭鹅在被宰杀前的叫声,也必然于心不忍。这些琐碎的念头,在观念层面有力量引发一场关于动物生命之权的反思。

将人与动物角色互换的电影《人肉农场》(The Farm,2018)剧照。
而“人造肉”生产公司在向外界介绍产品的过程中,开篇和结尾也离不开展示伦理意义。长期调查和报道食物的作家津贝洛夫(Larissa Zimberoff),“受企业邀请参观实验室和工厂,“我切开鸡肉,他们盯着我”,看到动物命运将可能被改变的希望和许诺,同时又想到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后果。
什么是“人造肉”?是否更环保,更道德?这是必须回到生产一线才可能完成的反思。

《炫技的食品》,[美] 拉丽莎·津贝洛夫 著,森宁 译,九州出版社·后浪,2023年2月。
鸡肉上桌,
鸡或许还活在农场里
我手里的包装盒看上去有模有样,就像我在超市里会挑中的东西一样。一个石盘的特写,里面铺着羽衣甘蓝和一些紫洋葱圈,上面放着一块烤鸡胸。包装盒上有一小块透明的玻璃纸,让我能窥视里面的内容塑料膜盖住的一块去了皮的鸡胸。盒子上印着“加州爱的结晶”。盒子背面的营养成分表下方是配料表,普通到你或许会忽视海盐、墨西哥辣椒、糖和大蒜。一切都很寻常,除了打头的原料:鸡肉(细胞培养)。
这确实是一块鸡胸,却不是从一只死掉的动物身上切下的。它是由位于加州伯克利的孟菲斯肉类在实验室用细胞培养而来的。那只贡献细胞的鸡或许还活在某个农场里。

《老友记》(Friends) 第五季(1998)剧照。
孟菲斯肉类大楼的二层通向一间巨型厨房,这里大到可以举办一场厨艺大赛。炉灶后面站着食品科学家摩根里斯(Morgan Rease),他留着时髦的大长须,穿着围裙。空气中弥漫着煎蘑菇的香气。我的鼻子抽动了一下,口水不自觉地流出来,尽管我才吃完午餐不久。“你有什么不吃的东西吗?”里斯问。我不喜欢吃的食物名单不长,但当写作这个主题时,我的座右铭变成了:“我什么都能吃。”
在我参观房间的装修和设计时,里斯和我一起等待着孟菲斯肉类的首席执行官乌玛瓦莱蒂(Uma Valeti)。在加入这场食品技术革命之前,瓦莱蒂是一名心脏病专家,这是一份拯救生命的职业,但他希望凭借着新事业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并停止虐待动物由于幼年时期在印度的遭遇,他对此感受极其强烈。从美国的医学院毕业后,瓦莱蒂留了下来。除了临床工作,他在明尼苏达大学还有一间研究实验室,那里的患者都有严重的心脏病。干细胞是治疗手段之一,但这位创始人开始设想他能否让人类更健康从食物着手如何?这个想法一度被他置之脑后,直到他被介绍给如今的联合创始人尼古拉斯吉诺维斯(Nicholas Genovese),一名肿瘤学博士。彼时,这对伙伴还需要一个催化剂细胞培养肉,让他们能够放弃医学事业,投身高风险和高度不确定的未来。
离开医学界已经5年,但瓦莱蒂仍然保留着医生的气质谨慎克制、谈吐文雅、成竹在胸,足以让他成为筹集巨额投资的不二人选。每一家细胞培养肉公司都对别人说他们的工作是“造假”而感到难堪,但在早期,细胞培养肉确实过于稀奇古怪,因此瓦莱蒂被大部分投资者拒之门外。尽管如此,在最早的种子轮融资阶段,瓦莱蒂还是募集到了300多万美元。“这个产业从来没有被资助过。”他说,直到他向投资者展示了细胞培养肉具备的可能性。如今,昔日的愿景已经落地生根为一家拥有超过60名员工的公司员工中有动物权利活动家、环保斗士,甚至还有肉食者正对成为第一家商业化生产细胞培养肉的公司跃跃欲试。
他们,野心勃勃
大部分的创始人都对细胞培养肉的未来信心十足。马克波斯特(Mark Post),荷兰莫萨肉类公司(Mosa Meat)的创始人,被公认为细胞培养肉运动的发起者。波斯特在实验室里研究细胞培养肉长达15年,无论是荷兰式的精明,还是漫长职业生涯中的屡次尝试,都让他对这条看似不确定的道路远没有那么保守。《食物飞客》(Food Phreaking)有一期“体外肉里有什么”专题,波斯特在其中写道,在实验室生产食用肉类为节约资源提供了可能,尽管这还需要证实。相反,瓦莱蒂只谈到需要“向世界证明这项工作行得通”,他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产品”以及“人们喜欢这个想法的证据”。
在我们去会议室的路上,瓦莱蒂在洗手间旁边墙壁上的公司年表前停了下来。孟菲斯肉类有很多里程碑式的日期,例如公司的成立(瓦莱蒂认为他的公司是第一家细胞培养肉公司,成立于2015年),第一颗肉丸(2016年生产,成本1000美元),还有2017年A轮融资筹集到1700万美元,这是当时细胞农业获得的最大规模的投资。
当大多数细胞培养肉初创公司还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物种时,孟菲斯肉类却全面撒网,声称它的平台能够培养所有种类的细胞和组织。在它17 000平方英尺的总部里,科学家们培养出了牛肉、鸡肉(美国消费最多的肉类)、鸭肉(消费最多的是中国),并让1000多人尝过。

《小鸡快跑》(Chicken Run,2000)画面。
瓦莱蒂又带我回到了厨房,里斯正将一小片鸡肉从煎锅中取出来。他把鸡肉放在一块砧板上,轻轻地逆着纹理切开。瓦莱蒂催我上前观看,“摩根切鸡肉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切法和质地。切起来真正像一块鸡肉”。
里斯身旁的盘子里,两把金色大勺子盛着浸着酱汁的样品。“没有人吃原味鸡肉。”瓦莱蒂说。我想,该把这句话告诉健身爱好者,瓦莱蒂一定希望他们能享用他的产品。其中一把勺子里的酱汁是柠檬香烤鸡排的味道,另一把则是沙嗲鸡肉配花生酱和自制的姜汁泡菜。两把勺子旁,还有一小份没有调料的原味鸡肉。我低头看了一眼盘子,又抬头看了一眼主厨,最后转头看了一眼瓦莱蒂。大卫凯(David Kay),孟菲斯肉类一号员工和传播主管,此时站在一旁拍照。在这些孜孜不倦地重塑我们食品供应的人面前试吃样品,是我最不舒适的职业经历之一。
我切开鸡肉。他们盯着我。
瓦莱蒂是正确的,它切起来很像鸡肉。我把半英寸长的一块放进嘴里。就像传统的鸡肉一样,它有韧性,也有嚼劲,一种需要我的牙齿将其咬住的感觉。我能够感受到嘴里丝丝缕缕的肌肉。但它也很干瘪,没有我希望的鸡肉的多汁和湿润。瓦莱蒂跟我保证说,在肌肉细胞之外还有脂肪细胞,但是我尝不出来。肉本身有味道,但是煎它用的油对我的味觉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接着我被告知,我吃到的肉是从一个鸡蛋的细胞开始培养的。这就又回到了那个老生常谈的起源故事蛋生鸡但是我不禁猜测,有多少人愿意这样调换呢?
接下来,我将那勺柠檬香烤鸡排味的送进嘴里。对喜好肉食的人而言,它很有滋味,比那份原味的好太多。鸡肉的质地与黄油、柠檬和刺山柑花蕾绝妙地配合在一起。

《顶级大厨》(Top Chef)第十九季(2022)海报。
此刻,周围的人密切注视着我的反应,就像在参加真人秀《顶级大厨》(Top Chef)。我避开他们的目光,默默希望自己能够留下一些记录。我说了很多次“哇喔”,这给我换来了思考的时间。“尝起来很健康。”这或许并不是他们想要听到的话,但确实是我的肺腑之言。最重要的是,他们抓住了质地所有仿肉的必要条件。“质地太棒了,令人印象深刻。”我一遍遍地重复着。
盘子里只有少许试吃的样品,因此我很难想象一整块鸡胸出来。据瓦莱蒂说,他们已经制作出了“完整形状的鸡肉”。
道德或利润?动机来源
当我跟这些硅谷的创始人交流时,信不信由你,钱通常是他们最不愿意谈论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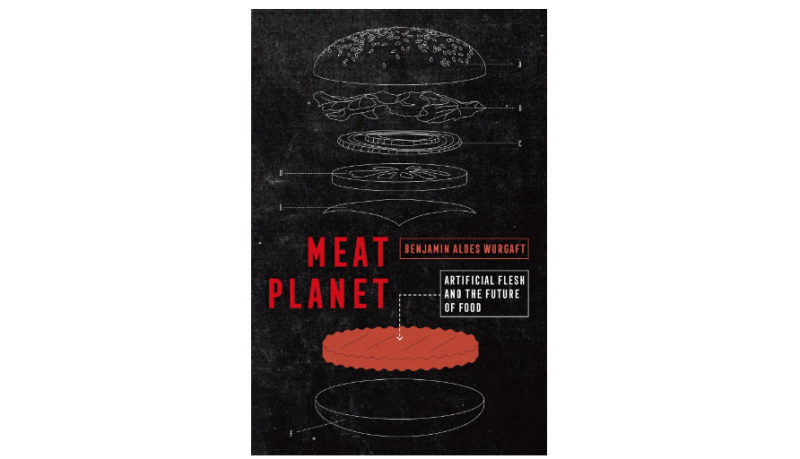
《肉食星球》(Meat Planet)书封,加州大学2020年10月。
《肉食星球》(Meat Planet)的作者本乌尔加夫特(Ben Wurgaft)对此也有同感。“我一直渴望(采访到)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想赚钱的人。创始人想要把道德使命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他们事业加速的主要动机可能是不忍心让动物受苦,也可能是钱。”
跟我一样,乌尔加夫特认为很多创始人都是真诚的。他们指出了动物福利的道德困境。发达国家的肉类消费仍然在稳步增加,我们需要杀戮更多的动物来迎合吃肉的习惯。从道德的角度看,数字并不重要。吃掉的是1只动物还是100万只,意义等同。事实上,2020年,全球一共有360亿只动物被杀死以供食用。
接下来这些创始人需要搞清楚传统畜牧业有多不可持续,对环境的破坏有多大,以及用动物喂养人类的转化率有多低。从投资回报率来看,用作物喂养动物进而生产蛋白质来喂养人类,是一种“效率极低的技术”。最后,他们搬出那个反复出现的统计数据,用问题来表达:“到2050年,我们拿什么养活90亿的世界人口?”耕地数量有限,年轻一代对农业不感兴趣,人类对蛋白质的需求日益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创始人将细胞培养肉作为拯救这颗行星和人类的最优选择。
向更健康的饮食方式转变需要付出努力。在“EAT-柳叶刀”委员会的一篇报告中,一群来自全球的科学家建议,我们应该将水果、蔬菜、坚果和豆类的摄入量加倍。或许更具挑战性的是,他们认为我们需要将红肉和糖的摄入量减少50以上。这么做“将会同时改善身体健康和环境”。委员会的一名科学家布伦特洛肯(Brent Loken)称,如果不做出这些改变,预计到2050年,与食物相关的碳排放将翻倍。“食物相关的碳排放极可能导致全球气温在30年到40年间升高超过1.5摄氏度的上限,在2100年前升高接近2摄氏度的上限。”这个观点被广泛接受。

《大号的我》(Super Size Me,2004)剧照。
“为了自己的饮食健康,而置地球的健康于不顾,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想法。”大卫·卡茨(David Katz)说,他是耶鲁大学耶鲁格里芬预防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也是一位营养学作家。
在2019年,当我的Instagram(一款社交应用)推送充斥着亚马孙大火的图片时,我明白这是所有与我交谈过的创始人的论据。《纽约时报》称这场火灾为“生态纵火”。饲养肉牛的牧场主在烧毁全球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带雨林。彼时,全球的抗议声排山倒海。如果那时细胞培养肉已经在售,它的广告一定会与这场灾难的图片一起在Instagram推送给我。
细胞培养肉还处于起步阶段,植物肉却已登堂入室。当植物性汉堡、培根、猪肉一飞冲天的时候,这些相对更棘手的细胞培养肉还是必需的吗?
细胞肉,是否更环保?
大规模生产细胞培养肉将会严重依赖水、能源和粮食。如果没有公司的确切数据,无法想象投入到底会有多少。
跟一磅普通牛绞肉相比,生产一磅细胞培养牛肉会耗用更少的自然资源吗?2020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托米亚山(Tomiyama)、洛瓦特等发表了一篇文章《缩小培养肉的科学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差距》(“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science of cultured meat and public perceptions”),指出理论上一头牛的一份活体组织能够在一个半月里满足10亿个牛肉汉堡的需要。如果换作传统畜牧业,生产同样数量的汉堡,需要50万头牛,耗时18个月。全球90以上的人口都吃肉。那么这30多家细胞培养肉公司能够让每个人都满意吗?

纪录片《地球公民》(Earthlings,2005)画面。
回到我之前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更关注植物肉,而非细胞培养肉?
传统农业会产生三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而细胞培养肉生产排放的几乎全是二氧化碳,它来自工厂所需的能源。从表面上看,这个差异会让我们认为细胞培养肉要好得多。牛津大学的研究者约翰林奇(John Lynch)和雷蒙德皮埃安贝尔(Raymond Pierrehumbert)在一项对培养肉和肉牛的气候影响比较研究中发现,“每单位培养肉的温室气体排放整体上要优于养殖牛肉”。但这不是全部结论。
最初,“培养肉产生的温室气体比肉牛少”,但是“长期来看,两者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在某些情况下,养殖肉牛产生的温室气体还会少很多,因为甲烷排放不会累积,而二氧化碳会”,后者是细胞培养肉生产排放的主要气体。要让细胞培养肉比传统肉更有利于环境保护,最好的办法是确保细胞培养肉产业主要依赖可再生能源。

电影《我是传奇》(I Am Legend,2007)中的世界末日。
一直以来,细胞培养肉行业对风险资本家、天使投资人和消费者的营销说辞都是,这将拯救世界。克丽丝蒂斯帕克曼(Christy Spackman),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未来社会创新学院助理教授,指出了这种思维的谬误。“我想说这不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工业化已经让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我们曾经为之欢呼雀跃的工业化,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困境例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产生无法重新进入土地的有毒废水。斯帕克曼感到,在新型食品工业化生产之前,我们亟须考虑细胞培养肉生产所需的配套系统。要记住,大规模工业化是每一家细胞培养肉初创公司一起步就想要达到的目标。
在《肉食星球》的作者乌尔加夫特看来,我们对于工业化肉制品的欲望缩减是一个好现象,但他希望这是公众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所做的自由选择,而不是迫于政府干预或市场压力:“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希望人们实际上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2017年,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新收获大会上见了面,当时他在那儿做访问学者。这位头发蓬乱不羁、架着眼镜的作家最让我喜欢的地方是,他并非一名饕餮之徒,不为任何一家初创公司效力,也不是一名投资者。他吃肉。在这场游戏中他没有利益瓜葛。他身上兼具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气质,对于细胞培养肉这个问题,乌尔加夫特也没有独断地认为吃动物就是不好的,或者吃素就是未来的唯一道路。
问题是无穷无尽的
监管往往被认为是这些产品通向市场的主要障碍之一(其他障碍还有消费者接受度和培养基)。
一些知情人士称,一旦美国批准了细胞培养肉,其他国家也会效仿。另一些人则认为,在那些监管更宽松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新加坡和日本,细胞培养肉或许能够更快进入市场。对FDA(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说,检查细菌、病毒和其他生物制剂可能造成的污染尤为重要。作为一个预算紧张的政府机构,FDA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去实地考察这些工厂,并透彻了解它们的技术以对其进行评估?“除非你有一个完全无菌的工厂,有洁净室,生物反应器由机器人操作,否则食品被污染的风险仍然存在。”乌尔加夫特说。好的一面是,受高度控制的生物反应器能够被实时筛查,甚至能够利用云端数据进行远程评估。相较之下,工业化农场的通道戒备森严,肉类包装厂的工人安全也不合格,疫情期间的很多丑闻就是证明。我们认为存在监管和法律两方面的保护,但保护在哪里呢?

《炫技的食品》(Technically Food)英文原版书封,Abrams出版社,2021年6月。
甚至FDA那些负责监管医用动物组织培养的专家,也认为培养食品级的肉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一次关于使用动物细胞培养技术生产食品的公共听证会上,FDA的消费者安全官员杰里迈亚法萨诺(Jeremiah Fasano)称,即便传统肉类和实验室肉类完全相同,安全顾虑依然存在,比如不同的次级成分生物体特有的辅助生长的物质和化学品,又如预期外的代谢物细胞呼吸的中间产物、副产物和终产物。生长中的活细胞会产生大量的代谢物。“恰当地说,生物生产系统相当复杂。”法萨诺说。
听证会上的另一名专家是保罗莫兹吉克(Paul Mozdziak),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养禽学教授。他谈到扩大生产规模的挑战,回应了乌尔加夫特的担忧,“(实验室中)每个转移的地方都有可能让污染进入,包括细菌、微生物、病毒的污染”。这里的诱惑将是使用抗生素,抗生素不仅不受畜牧业的欢迎,很多专家也认为它对公共卫生的威胁比气候变化更严重。在高技术生产环境中,安全规则必须一丝不苟地严格遵守,而这很大程度取决于员工的仔细程度——“在细胞培养中,大部分的污染其实是人员问题。某人若在某个环节出现了纰漏,将很难追查。”
在污染之外,还有其他值得思考的方面。这些细胞是克隆的,而万亿量级的克隆将产生基因变异。变异不是随时发生,但炸弹就埋在那儿。在《十亿美元汉堡》(Billion Dollar Burger)中,马克波斯特告诉作者蔡斯珀迪(Chase Purdy)这是一个可能发生的“灾难”。在每一次复制中,DNA都“可能发生基因突变”。这将生成不稳定的细胞,对于计划大量制造细胞培养肉的初创公司而言,这是一个挑战。我们被告知,吃下这些经过基因改造的细胞,不会对健康造成威胁。但我们最好不要轻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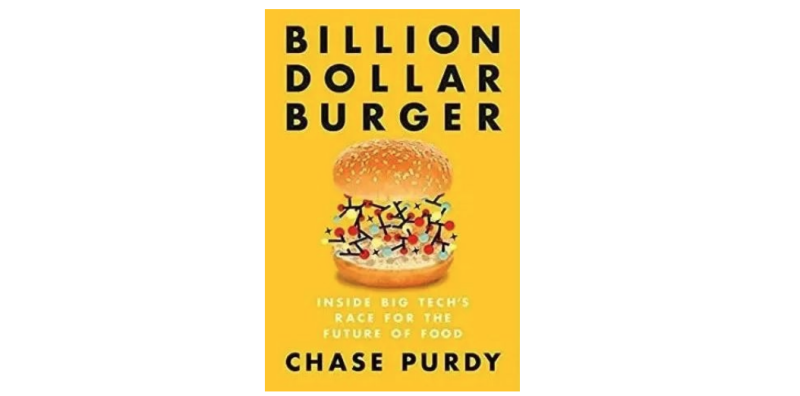
《十亿美元汉堡》(Billion Dollar Burger)书封,Portfolio出版社,2020年6月。
相关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
无法承受的后果
细胞培养肉与私房菜或在农夫集市上贩卖的小批量美食相距甚远。它还享受不了那样的奢侈。你能想象一块标价1000美元的鸡肉出现在农夫集市的折叠桌上吗?相反,这些公司正直接从实验室转向大规模生产,努力降低价格以吸引大众消费者。只向富人销售还不够,它将在高价市场停留一段时间直到成本“足够低”,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要普通人负担得起,价格还要低于便宜的牛肉。为实现这个目标,这些公司需要为生产系统开发出扩增流程,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并且要让一种此前从未被创造的营养成分的成本显著下降。

电影《雪国列车》(2013)中,下层人吃的食物。
未来,相互竞争的观念会创造出一个进一步分级的食物系统吗?这个系统是否基于不同人口群体的购买力差异,就跟目前我们所处的不平等结构一样?针对渴望便利的弱势人群进行定向营销,配以垃圾食品的低价格,让这些群体的健康持续恶化。接着我们被卷入了一场疫情中,我们最弱势的群体受到最惨烈的创伤。
在《石板杂志》(Slate)的一篇文章中,未来创新专家斯帕克曼写道,细胞培养肉“会持续地扰乱代谢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根植于身体对食物来源的直接体验”。未来我们会如何向下一代传授生态意识?让一个孩子知道苹果生长在树上,牛的价值高于它们细胞的价值,是多么重要。斯帕克曼“深深地热爱着食品化学”,以及“拆开食品再将其组装回去”的过程中无限的可能性。但这么做的代价是我们不再了解食品的制作过程。细胞培养肉不能简单地把动物排除在外。“这就是理性思维让我们失望的地方。牛确实存在,并参与到了一个循环之中,它们有一套自身的免疫系统,也是更新地球而不是养活人类的链条的一环。”她说。

纪录片《食品公司》(Food, Inc.,2008)画面。
在我们等待细胞培养肉上市的时候,有很多亡羊补牢的措施可以先行。善待已经耕种的土地,改良土壤,支持再生农业,关注生物多样性和作物弹性。如果你吃肉,请购买草饲、散养的动物,以支持当地或区域性的再生农场家庭。从实施了碳固存的牧场购买是更佳的选择。在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上集思广益。减少食品浪费把食品给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扔掉。最后,把饮食从以肉类为中心转为以植物为中心。
瓦莱蒂曾公开表示,等孟菲斯肉类的生产设施投产时,他愿意邀请大家参观。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只要能够走到后厨,了解食品的制作过程,这类活动我都会积极参与。我喜欢参观工厂,还记得小时候跟我爸一起去参观蓝钻扁桃仁工厂的情景。机器和装配线创造出了效率的奇迹。但如今情况不同了。想象一下,你和好奇的孩子们站在那里,你试图向他们解释这些大型的不锈钢罐子和里面的东西。那将是一场让人兴奋的对话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在罐子里养肉的方法!
或者这会作为一条警示的信息许多年前我们还吃过动物。或许,在工厂的隔壁,孟菲斯肉类能够开辟出一块小小的农场供孩子们参观。在那里,他们能模仿牛的哞哞,鸡的咯咯,鸭的嘎嘎。当然,或许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后代解释什么是农场,很久以前,我们还在户外的土地上种植粮食。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炫技的食品》一书。
原文作者/[美] 拉丽莎·津贝洛夫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