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哈佛学术自由委员会”的成立引起了海内外学术圈的广泛关注。这一委员会由知名学者斯蒂芬·平克领衔成立,其成员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诸多学者,其中也包含许多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名字,如拉里·萨默斯(前哈佛大学校长,美国前财长)和格雷戈里·曼昆(《经济学原理》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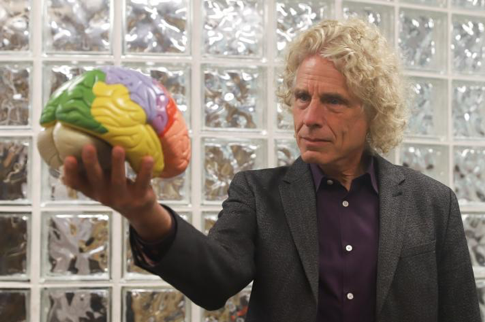
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语言学家,科普作家。被《时代周刊》《外交政策》《展望》等多部知名杂志称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图源:哈佛校报《绯红》。
乍看起来,对“学术自由”的吁求并非新异之举。但在当下,随着激进思潮与身份政治运动的蔓延,人们极易由此联系到有关“取消文化”的种种争议,也往往会将其视为“保守主义的回潮”。例如,美国《华尔街日报》在评论此事时即认为:“美国大学里的保守派如此之少,以至于旨在恢复学术自由和公开辩论的斗争将不得不由在过去被视为‘自由派’的人领导。”
诚然,在发布于《波士顿环球报》的“成立宣言”中,平克与他的共同作者,哈佛大学精神病学专家贝尔塔·马德拉斯 (Bertha Madras)确实对伴随激进运动而来的“言论审查”表示了担忧。但从全文来看,这篇宣言更近乎于对“学术自由”的捍卫,而非对特定思潮与立场的谴责。他们写道:“一个旨在求真的机构之所以必须保护言论自由,是因为没有人能做到万无一失或无所不知……我们学习和进步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猜测和反驳的循环。”因此,必须对基于理性的分歧保持足够的宽容。
从这一委员会的成立当中,我们不难意识到,在充斥着分歧乃至对立的西方社会,如何看待与维护学术自由已成为了一个摆在学术从业者面前的紧迫难题。一方面,我们需要清楚校园里的学术自由在当下各种社会思潮中如何受到了冲击,并了解相关各方的观点;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追溯学术自由的来龙去脉,以了解其为何脆弱,又能如何得到维护。
成立学术自由委员会
是“保守主义的回流”吗?
在当下,许多媒体在刻画“学术自由”受到的冲击时,往往会提供这样一幅图景:即来自各种“左翼运动”的一小撮“激进分子”对校园中的保守派人士发起“围攻”。他们扰乱后者所参与的学术活动,在校园内张贴侮辱和讽刺性的漫画,并煽动针对后者的孤立与抵制运动。
在他们看来,“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往往会造成“寒蝉效应”,使得为数众多,但更加遵守秩序或攻击性较弱的群体不敢发声。有一些数据支持这一图景:如根据英国民调机构“YouGov”的统计,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只有15%的人乐于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有88%的拜登支持者愿意亮明身份;英国智库“Policy Exchange”的调研也认为,许多学者虽在争议性话题上持有不同于“政治正确”的看法,但因担心自己被审查和歧视而不敢发声。
在许多人看来,上述图景已然构成了对学术自由的侵犯。他们认为这些“激进分子”对不同立场的否认绝非是基于理性,而仅是因为这种立场“让自己不舒服”。于是,就像他们会在视频网站上“屏蔽”令自己不快的视频一样,当面对自己“不喜欢”的观点时,其所做的也不是认真剖判,而是将其“取消”。
例如,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即认为:“当代的学生是娇生惯养、受到过度保护的一代。他们在成长中没有经历过多少不适,因而在面对观点分歧时也格外暴躁。”如此一来,激进运动的良好初衷也被遗忘殆尽:在过去,“激进”往往被理解为理论的“彻底”;但在当下,“激进”则仅仅意味着“过激的手段”,而丧失了对“探求真理”的承诺。

《娇惯的心灵》,作者: [美] 格雷格·卢金诺夫 / [美] 乔纳森·海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
然而,“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往往会对这一图景进行补充。在他们看来,“保守派”人士善于使用“合法”手段占领舆论阵地——毫无疑问,这同样应当被理解为对“学术自由”的压抑。如刊载于《卫报》上的一篇文章便曾指出,“政府正在将大学视为其正在进行的反左文化战争的战场。”通过立法手段,一系列旨在捍卫“主流共识”,限制“激进言论”的措施得以被实施。
更重要的是,“保守派”人士往往会滥用“学术自由”:他们借“学术自由”之名所传达的许多观点并无严格的学理依据,而是掺杂了大量“私货”。例如,马萨诸塞大学的一名学生便表示自己曾多次从教师口中听到否认纳粹屠犹的言论——作为一名犹太人,他对这种明显有悖事实的言论极其愤慨。
以上只是一个相当粗略的梗概。但只要熟悉了论争双方的大致理据,我们便不难意识到,平克等人的宣言实际带有一种“超越左右之争”的意味。这份宣言批判了校园中的“激进分子”,认为他们“掌握着发起不对称战争的武器库,包括扰乱活动的能力、在社交媒体上召集电子暴徒的能力。且他们乐于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跨性别恐惧症一类的指控来抹黑使其不快的目标。”但也同时对来自保守主义阵营的“合法干预”感到担忧:“政客们试图通过立法规定教育内容,或在董事会中安插亲信来对抗左翼力量。但学术领域的硬通货应该是说理和论争。”
换言之,它既反对“变味的激进”,又抵制“来自上层的压力”。相较于特定立场,毋宁说平克等人捍卫的是“学术自由”本身。这种“学术自由”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想商谈语境”:在一个平等的环境当中,商谈各方都拥有发声的机会,且可以期待自己被认真地倾听;而在商谈的过程中,他们将仅仅以说理的方式来影响他人。

《英文系主任》剧照。
学术自由的理想
为何“生而脆弱”?
在许多人看来,平克所设想的这种“学术自由”正是大学所应具有的“本然面貌”。只有获得了这样的学术自由,大学才能可靠地承担起“思想启蒙”的使命。然而,正是这种在人们看来“理所当然”的状态,在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却显得相当脆弱空洞,甚至从未得到充分的实现。
如在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看来,当代的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其中的人文社会学科,自诞生起便与权力密切交缠。
在追溯社会科学之起源的过程中,沃勒斯坦指出,社会科学始终将“促进社会改良”作为自身的使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社会科学需要与国家权力相结合,才能将其理论转化为实践。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科学所“服务”的国家大都兼具“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属性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换言之,社会科学如要一展抱负,便不得不和此类国家所从事的实践相“结合”。因此,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取径从一开始便受到了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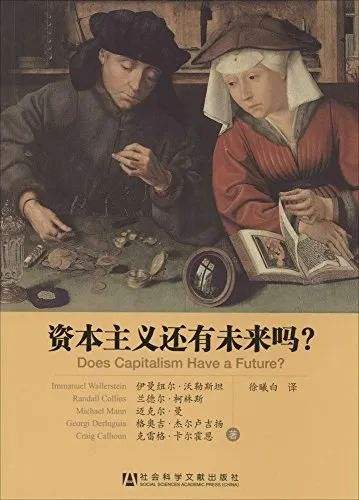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
沃勒斯坦列举到,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往往将“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转机制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并旨在培养能维系此类机制运转的“国家精英”;而人类学、东方学等学科则旨在帮助现代强国更“明智有效”地“管理”其所遭遇的异质性文明,并将其纳入“现代世界”的体系。
同时,如若某些研究无法很好地服务于上述实践,甚至旨在颠覆此种实践,那么这些研究便极有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被驱逐出大学体制。例如,批判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职时便曾遭到过排挤。当然,他的学生安吉拉·戴维斯因其在激进运动中的作为而被联邦调查局列入通缉名单。马尔库塞则因公开为戴维斯辩护而招致了右翼人士的敌意。一方面,校方开除了马尔库塞(有说法认为,对马尔库塞的开除采用了一系列复杂的花招,以便在平息州长罗纳德·里根的怒火的同时又保住学术自由的门面),另一方面,马尔库塞还收到了来自极端分子的死亡威胁。

《英文系主任》剧照。
当然,尽管研究型大学自其成立之始便具有倾向性,但“学术自主”和“追求客观”的观念仍被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理想而提出。此种观念最著名的倡导者即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试图建立一种“既是有用的、事实上又不被用于为特定党派利益做辩护”的学说。而在当代,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等人也同样因其对“公共领域”的设想而闻名——一个运转良好的公共领域能平等地容纳种种话语在其中互相“说服”,进而形成基于理性的共识。
很显然,这样的观念与“学术自由”的愿景相当接近。但这些观念在现实中的效力则是存疑的。如针对韦伯“学术自主”的理想,法国学者雷蒙·阿隆便曾指出:韦伯“既将政治和科学分离开来、又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说分离是因为科学必须独立于我们的偏好,不掺杂任何价值判断。说结合是因为科学是以一种对指导实践所必需的方式来加以建构的。”
如果说“学术自由”在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是“脆弱”甚至“空洞”的,那么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带有倾向性的大学机构何以能具有“学术自由”的外观?对于这一问题,援引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或许会有所帮助。在葛兰西看来,“霸权”意味着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得到了人们的“积极同意”。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某种“霸权”性观念的存在使得大多数学者自发地围绕此种观念建构自己的理论,并将分歧限定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由此,“学术自由”的问题也就不再那么尖锐。

《英文系主任》剧照。
身份政治引发的新困境
虽然学术研究始终带有偏向,且充分的“学术自由”从来都十分脆弱。但近年来,“学术自由”遭到侵蚀的印象似乎尤其明显。正如平克等人在其宣言中所提到的,美国人对本国高等教育的信心迅速下降,他们普遍感受到作为智识殿堂的大学也开始频繁地压制意见分歧和不那么“政治正确”的言论。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症候”来自于两方面作用。从一方面来看,既有的“霸权”观念正逐渐面临“合法性丧失”的问题。在19世纪,“历史进步论”一度风行,人们普遍相信通过逐步进行适度的“社会改良”,一个更加完满和美好的未来是可能的;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打破“进步论”迷思的同时,战后的“专家治国”和“技术至上”主义再次扮演了“霸权”观念的角色。此种观念将任何社会问题化约为可以通过“技术途径”被解决的“技术问题”,进而起到了消解社会对立的效果。然而,正是随着包括身份政治在内的一系列“新社会运动”的流行,此种观念的“霸权”地位再度受到冲击。人们意识到,争取平等和“承认”的斗争绝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
而另一方面,“新社会运动”尚未找到一种“合法”的表达途径。在克劳斯·奥菲所著的《福利国家的矛盾》中,这种状况得到了相当完整的刻画。奥菲说:
“这些社会运动在所有方面都与政党的逻辑相反;它们是通过聚焦于一个或一系列问题来获得其力量的,因此,对于其他诸多集团的支持,它们基本持敌对的态度,而不是接纳的态度……它们在表达个人认同与集体认同方面把个人置于优先地位,但同时,它们又无法进入既定的政体形式中去。”

《福利国家的矛盾》,克劳斯·奥菲 著,郭忠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
换言之,这些新兴的社会运动本就是围绕一系列特定的问题而形成,因而其并不旨在提出一系列连贯的施政纲领,也并不过多思考如何与其他社会诉求协调的问题。因此,他们难以通过传统的政党政治或“合法”途径来令自身诉求得到实现。如此一来,在旧的“霸权”已经坍塌,而新的“沟通渠道”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些社会运动对包括“学术自由”在内的秩序所产生的冲击也就尤其显著。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说平克等人的宣言是对激进运动的一种反抗,不如说它所提出的关于“学术自由”的倡议实际为论证中的各方都提供了发声的空间。正如平克所期待的——“我们将赞助关于学术自由主题的研讨会、讲座和课程。我们还打算让新教师了解哈佛对言论自由的承诺,以及当言论自由受到威胁时可供他们使用的资源。我们将鼓励保护学术自由的政策。”如若这些建议能得到实际的落实,那么其的确可能缓和矛盾,使学术分歧不至发展为社会分裂。
同时,还有学者提出科研人员应更谨慎地利用自己的“学术自由”,使之真正建立在学理之上,而不至于成为伤害的借口。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构成了捍卫学术自由的前置条件。如科学家贝彻(Bettcher)表示:“学术自由伴随着责任;我们不应利用这种自由来伤害人们,尤其是我们社区中更脆弱的成员。对该问题的担忧不应被视为对学术自由的威胁。”
简言之,重建一种更加充分,且能容纳多种异质性学说的“学术自由”必定是一项相当繁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意味着大学师生应努力建立起某种行之有效的“公共空间”,更意味着大学与权力的结合,乃至其学科体系需要被重新看待。然而,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平克等人的呼吁仍不失为一种能力范围内的有效之举——它意味着今天的学者中仍有人珍视其“探求真理”的使命,并愿意为此而包容不同的声音。
参考文献:
[1]Is cancel culture threatening universities?
[2]New faculty-led organization at Harvard will defend academic freedom
[3]Stop using “cancel culture” to talk about academic freedom
[6]academic-freedom-and-cancel-culture
作者/谢廷玉
编辑/李永博
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