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一生中遇到许多被排斥的情况。一扇打不开的门、不舒适的座椅靠背、只支持某个语种的操作系统、只接受信用卡的支付系统、无法完成的验证环节……被设计拒绝时,我们难免疑惑:到底是自己不够正常,还是设计不够包容?
设计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体验。不包容的设计却无处不在,这种不包容可能仅仅因为设计师的偏见,或者对用户需求的误判。与其说好的设计要包容更多元的人群需求,不如说设计师应该从根本上打破所谓“正常人”的概念。正是这个危险的概念,让某个标准以外的人失去了应有的权益和良好体验。设计应该重视“以人为本”,而这个“人”,当然不能只是“正常人”。以下内容选自《误配:包容如何改变设计》,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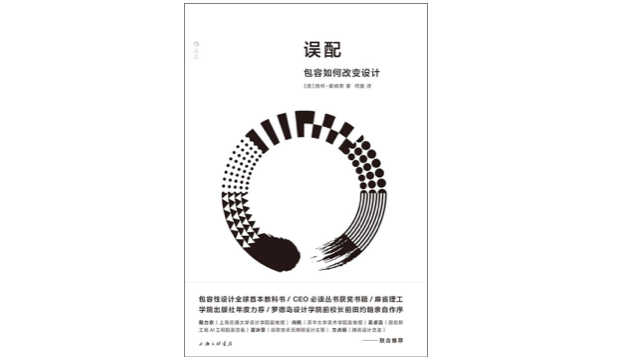
《误配:包容如何改变设计》,[美] 凯特·霍姆斯 著,何盈 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2月。
“正常人”:一个危险的概念
世界上到底存在多少种人?
如果我们想要造福全球数十亿人,那么我们的设计就必须满足不同人的奇特需求。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人是很难预测的。面对这种复杂性,我们该如何设计?滋生惯性排斥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往往一开始就过分简化了“谁是用户”这个问题。而随着设计的推进,“人类的多样性”这个重要元素也没有被纳入考虑范畴之中。
为了让设计能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设计师们通过各种技术对“普罗大众”进行假设,他们常常陷入一个危险的概念——“正常人”。
“正常人”这个概念,其实一直以来深受19世纪比利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背景,故事源自于托德·罗斯(Todd Rose)的著作《平均的终结》(The End of Average)。凯特勒希望能成为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那样出名的科学家。牛顿的运动定律和热力学定律,让宇宙中看似不可预测的现象变得有规律可循,也让概率论和数学预测越来越受欢迎,甚至催生出新的科学领域。凯特勒把自己的野心投到了另一个方向:通过数学方法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他开始对人类的各种数据进行测量,并制作了统计模型。
其中一个数学模型主导了凯特勒的研究:高斯分布,通常被称为正态分布曲线。这个概念最初由和牛顿同时期的法国数学家亚伯拉罕·棣莫弗(Abraham de Moivre)提出,几十年后由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证明。

丹麦纪录片《重要时刻》(2017)剧照。
高斯证明了一个事件的概率(比如天体的位置或者硬币的正反)可以用一条简单的曲线来描述。而这条曲线的平均值,即下图的垂直中线,是该事件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表达。正态分布曲线的钟形让大众很容易记住这个理论。凯特勒收集了比利时和附近地区数千人的身高/体重比、生长速度等数据。当他试着把数据制成图时,他意外地发现数据分布与正态分布曲线相吻合。
基于这个发现,凯特勒开始测量人类其他方面的数据,包括生理、心理、行为、道德等。在不同的测量研究里,他都发现了正态分布曲线的踪迹。他非常痴迷于用各种测量数据的均值来描述“完美人类”。凯特勒描述了“完美的脸”“完美身高”“完美智力”,甚至“完美道德”: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均值去定义一个“完美人类”,那么任何与其情况不同的,都可以被认为是畸形或疾病。
后来他发表了《论人》(Treatise on Man),这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书中,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与“完美均值”相比较。通过“完美均值”,我们可以计算出一个人的先天“异常”程度。人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视为错误。这个想法非常具有感染力,而且经久不衰。
正态分布曲线不仅被用来革新现有的研究领域,更催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尤其在社会科学方面。基于均值的疾病诊断方法促进了公共卫生的发展。时至今日,全球许多地区依然使用凯特勒的身体质量指数(BMI)来检测肥胖程度和健康状况。优生学及其中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论点,包括如何根据能力、种族和阶级择优繁衍,都源于对凯特勒“完美人类”的崇拜。
基于凯特勒的方法得出的结论,被用来强化某些人的影响力,同时让另一些人失去了应有的权益。
从“为所有人”设计到无人受益于此
如今,正态分布曲线对于设计的影响仍然在社会上随处可见,无论是在电脑上还是在教室里。左撇子的学生不得不使用为右撇子的“正常人”设计的桌子,智能手机上的重要功能也是根据右撇子的“正常”用户的触摸习惯而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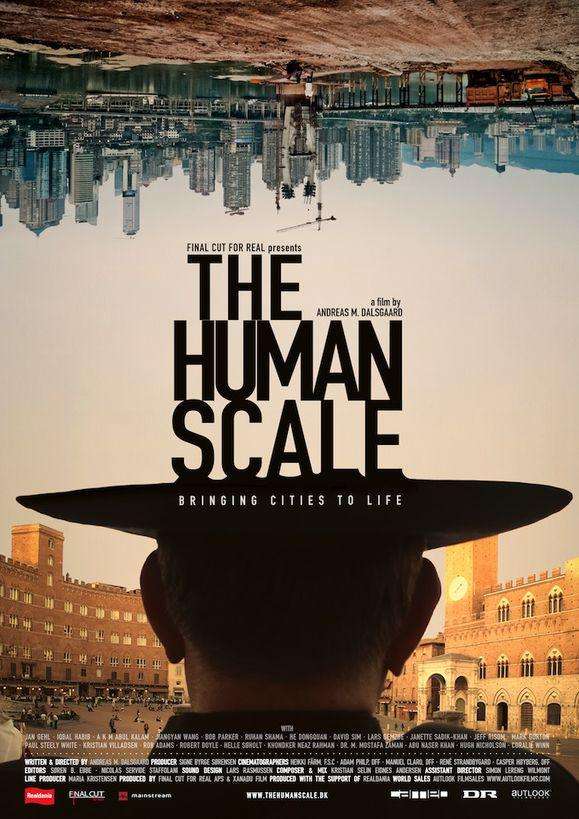
丹麦纪录片《人的尺度》(The Human Scale)(2012)海报。
“80/20法则”是对这个概念的总结。“80/20法则”最初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他发现意大利20%的人拥有80%的土地。约瑟夫·朱兰(Joseph Juran)作为质量管理领域的先驱,将帕累托这一发现转化为质量管理的规则,指出大部分问题(占问题总数的80%)是由少部分原因(占原因总数的20%)造成的。本质上,他把其中少数造成问题的“重要原因”从大多数“潜在有用的原因”中剥离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设计团队将“80/20法则”与正态分布曲线混为一谈。常见的误解是,曲线的中心代表了80%的主要用户或亟需解决的问题。人们假设:如果设计符合曲线中最大部分人的需求(即中值),那么这个设计就适用于大多数人。这个推论导致许多团队将剩下的20%视为异常值或“边缘案例”,导致相关解决方案常常遭到拖延或忽视。
事实上,这些“边缘案例”恰好能让我们创造更优秀的设计,很多被排斥专家解决的问题都与边缘案例很相似。可是,当我们提起“边缘案例”时,就意味着我们默认了“正常人”这个概念是合理的。回到设计本身,假如这个“正常人”只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呢?
为所有人设计?不为任何一个人设计?
罗斯给我们展示了美国空军史上的一个生动案例。20世纪40年代,第一款战斗机原本是为普通飞行员而设计的。为此,美国空军召集了数千名飞行员,收集了包括身高、体重在内的数百种身体数据,希望基于这些数据的均值来设计飞行甲板和驾驶舱。

NHK专题片《啊!设计》(Design Ah!)(2011)剧照。
飞行甲板的每个部件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不允许进行任何调整。当时的预设是,即使飞行甲板的仪器和部件不能完全贴合每个飞行员的身体尺寸,但他们应该可以通过自我调整去适应这种设计。
然而,当时的美国空军却有着高频率的坠机事故,很显然这不能单纯地归咎于机械故障或飞行员的失误。因此,中尉兼研究员吉尔伯特·丹尼尔斯(Gilbert Daniels)从原始飞行甲板的设计中抽取了10种人体数据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他召集了4000名飞行员进行数据测量,想确定这些人当中有多少能完全符合这10个均值。答案是0。
4000人里没有一个飞行员的数据能完全符合这10个均值,每个人都至少在一个方面与均值不同。美国空军一开始希望通过测量均值,设计出适用于所有人的飞行甲板,结果设计出来的甲板不适用于任何人。
后来,基于“个性化”的设计原则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可调节的安全带、座椅和控键等创新设计开始逐步投入使用,一旦飞行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调整飞行甲板上的各种部件的位置,飞行的安全性和飞行员的表现就会得到提高,同时这也让更多体形不同、身体机能迥异的人有机会成为战斗机飞行员。
这些进步慢慢影响了其他工业产品的设计。每次驾驶汽车时,我们都可以把座位、安全带和后视镜调到最合适的位置,不知不觉间每个人都成了个性化创新产品的受益者。
战斗机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它从“为所有人”设计到无人受益于此,我们应该引以为戒。无论是设计书桌的形状还是强调特殊学习方法的课程,如果我们总想着为“正常人”设计,很可能会让许多人步上第一批飞行员的后尘:用户不得不为了适应这些不匹配的设计而用极端的方式调整自己。
“正常人”这个概念由一位19世纪的数学家提出,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出现对于促进社会某些领域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果被误用在某些领域,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伪命题呢?我们的一生都在变化中度过。如果思想和身体的变化本来就是不可预测的呢?“以人为本”设计里的这个“人”,究竟应该是谁?
我们该如何为这些不确定性设计?
用户画像是设计师和营销人员在考虑或者定义产品用户时常用的工具。一个用户画像是对一个虚构用户的描述,其背后有大量研究数据支撑。这个用户可能会配上“珍妮特”这样的名字,外加一张女性照片,旁边的文案写着:“我是一名‘足球妈妈’,同时也是自由职业顾问,平时需要管理家庭琐事,学习新技术的时间有限。”用户画像还有男性版本,他笑眯眯地坐在电脑前,旁边写着:“我是吉姆,初创公司里唯一的信息技术专业人士,我总是紧跟潮流,喜欢使用最新的电子产品。”
和正态分布曲线一样,用户画像的目标是尽可能概括一群人的特征和需求,以此来简化不确定性因素。用户画像也是为了不断提醒设计师和工程师,他们此刻正在为别人,而非为自己设计。尽管出发点是好的,用户画像还是过分简化了人的多样性,而且没有明确指出如何或何时该将人类的多样性重新加进设计过程。

NHK专题片《啊!设计》(Design Ah!)(2011)剧照。
另外,正态分布曲线的长尾部分,代表了人们在使用解决方案时可能出现的边缘案例和某些例外情况。特别是关于可达性的问题,常被视为长尾的一部分。正态分布曲线的思维模式误导了我们,让人以为可达性的市场需求很小。在“正常”设计中,可达性被归类到特殊情况中。
如果没有“正常”用户,那么“特殊”用户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没有属于长尾范围的人群,没有“异常”情况,自然就不存在什么边缘案例。相反,我们需要更多新工具来满足人类的多样性,挑战为“正常人”设计的传统观念。
在个人电脑刚出现的时候,基于对大多数人的假设去设计电脑图形界面是合理的。因为那时的用户和使用场景都比较单一,通常是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中使用一台电脑,每次只需完成一两个任务。在数字技术早期,用户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大多数人都是电脑打字或制作电子表格的新手。
因此,在这种前提下对用户做出假设也相对容易,比如哪些人会使用电脑、他们会怎样跟电脑交互、他们的操作水平如何——他们很可能坐在屏幕前,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使用键盘打字。基于这些假设,当时的图形界面被设计成用户必须在隐晦的界面上找到各种图标,这对他们的视觉和认知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但由于他们的使用环境相对简单,这种设计还算合理。

NHK专题片《啊!设计》(Design Ah!)(2011)剧照。
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使用技术的方式的不确定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海量用户爆炸式涌入,技术的交互面临多样性的挑战。几乎每个行业都想通过数字化转型去重新构建他们的业务、产品和服务。对于许多希望在21世纪保持竞争力的企业来说,这是必经之路。
人们一天内与数字界面进行多达数十次交互,除了智能手机,还有更多不同的机器。人们在购物、导航、搭火车、买咖啡、申请工作、在学校学习、在图书馆借书时,都需要与数字界面进行交互。他们可能在灯光昏暗的电影院、阳光明媚的公园、嘈杂的咖啡馆、下雨时、为孩子们设置睡前音乐时使用电脑。有时候他们想要绝对的安静,这样才能集中注意力。当然,他们有时也愿意被家人的紧急消息打断思绪。
也就是说,技术光是先进可不够,它还必须很好地配合不同人的需求,帮助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目的下完成工作。哪怕只是想想多样性,都让人不知所措。当人们频繁切换环境和设备时,我们该如何为这些不确定性设计?
显然,仅凭数学公式是办不到的。数学模型是技术设计的基础,对于在一大群人中找到行为模式非常有用,但这些模型能否顺利应用到人身上呢?显然,数学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无法灵活地描述人类的个性。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创造对生活有益的设计,那么仅通过数学来理解人类,就相当于给未来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科技还需要向人类学习很多,尤其向那些经常被技术排斥的人,他们对误配有深刻的理解,聆听他们的真实体验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花时间去理解人类的深度和复杂性
玛格丽特·米德博士(Margaret Mead)被誉为改变我们看待人类文化方式的先驱,她让人们意识到文化在塑造个性上的重要地位。同时,她积极地推广文化人类学,在她去世时,她已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之一。当许多社会学家还在尝试利用大量研究证明种族和性别的优劣时,她就指出了智力测试其实一直存在偏见。
尽管当时凯特勒的方法激发了许多学者利用正态分布曲线的理论去总结人类特征,米德却用她自己的方法深入研究了不同类型的人类文化,有些与她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她花了大量时间深入大洋洲的土著村落——特别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和当地人一起生活,观察他们的行为和文化。1978年,《纽约时报》刊登了米德博士的讣告,摘录如下:
她的推论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细致入微的观察之上,在无法对人体数据进行测量、测试或统计调查的情况下,她会通过图像去描述观察结果。
米德博士跟当地人住在一起,吃他们家的野猪、野鸽和干鱼;帮他们照顾生病的孩子,和他们建立互助互信的关系。她曾经修过一座没有墙壁的房子,方便她随时观察周围的一切。她拥有一种同期人类学家都没有的特质,一种摆脱西方先入为主的习惯的能力。
米德博士通过亲身参与来发现研究对象的行为模式,得出自己的结论。她认为研究对象才是研究中的领导角色,他们才是真正的人类行为专家。

纪录片《座椅时代-坐的历史: 1800至今》( Chair Times-A History of Seating:From 1800 to Today) (2019)剧照。
当凯特勒收集人类数据时,他完全沉浸在“正常人”的各种数据中,比如脸、身体和性格。他的动机是找到一个理想的均值,让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趋向这一均值,同时把任何偏离这一标准的人视为“不正常”。这种动机明里暗里地被支持者一代代地继承至今,当中包括很多设计师、工程师和营销人员,他们一直崇尚这种观念。
随着数据科学一日千里地发展,情况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给计算机提供行为数据,让这种理论的数据集越来越庞大。可是,毕竟数据也只是数据,它无法给出真实而确切的答案。如何从数据中得出结论,是一门艺术。关键就在于知道如何收集、组织和理解数据。
花时间去理解人类的深度和复杂性,即便只从身边的一小群人出发,也可以帮助平衡“大数据”的劣势。“厚数据”(Thick data)是指一系列可以用来解释人类行为及其前后关系的信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他的著作《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中首次将其描述为“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厚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人们的感受、思考、反应和潜在动机的方式。
把“大数据”和“厚数据”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找到在设计中科学地引入人类多样性的方法。对设计而言,大数据就像一张热度图,可以清楚地指出哪些才是值得关注的区域。特别是当人们的行为模式跟设计师的预想出现偏差时,大数据能有效帮助我们找到其中的规律。
作为“大数据”的互补,“厚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放大并理解真相。它有助于人们发现大数据规律的根本原因,识别人类行为对大趋势的影响。大数据和厚数据并用,可以让我们理解产品及其使用环境中哪些地方存在排斥。试图通过一种通用模式去理解人类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甚至是负面的事情。但从个人出发,深入理解并解决用户的一个特殊问题,倒是可行的。
了解人们为什么需要这个设计
之前,我们研究了包容性设计和通用设计之间的区别。包容性设计强调一对一的设计,一个方案只针对解决一个问题;通用设计则强调一对全部的设计,一个方案就能满足所有需求。用户画像合集是一种包容性的设计方法,从为一个人解决问题出发,延伸到更多人身上。
回想一下电视这种视听媒体是如何崛起的。字幕最初由美国国家标准局和美国广播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明,目的是让聋哑人或听力较差的人也能理解电视内容。1972年,茱莉亚·查尔德(Julia Child)主持的《法国大厨》(The French Chef)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播出,成为第一档配有字幕的电视节目。
今天,世界上大约有3.6亿失聪或听力严重受损的人,其中3200万是儿童。随着年龄增长,几乎每个人都会丧失一部分听力。
字幕的出现让数百万人能公平地获得信息,越来越多人也获益于此。比如在嘈杂的机场或拥挤的酒吧里,球迷们可以依靠字幕观看体育节目和新闻;在安静的环境里,越来越多人因为不好意思调高手机音量而依靠字幕观看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很多人也在通过字幕学习新语言。

NHK专题片《啊!设计》(Design Ah!)(2011)剧照。
这个设计最初是为了解决电视音频和聋人群体之间的误配而诞生的,但惠及了越来越多的用户,包括因年龄增长、意外受伤或特殊环境听力受损的人。
用户画像合集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可复制的方式来创造包容性设计。让我们来看看这四个用户画像合集的例子,它们和人类的各种能力一一对应。类似的用户画像合集还可以引申到其他能力的问题上,涵盖人类的生理、认知、情感、社会等方面。这完全取决于你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以及现在人们如何与产品交互。
每一组用户画像合集的最左边,是经历误配最多的人。假如你在为电动汽车设计充电站,那么生来只有一只手臂的司机应该如何使用?在设计过程中,这样的例子肯定需要被考虑在内。和人们聊聊他们如何看待加油站里的油泵设计,相信你会从中得到很多启发。
另外,如果你可以花时间和盲人聊天,了解他们如何使用现有的付款机购物或买公交车票,也能从中获益良多。假如自动驾驶电动车在未来成为主流,那么盲人也需要能顺利使用它们,以上的用户反馈依然非常重要。做用户画像合集的目的,不仅是列出不同人的能力缺陷,更多的是让我们理解合集里的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设计。
由微软开发人员斯威莎·马卡纳瓦贾哈拉(Swetha Machanavajhala)发起的“智能助听”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天,她的邻居忽然出现在她家前门,因她家公寓发出的巨响火冒三丈。产生噪音的其实是她的一氧化碳探测器,可她因为患有严重的听力损伤,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激发了她创造新应用程序的灵感,提醒人们环境中的声音。通过包容的设计过程,她的团队从一群聋哑人和听力受损者那里学习。他们了解了聋人文化的重要性,参与了美国手语课程和活动。在过程中,她发现了一个重点:大家其实并不想要一个“修复”或“代替”听觉能力的产品,所以替人识别声音的功能,比如指出哪些声音是婴儿的哭声或喇叭声的设计,其实都是不合适的。
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声音里的情感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引导他们对声音做出判断。比如,识别出一个人说话时语调的变化,以此来判断他们到底是在嘲讽还是生气了。为此,斯威莎和团队设计了一个产品,能够对声音的强度和声音的方向进行视觉化处理,这样用户就可以转向发出声音的方向,并自行判断他们听到了什么。
回到用户画像合集本身,了解人们为什么需要这个设计相当重要。我们很少遇到单纯的功能性需求,比如想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一般来说,人的需要都比较人性化,比如想要变得更独立或者跟别人产生情感联系。
这些共同需求就像用户画像合集中不同用户的聚合剂。当我们为一个被排斥用户设计时,我们可以问问是否还有其他临时遭到排斥的用户也需要这个解决方案,因为临时或基于特定环境的需求往往很容易被忽略。如果把这些临时的排斥也考虑在内,那么这些用户也能受益于这个设计。用户画像合集可以改进现有设计方案的包容性,把看似小小的设计方案传播到广阔的人群中,并确保这个设计在未来依然适用。
为社会的包容性设计,需要考虑
更宏观的文化背景
以上介绍过的用户画像合集主要针对生理上(身体障碍引起)的误配。实际上,排斥性设计在认知、感官和社会等领域也同样存在。在这些领域中,我们也许更难发现它们的存在。因为身体障碍一般更明显,会直接阻碍你的行动,而其他误配表现得可能更微妙。以下是关于如何把包容性设计的基础扩展到身体能力之外的一些想法。
对于数字产品,设计师能理解认知上的误配尤其重要。各式各样的软件每天都在抢占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思维也常受到各种干扰。增强现实产品正在改变人们看待现实和虚拟环境结合的方式。设计一个适合学习、记忆、专注、表达、还原各种感官感受的体验,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挑战。
想要完全理解人脑和人体运行的方式,现在看来依然遥不可及。然而,在认知能力上具有包容性的产品越来越多,当中很多都集中在教育和学习领域。这些产品之所以在认知能力上具有包容性,一部分原因是邀请了有认知和感观障碍的人共同参与设计过程,另一部分则是针对认知方法的多样性(非认知障碍)而设计的。
从社会角度看,技术是一座桥梁,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接触到各种经济和社会机会,尤其当他们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时。中国现在有至少7.3亿人使用互联网,大约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其中,95%的网民通过移动设备(手机等)接入互联网。许多人通过语音输入设备接入互联网,而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也慢慢成为数以百万计的人连接互联网的重要方式。
不同的人在使用数字产品上的差异,给设计带来很多有趣的挑战。在触摸屏高度普及的领域,大多数设计师都专注于图形界面设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并触摸图形界面。而在语音输入为主的领域,设计师们则专注于语音命令和对话的设计。为社会的包容性设计,需要考虑围绕设计的更宏观的文化背景。语言、政治、货币、互联网带宽、社会细微差别等复杂的挑战,都是设计包容性方案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包容性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设计师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其所处环境里各种能力和技术的极限。我对包容性设计的了解越深,我就越相信这个星球上存在着74亿种不同类型的人。“同理心”是一个在设计中经常被提到的词语,为数十亿人创造具有同理心的设计到底意味着什么?随着技术人员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创造的产品可能会把用户排除在外,人们对同理心的关注将会再度点燃。“同理心”这个词和“包容性”一样,可以从很多层面去理解。

NHK专题片《啊!设计》(Design Ah!)(2011)剧照。
一些关于同理心的设计方法专注于单纯通过跟人交谈获得反馈。例如,向路人介绍自己,征求他们对某个想法的意见。另一些则倾向于对自己的假设提出质疑,想象其他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些团队拥有自己的研究部门,让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起进行研究。可是,大多数方法都无法同时理解数十亿人的想法。
不同文化对同理心的描述各异。在设计技术的背景下,关于同理心的两个中文描述特别有意思,我在每个汉字底下都标注了英语翻译。同理心,“用心去理解”,去“全方位地感知”。构想全球化的设计方案,需要设计师同时做好这两件事。它通过对更大的背景及其中关系的理解,结合人性的广度和深度而变得有意义。这就是迎接为74亿人而设计的挑战时同理心的进化方向。
包容性需要我们改变对设计受众的假设,它始于好奇心和观察。分析大量数据可以使问题涉及的范围更广,帮助我们更快地迭代想法并优化方案。当我们在设计解决方案时,我们有责任确保方案在功能和情感上都能很好地为人们服务。为了修正当中的细微差别,我们需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去聆听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不是每个人都是人类学家或数学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抛开他们的文化偏见,但我们都能学着去寻找那些被排除在外的观点,让它们在我们心中扎根。
原文作者/[美]凯特·霍姆斯
摘编/何也
编辑/王菡
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