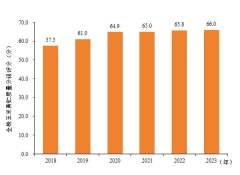蔡志洪是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的一名未检检察官,所谓未检,就是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检察。去年12月,在一起组织卖淫案中,她发现多名被性侵害的未成年女孩,她们曾因严重的妇科疾病在多家医疗机构就诊。接诊医生在发现这些未成年人受到严重侵害,且没有法定代理人陪同就诊后,并没有及时报警,导致这些女孩继续被犯罪分子控制,被迫卖淫。
涉案的8名医师本有强制报告的法定义务——2020年5月,国家监委、最高检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和2021年6月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公职人员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8名医师最终受到处罚,在福州市台江区,这是强制报告制度第一次真正“露出牙齿”。
从事未检工作13年,蔡志洪目睹过太多本可以避免的悲剧。除了是一位检察官,她也是一名女性,一名母亲。她清楚,法律可以守住底线,但让孩子免受伤害、获得充分的安全感,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的共同作用。
以下是她的自述:
将心比心
这是台江区第一次对未履行强制报告制度的责任人作出正式处罚,源头就是我承办的这起组织卖淫案。案件涉及7名未成年女孩子,都在15-17岁之间。她们大多从外地被骗过来,就是谈男女朋友,男的对她们说我们现在没有钱,为了美好幸福生活要去赚钱,就叫她们去卖淫。去年12月,这起案子我们已经以组织和介绍卖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目前法院正在审理中。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多个未成年女孩分散在台江不同的医院和诊所看病,就诊记录上清清楚楚写着她们的年龄,还有医生下的诊断。这些很明显就是非正常损伤,还有女孩子住院治疗,但是这期间,竟然没有一个医务人员在发现异常后选择报警。
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揪心。干未检工作已经13年了,我接触了大量的未成年被害人,她们被性侵后,身体和精神上都会遭受巨大的创伤。我很难想象造成那些病历上记录的损伤,会经历怎样的身体疼痛,或者会对她们以后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为人父母,我能感同身受。一个孩子的生活毁了,就意味着一个家庭也毁了。我之前办过一起强奸案,被害的女孩最终患了精神疾病,有自杀倾向,无法和人接触。后来女孩退学,她妈妈只能把工作辞掉,天天在家看着她,整个家庭全靠爸爸一个人送外卖赚钱。
我接触的性侵案或卖淫案被害者家属,他们面对检察官的态度出奇地一致,基本都是说,你不要再给我提这件事,我一个字都不想听到,我不要赔偿、什么都不要,我只要重判。然后他们往往会全家搬走,花费很大力气,想要抹去这段记忆。我了解,这是出于无奈,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这样。
正是因为了解被害人和她们的家庭将会面临什么,我才觉得气愤。如果医务人员在那些女孩看病的时候动动手指,随手报个警,她们就不用再被带回去继续卖淫,不必再遭受这种折磨。哪怕早一天被解救出来、少遭一天折磨也好啊。

4月4日,蔡志洪在取证医院召开专场培训会,为医护人员普及强制报告制度。受访者供图
这种情绪驱动我开始主导这起案件的倒查——到那些医院和诊所,去查以往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今年2月,台江区检察院开始去卖淫案女孩就诊的医院和诊所倒查取证。我们拿着掌握的资料,要求看病人的就诊记录和病历,遇到了很多阻力。
我们就回来想办法,给院方发函,同时一家家跑去和各个单位磋商,介绍这起案件中未成年人被侵害的严重情况,了解对方可以帮助我们取证做哪些工作、双方能达成什么共识、能共同做些什么。幸运的是,因为涉及未成年人,这个事情得到了各单位领导的重视和全力配合,这才有了后来一系列工作的顺利开展。
3月中旬,我们一行七八人的取证队伍来到涉案医院,除了检察官,卫健局、公安、市场监管局都派人来了。在现场,我跟院方讲情理,我说,咱们将心比心,如果她们是自家的孩子呢?
因为有卫健局的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几番交涉下,我们的一名干警在医院医政科人员陪同下,查看、拍摄了过往的就诊信息,进行取证。
我们前后一共去医院和诊所取证三次,查到9个未成年人在没有监护人陪同下,被确诊妇科疾病的就诊记录。庆幸的是,她们没有出现明显的非正常损伤。
除了医疗机构,这起组织卖淫案还暴露出酒店宾馆也是强制报告制度中落实不到位的主体之一。我们询问了卖淫案的嫌疑人和被害人,为什么每次都选择到涉案的这几家酒店日租房开房,得到的答案是“因为管理很松”。我们检察院就督查属地派出所民警执法,在翻房率高的酒店公共区域安装实时传送到派出所的摄像头,看到疑似未成年人来住,多查多问。
处罚结果太重?
3月30日下午,卫健局邀请我开一场关于强制报告制度的培训会,直播辐射到台江区整个卫健系统的270家医疗机构。卫健局的领导非常重视,在会上宣读了对涉案医师的行政处罚决定,下了一道警告处分,明确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就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3月30日,蔡志洪为台江区医疗机构做强制报告制度培训。受访者供图
在场有医生提出了质疑,认为处罚太重,因为这样一件事,就葬送了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是不是有点过?
卫健局的领导先是从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中找出了处罚依据,然后,他反问提出质疑的医生:如果是自家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要不要管?早报告、早报警,是不是可以从源头上避免悲剧发生?
我也在想,这些医生为什么不报警呢?问他们,他们就说不知道需要报警。我觉得除了法律意识淡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职业意识的问题——治病救人之外,其他都不属于医生的本职工作。但保护孩子,好像跟职业无关。
参会医生的另外一个主要疑问,是在不知道什么情形下要报警,这个问题经过培训基本解决了。
还有医生问我:如果报警了,警察来了没发现问题,会不会给患者和警方添麻烦?如果患者不愿意报警怎么办?如果女孩自己来做流产要报警吗?出于这些顾虑,有医生干脆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给他们明确,发现异常报警是医护人员的义务,不需要取得患者同意。作为医生,一旦发现情况不对,第一要详细记录患者信息、受损伤的情况、监护人信息;第二找到合适时机立刻报警。这样警察来了,即使患者跑了,也能为警方提供一些线索。
尤其是未成年人性侵案,发现难、取证难,医生的及时报告和检查记录恰好能够解决这两个难题。未成年人来做流产必须有监护人陪同、签字,否则万一手术过程中出现问题,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我们去取证的涉案医院的副院长也参加了这场培训会,他明确表态接受处罚,还当场邀请我去涉案医院办专场培训会。这两场培训会之后,仅一个多月时间,我们就接到四五起来自医护人员的主动报告,正在由公安机关处理。
是检察官,也是母亲
提起公诉就代表刑案结束了,但未检工作有个特点,就是需要履行综合治理职能,不能止于办案,要从个案延伸出来做更多事情,从源头上消灭犯罪因素。
从去年12月到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查漏补缺。造成这起犯罪是因为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些漏洞和问题,比如医院、宾馆的不作为,家庭教育的缺失,我们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监护令等措施,从源头堵上漏洞。
3月28日,区政法委对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建立强制报告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相当于把这个制度作为一个长效工作机制确立下来,合力补上了这个漏洞。
我毕业来检察院工作的第二年就开始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至今已经13年了。13年来帮教的未成年人可能得有百来个。我们和社工机构、心理咨询机构、女童保护机构、法律援助机构都有合作,就是要在各方面为未成年嫌疑人和被害人提供支持和保护。
虽然我自己也有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育的证书,但是有的孩子对检察官的身份会有抵触,而且客观来讲,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长期跟进,专业社工可以和孩子打成一片,我就会帮他们对接专业的人,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帮扶。
这些年来我有个最大的感触,对未成年人来说,家庭因素非常关键。我接触的这些未成年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家长要么不管,长期忽视孩子,要么管太严,只盯着孩子的成绩,不关心孩子的成长,亲子间极度缺乏沟通交流。
干未检这十几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孩子我不要了!”我感觉很无奈。

蔡志洪在幼儿园普法。受访者供图
因为工作原因我和女童保护组织有合作,我女儿从3岁开始,我就陪她一起上儿童防性侵的课程。3岁的孩子已经有性别意识了,能分得清男孩女孩,是接受性教育的最好的时期。这时候孩子很脆弱,也很单纯,开展性教育不会尴尬。课上,老师会讲,哪里是不可以摸的,熟悉的人摸你,你如果感到不舒服也要说不。我女儿听得很认真。
我发现,现在的学校很重视安全教育,主要针对的是地震、火灾等突发情况,做得很到位。有天我女儿突然提出让我买一个灭火器放家里,一问才知道学校给他们上了火灾演习课。
但对于性教育,学校却不知道怎么去给孩子说,不知道界限在哪里。我觉得这套课程是可以推广的,就把它给一些学校。但可能是因为传统观念的限制,或是担心学生家长反对,引入防性侵课的学校还是少数。
在未检检察官这个角色上,我的成绩单不是一份起诉书、判决书,而是孩子的录取通知书、毕业证。对有的情节不严重的未成年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后,他们被学校开除了,我们就找到学校,跟校领导求情。
有一次,一个一米八几的男孩子跑到我们单位来,塞给我一张大学毕业证。跟我说他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了,来感谢我。我都蒙了,对他完全没有印象。
后来听他说才想起来,是2014年前后,我们对他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他说,我当时告诉他以后有出息了就拿着毕业证来看我。他一直把这句话放在心里,最后真的来了。接受到这种反馈,我发自内心地快乐,那种感觉就像医生治好一个病人一样。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编辑 杨海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