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31日上午8时45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盟国空军第三十三联队少校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踏上舷梯,微笑着向地面上的人挥了挥手。飞机像离弦之箭穿破了地中海湛蓝的天空,直到油料燃尽的下午2时30分,雷达的屏幕上都没有出现它返航的身影,甚至到了今天,人们也没能找到飞行员的下落,他仿佛永远离开了大地。这位出生入死、伤痕遍体的传奇英雄生前给孩子们写下了富有哲理的童话《小王子》,身后又为孩子们的长大准备了一部寓意深沉的《要塞》。圣埃克苏佩里声称:“这部书在我死后出版,我的其他著作与它相比,只是习作而已。”为圣埃克苏佩里英年早逝而伤惜的人,看过这本随笔之后会深感安慰。我相信,他是极少数最终在沙漠里找到水源的人。
《要塞》虽然是由很多零散的随笔篇什组成,但也可以视为一部童话。在这本断断续续写了许多年的书中,圣埃克苏佩里叙述了一个关于沙漠、水井、城墙、要塞、生命、死亡、神庙、宝藏的故事。书中塑造了一个德高望重的父亲,一个帝国的国王,被乱臣贼子推入了永生。尽管如此,他的死亡也无须旁人来惋惜,因为死亡对于他是生命的完成。他的入化像一缕清风拂过河面,像一只天鹅飘入白云。当他咽气时,三天之中没有人敢出大气,而元凶也慑服于死者的威仪而跪在地上。当孩子们将父亲放到穴底时,他们觉得“不是在埋葬一具尸体,而是在储藏一份财富”。父亲不仅是一个刚毅的长者,还是一个掌握着存在秘密的先知,他以惊人的洞察力揭示了事物的本质,教导孩子们如何在沙漠中去寻找生命的宝藏和水源。因此,无论是对于圣埃克苏佩里,还是对于这位父亲来说,《要塞》都是一本遗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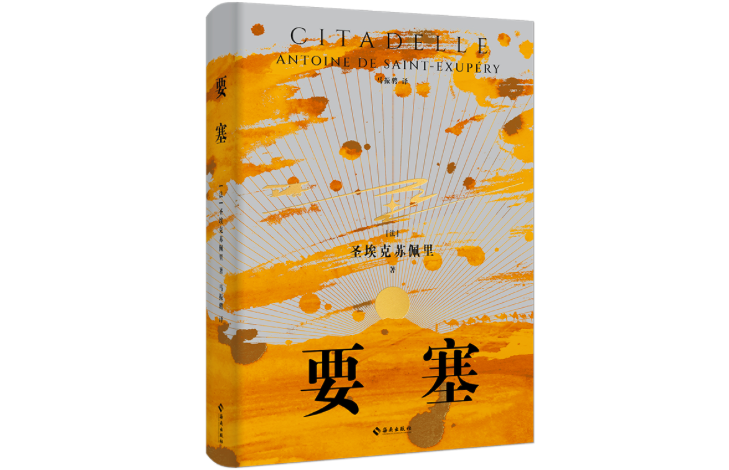
《要塞》,[法]圣埃克苏佩里 著,马振骋 译,海南出版社 2023年5月。
蜡烛的本质是光明
我们生活的空间里,飘浮着各式各样的事物,搬运这些大大小小的事物,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就连搬运这些事物的人本身,也是日常事物的一种。后现代的学者们习惯于以身体来指称人,拒绝接受超出身体之外的保留。这种与先贤闹别扭的态度,意味着取缔人类精神上的诉求,从而把几千年来有关这个范畴的传统视为垃圾加以处理。当人们把自身的存在归结为身体,从身体里长出来的对物的欲望自然成为生命的主宰,肉体狂欢的节日就到来了,形骸的放荡和精神的委靡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状态。然而,谁能说这不是一种以物为信仰的邪教?作为生命当局者,人对生活的见地深深地改变了生活的内涵。如果一个人愿意咎由自取,旁人也无话可说。正如《要塞》中提到的,“那个心中已不再存在帝国的人说‘我从前的热忧是盲目愚蠢的。’当然他说得有道理”,因为“帝国以前是由他的心创造的”。
圣埃克苏佩里没有否定形下事物的存在,但他对存在的探索突破了物质的外壳。在他看来,物的本质并不局限于物的范畴,“本质不是虚饰之物,而是神的智慧。因而蜡烛的本质不是留下残痕的蜡,而是光明”;同样,“树不是种子,也不然后是枝干,然后是弯曲的树干,然后是枯木。决不应该把它分割来看。树,是慢慢伸向天空的力量”。树的这种力量是决不能通过将树锯开来加以认识的,就像蜡烛的光明只能在燃烧中获得,将蜡碾成碎末是找不到的。神庙是由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的,但神庙绝不是那一块块冥顽的石头,它是把石头连接起来,赋予它们特别意义的东西。如果你已经拆掉了高高的神庙,狰狞的石头又算得了什么呢?同样的道理,人的生命并不是骨头、血液、肌肉与内脏的混合物,而是他眼睛里透露出的光芒,是尘土中看不见的东西。“宝藏首先是看不见的,因为它从来不是物质的要素”。
然而,看不见的东西谁能够证明它存在?这是一个古老的困难。于是,人们宁愿在尘土中去寻找,攫取那些粗粝的石头,并且相互炫耀占有的荣光,以此为富足,甚至高高举起石头来威胁和打击对方。他们会对你说:“把家园、帝国或上帝指给我看,因为我看到的、碰到的只是石头和材料,我只相信我碰到的石头和材料。”对于这个问题,圣埃克苏佩里承认:“这里的秘密只可领会无法言传,我决不妄想说了出来会使他信服。同样,我不能背着他上山让他发现一种风景的真理……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盲人看不到眼前的火光,毛毛虫看不到晒在身上的太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而且还不好改变。
多少人在尘土中营建自己的家园,用石头盖起了自家的房子,定居在物质的庇佑之下。对于他们,圣埃克苏佩里一再给予了劝告,希望他们能够迁移出去。因为,定居在以道路、麦田、山冈、绵羊、房屋组成的家中的人,他们的家园必会受到风沙的威胁。他说:“定居的人以为可以太太平平住在自己的家里,这是空想,因为任何人的家都受到威胁。你建在山上的神庙,受到风的袭击而慢慢腐蚀,只剩下像旧船的艏柱,已开始沉没。那一座房屋被沙包围,渐渐占领。不久在它的基础上你将看到一片沙海。”对此,已故的父亲曾深刻地揭示:“这是人的一大神秘。他们失去了本质,还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躺在积蓄上享受的绿洲定居者也不知道。的确,他们失去了什么并不表现在物质的变化上。映在眼前的依然是同样的绵羊、山羊、房屋、山岭,但不再组成一个家园……”
对于尘土中的定居者,对于这些以收集石头为乐的人,圣埃克苏佩里当然不会羡慕,但他也没有怨恨,倒是有些同情。他知道,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太多了,他们的意见由于互相之间的印证和支持而成为坚固的信仰,但他仍然要告诉他们:“重要的东西不显示在尘土中。不要在这些尸骨上花费时间了。”你们这些在“虚饰之物”中讨生活,以为占有就是幸福的人,实际上是赶着骆驼朝一口没有水的枯井前进,你们已经陷入了“沙的阴谋”之中了。已故的父亲曾经对着一口枯井旁边的白骨,教导他的孩子:“你见过宾客和情人离去后的婚庆宴席,晨光照着他们遗留下的满地狼藉,打碎的酒坛,推倒的桌子,熄灭的炉火,这一切保留着喧闹凝结的混乱痕迹。但是看到这些景象,你学不到爱情是什么。”

圣埃克苏佩里。
神圣的纽结
通常,人们之所以以某个地方为家,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居住在这里,所谓住久了就成了家。他们担心迁移之后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除非指出一个新的家园,否则一旦离开熟悉的村庄,迁移者就不胜承受自己的焦虑。但圣埃克苏佩里“怕的是日后他们会毫无乐趣地徜徉在一座空营地里,由于找不到钥匙,让宝藏白白烂掉”。
对于圣埃克苏佩里来说,家与家里的东西或者说家当是不同的,家意味着一个人的出身、一条河流的渊源,没有家的居住实际上是一种流放。
他告诫人们,靠近家园的时刻需要静默地体会,听从神圣的召唤,喧闹、饶舌和自作聪明不利于本质的显现。“要认识一个真理,可能在静默中就可以看见。要认识真理,可能需要永久的静默。我常说树是真实的,这是树的各部位之间的某种关系。然后说到树林,这是树与树之间的某种关系。然后说到家园,这是树、原野和家园的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某种关系。然后说到帝国,这是家园、城市和帝国的其他组成部分的某种关系。然后说到上帝,这是各帝国和世上一切事物之间的一种完美关系。上帝跟树一样真实,虽然更难以阅读。”
圣埃克苏佩里所理解的本源,是把事物连接起来的神圣的纽结,正是这种纽结将散沙一样的事物组织到一起,获得了超出沙子和尘埃的意义。“我的家园不只是这些绵羊、这些田野、这些房屋、这些山岭,而是统率和连接这一切的东西。这是我的爱的王国。他们若知道这点就会幸福,因为他们住在我的家。”至于什么才是这个神圣的纽结,圣埃克苏佩里有时候明白地说是心灵和精神,有时候象征地说是神灵或上帝。在他的文字中,心灵与上帝、家园与帝国是相互贯通的意思。他说,人注入的灵魂才是圣地,这是人的真理,人只通过心灵存在。
同时,又把全身心奉献自己去完成的行动当作是对上帝的祈祷。心灵既可以因对物质的收藏而封闭,如阿里巴巴的山洞;也可以因为爱的给予而向天空和大海敞开,通往神的恩典。它存在于事物本质的领域:“主啊,孤独只是精神不健康引起的结果。精神只住在一个祖国,那就是万物的意义,犹如神庙,它是石头的意义。只有在这个空间里它展翅高飞。它决不会因物而欢乐,但通过物的联系解读其中的面目才会欢乐。”正是那颗从对物质的眷恋中超脱出来的盈满着爱的心,正是人心中神圣的情怀,将生活中的事物,包括生命本身统摄起来,赋予了超出事物和生命的含义,就像水把零散的沙子关联起来,变成了茵茵的绿洲。圣埃克苏佩里请求人们去寻找自己内在的禀性,而不要在禀性之外寻找幸福,因为幸福是心灵品质臻于完美的标记,而不是某种特殊的、稀缺的物质的功能。
人居住下来,事物的意义也随之变化。那些锅碗瓢盆、坛坛罐罐原本有什么意思呢?是主妇的情怀赋予它们特别的情味。还有太阳底下的那些坡地,是农人的愿望改变了它的模样,让它长出了金黄的谷子,扬起闪光的麦穗。当然,圣埃克苏佩里想得最多的还是孩子,他们在庭院里玩耍,变换白石子的阵势,说这是行军,那是牛羊群。但过路的人只是看到石子,不明白他们心中的财富,不知道孩子们已经改变了石子的意义。圣埃克苏佩里还把这个意思加以引申:“没有人爬上山坡,大好的风景也就寂寞空谷,得不到欣赏。如果有人抬着滑竿把你送到山顶,你看到的只是平淡无奇的景物罗列,你怎么会赋予它实质呢?因为对于双臂交叉在胸前深感满意的人,这样的景色是经过努力后气定神闲的享受,在蓝色黄昏中也体现井然有序的满足,因为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在调整山河,推远村庄的砾石路。这个景色起自他的胸臆,我发现他的快乐也是孩子的快乐,他排列了石子,建造了城市,于愿已足。"
这个将日常事物联结起来形成家园的通玄的心灵,圣埃克苏佩里也称之为要塞。它是如此的重要,只要找到它,你就可以救你免于陷入沙的阴谋。一旦失去了这神圣的纽结,事物就散开来,撒入了落寞无边的所在,蜡烛就会熄灭,树木就会枯干,绿洲就会变成荒漠,神庙也就变成了石头,露出狰狞的面目,人也就家破人亡了。而在人生命的过程中,这种危机随时都存在着。人生下来,如同在沙漠中扎下了三角营地,时刻面对着沙尘暴的威胁:“我的帝国危机四伏。它的财富只是山羊、绵羊、房屋和山岭的普通结合,但是如果它们的绳索断了,它们只是一堆零星的物件,听任别人的盗窃。”
世界上的事物,许多是可以或缺的,家里的器具也可以遗失,但这神圣的纽结是须臾不能断开的。“如同高耸入云的教堂,如果没有人欣赏它的全貌,体验它的静默,在静默中得到圣召,那只是一堆石头。”君不见,许多人“他们并不缺少什么,就是缺了连接事物的神圣纽结。于是他们就一切都缺了”。

首领不应该由下属来审判
心灵是人的禀赋,而物质则运行于心的表面。一般来说,在生活中,人缺少某些事物甚至缺少某个器官的情况是存在的,但缺少心灵或精神却难以理解。然而,后一种情形却相当普遍,因为人们不知道生命的根本所在,他们的心灵被物质的重量所吸附,胸臆间堆满了块垒。当他们拥有足够多的石头时,他们就觉得不可一世,以为万事俱备于我;但石头纷纷离他而去,滚入深深的山谷时,他们便难以自持。于是石头成了他们尊严的脊梁,成了他们审判自己的法锤。这种情形,圣埃克苏佩里称之为首领由下属来审判,是没有合法性的行为。因为父亲曾经说过,下贱的人是自身下贱。
一个有着高贵心灵出身的人,不应该在物质面前失去自己的尊严,他可以而且必须搬运石头,但不能因此接受石头的摆弄。或者说,他应该把石头举起来,而不是被石头压下去。在叵测的命运变迁中,一个公主可能有一天会沦为洗衣妇,但沦为洗衣妇的公主依然雍容华贵;一个施舍的人可能会沦为乞丐,但他还是一个慷慨的施舍人。
人依禀赋而高贵,心灵的品质有一种不同于物质的地方,那就是它不能通过偷盗或乞讨而获得。心灵的财富是永远不会失窃的,因此人不必为它设防。偷盗者以为他们可以把别人的金子据为己有,他们想错了,就在他们生起贼心的时刻,金子的品质发生了改变。“金子像星星闪闪发光,这种不可名状的爱只是用在一团他们无法掳掠的亮光上。他们盗窃其他人的财物,从浮光到浮光,就像那个疯子为了捞起井中的月亮,要淘干黑色的井水。他们偷的是无用的尘土,都虚掷在花天酒地的短暂狂欢中。”
能够偷盗来的只是尘土,能够乞讨来的也只是石块。圣埃克苏佩里写道,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怜悯过乞丐和他们的溃疡,给他们延医买药,“直至有一天撞见他们在挠痒,撒上脏物,就像给土地施肥,催开绛红色的花朵,我明白了他们把溃疡像珍宝一样看重。他们骄傲地互相展现身上的疥疮,炫耀得到的施舍,因为乞讨得最多的人,生活不亚于有镇寺之宝的大主教”。现在,他要收回这份感情 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免于损失,而是为了治疗乞丐内心的溃疡。他还说,有一个时期,他还怜悯过死者,以为他们是在绝望的孤独中郁郁而死,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极度伤悲。现在,对于叫女人家心惊肉跳的外伤,垂死和死去的人,他都拒绝给予这种怜悯,还说,“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见过女人惋惜死亡的战士。这是我们欺骗了她们!”被死神选中的那个人,吐血或捂住肠子时顾不得别的,“他独自发现了真理:死亡的恐惧是不存在的。在他看来,自己的躯体已像今后再也用不上的器物,完成服务使命后必须抛弃”,即使濒死时候得到一个解渴的机会,最好还是要摆脱。
圣埃克苏佩里一生在刀刃上行走,有过不止一次濒死的体验,领略过死亡的完美,那是一个人的心灵完全脱离物质桎梏的机会。他这样描写了弥留的状态:“回忆好似潮水涨落,带走了随后又带回了所有积蓄的形象,所有往事的贝壳,所有曾经听到过的声音的海螺。它们把心里的海藻冲上岸来,重新漂洗一番,千情万意再一次涌动。但是昼夜平分时,最后一次退潮,心空了,潮水与积蓄又回归上帝”。父亲的死正是这样。对于完美的死者,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哀悼他们的完成呢一一如果我们坚持不以下属来审判首领的话。当然,圣埃克苏佩里并不怂恿人们杀死自己,他在爱的牺牲与绝望的自杀之间作出了严格的区别:前者是高贵的,后者是庸俗的,“要做出牺牲,必须有一个神,如家园、群体或神庙,它接受了你代表的和与之转换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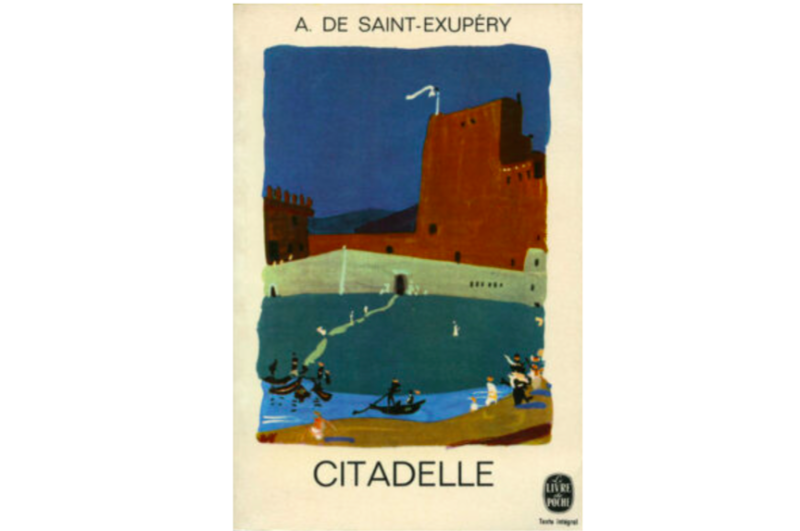
《要塞》书封。
的确,一旦审判关系发生变化,法律的条款内容也会随之更改。圣埃克苏佩里对命运中人人视若洪水猛兽、避之惟恐不及的艰难险阻和凶顽敌人,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甚至表示了隐晦的感激。他将这些负面的逆缘称为帝国内部叛乱的图谋,父亲完美的死亡就是在这种图谋中得以实现,当一个少妇被法官以某种莫须有的罪名,判她脱下衣服,拴在沙漠里的一根木桩上受到太阳的煎熬时,父亲却对他的孩子说,这个女人已经超越了痛苦和害怕,发现了事物的本质。而孩子们也依然相信父亲是仁慈的。之后,父亲还对孩子说:“今夜在帐篷里,你会听到流言蜚语和他们对残酷的斥责。但是叛乱的图谋,我不会让他们说出口:我在锻炼人。”的确,父亲的这些话是不能随便说出口的,说了就变成怂恿。
圣埃克苏佩里宣称,用来接待他朋友的房子,不论建得多宽敞都不嫌大,都会被坐满。“因为我认识世界上的人,即使那个被我砍了头的人,身上总有什么可以成为我的朋友,尽管这部分是那么小,那么容易消失……即使那个对我恨之入骨,要是可能就会砍下我的头的那个人。不要认为这样说是心慈面软,忠厚老实,因为我依然严厉、刚正、沉默。”显然,他对朋友的理解超出了字典上的意思,他的朋友包括了我们所理解的他的敌人。“朋友与敌人是你杜撰的字眼……但是一个人不是由一个字眼所能概括的。我认识的敌人比我的朋友更接近,有的更有益,有的更尊重我……我甚至要说我对敌人比对朋友更易施加影响,因为跟我走同一方向的人,相遇与交流的机会要少于跟我走相反方向的人。”能够彼此受益的皆可以称为朋友,而敌人以他的针锋相对,以他的阴鸷毒辣、诡计多端和不屈不挠对你的弱点和致命之处展开了毫不留情的进攻,帮助你克服自己的缺陷,放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从而成全了你的品性,让你变得更加完美。这是那些和你同穿一条裤子、同睡一个枕头的人不能给予你的。
圣埃克苏佩里告诉我们,那些被人理解、抬举、感谢、奖赏的人才是真正的命苦,他们不久将踌躇满志,俗不可耐,夜里不惜用天上的星星去换取地上的尘土。他不无动情地说:“你若带给我一件珍宝,我愿意它非常脆弱,一阵风就可以从我这里夺走。我喜欢的青春面孔会受到衰老的威胁,我喜欢的微笑会被我一句话轻易化成眼泪。”他在得到一件东西的时候就已经放弃。此所谓得即非得,非得乃是真得。
当人们以心灵来审判身体,而不是以身体来审判心灵时,他们也就克服了对时间的恐惧。物质在时间中消耗,像沙子一样,但精神却在时间中完成一次又一次葡萄的收获。圣埃克苏佩里曾经被萨特引为存在主义的同道,但和众多存在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对死亡有大欢喜。他不把死亡视为生命的断送,而是生命的完成,是天鹅舒展翅膀的时刻。
日转星移,历经艰苦磨砺,肉体的生命日见衰败,但心灵的品性臻于完成,幸福也蕴涵在其间。圣埃克苏佩里这样描述了一个从山上下来的老人内心的慰藉:“我也感到摆脱桎梏的安慰,仿佛这身老骨头在无形中已经转化成了一对翅膀;仿佛我已脱胎换骨,陪伴着长年寻觅的这位天使在散步;仿佛我脱下了那层蜕壳;发现自己异常年轻。这个青春不是来自热情与欲望,而是异常的安详。这个青春是接触到永生的青春,不是迎着朝阳接触到生命喧嚣的青春,它是空间与时间。我觉得终于成长完成后变得永生了。”

圣埃克苏佩里。
我恨定居者
说到家园,人们一般认为是一个定居的地方、一个歇息的场所、一个行动的终点。对于圣埃克苏佩里来说,却没有这样的意思。他说,他要把家建成一条乘风破浪的船,而不是山脚下的一幢房子。因为人的家园并不是物质的形态,而是心灵的禀性。一旦从对物质的依傍和附着中解脱出来,心灵便是最轻爽、最自由、最会飞翔、最有创造力的东西。心灵若附着于物质,就会变得沉郁,并为物质所愚弄;心灵若附着于心灵自身,也会变得枯萎和僵死。圣埃克苏佩里明确表态:“我不喜欢心灵上坐定的人。这些人不转换什么,也什么都不是。”“因为事物的意义不存在于完成后由定居者享受积蓄”,生活的价值并不像金钱一样存入自己的银行户头。因此,当帝国的将军们说“这样好,不用改变!”的时候,国王却发怒:我恨定居者,完成的城市是一座死城。
于是,家园不再是一个囤积粮食的仓库,而是一片耕耘着的田野、造物主的作坊。搬运石头的工作仍然在进行,人在尘土中与事物的交换也还在继续。不过,这些家务活由于服从于某种目的,内涵悄悄地被偷换了,就像神庙门前的石阶不同于荒坡上的顽石。“有了台阶可以进入神庙,这是紧急的事,不然神庙无人光顾。但只有神庙是重要的。人生存下来,在周围找到成长的手段,这是紧急的事。但这里只是说引导到人身边的台阶。我认为注入的灵魂才是圣地,因为只有这才是重要的。”搬运石头的工作由于服务于神庙的建设,具有了超越尘土的意蕴。在《要塞》中,父亲把家园里的劳动描述成一首圣歌:“让他们首先把自己的劳动果实给我送来。让他们把庄稼源源不断倒入我的仓库。让他们把粮仓盖在我的地方。我要他们噼噼啪啪地打麦,打得金光四溅时宣扬我的荣耀。这样打粮食的劳动就变成了圣歌。他们弯腰背着沉重的袋子走向麦垛,或者全身白面往回背的时候,就不是一桩苦役。袋子的重量像一首祈祷使他们崇高。他们快活欢笑,一束麦穗捧在手里像一座枝形烛台,鲜艳夺目……当然这个小麦他们会回来取走,喂养自己,但是对人来说这不是事物重要的方面。滋养他们心灵的不是他们从麦子取走的东西,而是他们给麦子带来的东西。”
圣埃克苏佩里不仅要求在家的人要做家务事,还对家务劳动提出了创造性的要求。他所说的创造,并不是无中生有,造作出原本不存在的东西,而是改变物质的形态。创造的活动就像舞蹈,自然包括跳错的那一个舞步;创造的工作当然也包括了石头上凿坏的那一凿子,因为动作的成功与否不是最主要的。这种对成功与失败的超然,源自于创造者的精神对创造物的逾越,“创造本质上跟创造物是不同的,它摆脱种种标记,把标记抛在身后,又不表现在任何符号中”。创造者不应该落入自己制造的窠臼中,他像炼金术士那样隐退山林。“没有炼金术士的觉悟,生命决不会出现的,炼金术士据我知道是活着的。大家忘了这点,因为他永远从他的创造物中脱身而出了。”创造者在永远的创造中,而不在他的创造物中,一旦在创造物中显山露水,或是企图占有创造物,甚至要在创造物中做窝,他就被物质的力量所俘虏,失去了自由的意志和创造的力量,失去了存在的本质。
圣埃克苏佩里放弃物质依附的心灵要求是那样彻底,哪怕这种物质的形态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也不例外。创造是没有止境的,“我对你说,世上不会有神的大赦,让你不去变化。你愿意不变,那只是在上帝那里。当你慢慢变化,动作僵硬时,他把你收入他的谷仓。因为,你看到,人的诞生是很费时日的。”
他还说,占有带来最大的痛苦,真正的爱开始于你不盼望回报的时候。
撰文/孔见
编辑/李永博 王铭博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