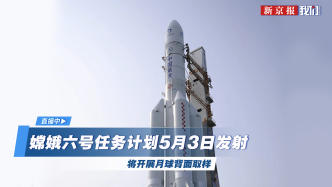8月中下旬,洪水过去了将近一个月,水电路网逐渐畅通,淤泥被清理干净。在外界,关于暴雨洪水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在受灾的山村,源源不断进入的物资,帮助着那里的人们不断地恢复正常的生活。
很少有人注意,如今努力恢复生活的人,还有当初直面灾难的人,大部分都是老人。老龄化、空心村,这些在过去的乡村发展中,反复被人们提起和讨论的概念,在空前的自然灾害中,显现出了它格外脆弱的一面。

8月13日,斋堂镇白虎头村,62岁的村支书宋福强,讲述洪水中救人和灾后恢复的情况。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救人的人,其实同样是老人
塌方的时候是什么声音?砂石混合着泥浆,被洪水冲下山坡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声音?
“有点儿像窜天猴,凄厉,悠长,轻易地穿透暴雨和洪水的轰鸣声,刺进人的耳朵里。”8月14日傍晚,北京门头沟区白虎头村村委会的院子里,62岁的村支书宋福强回忆当初的惊险经历,说话的时候,他的身旁,还有一块未曾清理的巨石。
13天前的凌晨1点多,他和这块石头擦身而过。当时,他刚刚走出村委会,准备叫醒熟睡的村民,转移到高处。他前脚离开,塌方的山石就滚进了村委会,砸塌了一栋小楼,把另外一栋楼砸得千疮百孔。
那天夜里,他和村委会的人们,在大雨和洪水中,转移了46个村民,背出了一位95岁的老人。

8月13日傍晚,斋堂镇白虎头村,村民们正在重修供水管道,他们大多都是村里留守的老人。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洪水之后,人们为劫后余生而庆幸,也为洪水中救人的人们而感动,但很少有人关注,这些救出老人的人,其实自己也是老人。
8月1日凌晨一点多时,雨大得可怕,院子里的水没过了膝盖。在山体塌方的前一刻,他走出村委会,一家一家地拍门,转移了46个人,雨声、水声太大了,光挨家叫门,就花了一个半小时左右。
被转移的人,大部分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年纪最大的98岁。这位98岁的老人,和她60多岁的女儿一起生活,洪水和暴雨肆虐的黑夜中,女儿无法在将母亲带到高处,绝望中一度想要放弃。
暴雨过后,宋福强没有问过那位60多岁的女儿,究竟当时是怎样的绝望。就在转移的当夜,他找人背出了98岁的老人,安置在村里的一家民宿中,那一晚,有46个村民安全转移,没有悲剧发生,没有人员伤亡,不论是对宋福强,还是对所有白虎头村的人,这就够了。他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顾不上复盘那一夜的惊险和得失。
在山村里,50岁还算年轻人
8月13日,门头沟清水镇梁家铺村,70岁的于克俭独自在村委会临时的办公点,领了当天的救灾物资,1桶食用油,4袋面,1包蔬菜,1提瓶装水……
于克俭家离村委会不远,他打算自己把物资扛回家,一趟不行,就多来几趟。包村干部周利军上前帮忙,扛起了面粉和瓶装水,帮于克俭送到家里。
梁家铺村位于百花山脚下,是109国道进入百花山时途经的第一个村庄,被称为百花山下第一村。村庄建在两山之间的沟里,村旁一条小溪,常年有百花山流下来的水。村里还种了中药材、果树等。但风景和新的产业,不足以留住年轻人,村里留守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全村58户人,暴雨前统计的居民只有158人。甚至连村两委成员也都是老人,64岁的村支书梁怀军说,村两委中的干部,最小的一位55岁,其他的,都开始领农村养老金了,“在村里,五十岁还算是年轻人。”

8月13日,清水镇梁家铺村,60岁的张克浦参加完村里的清淤后,回到家里晾晒被洪水泡过的电器。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一个老龄化的村庄,在暴雨和洪水中如何自救?60岁的张克浦,在暴雨中和村干部一起救了6个人,在一户被洪水淹没院子的人家,他们搭着梯子,从后墙翻进去,救出了四口人,又用绳子绑在腰上,把人从被洪水淹没的家里拉出来。
收拾家园,82岁老人也劳动
于克俭一个人居住,洪水之后,孩子们回来帮了几天忙,又回去上班了。家里和院子里二指厚的淤泥,他一个人清理得干干净净,只有地上的一层干燥的浮土,还保留着洪水的痕迹。
洪水过后,村里组织村民展开自救,包村干部、村委会干部,还有志愿者们,一家一家地帮助排水清淤,于克俭清理了自家的淤泥后,又参加了村里的劳动,清理街道淤泥,干了三天。
梁怀军介绍,在梁家铺村,许多老人自愿参加村里的恢复工作,年纪最大的82岁了,“我们不让他干,但他还是干了不少活儿。”
8月14日上午,斋堂镇东胡林村,66岁的刘海柱,和几位同样年老的村民一起,正在梯田中砌墙,洪水过后,梯田之间的矮石墙被冲得七零八落,他们要尽快砌好,才能保证这一小片村民的自留地能够重新恢复生产。就在距离他们几十米的地方,77岁的刘丰民,一个人蹲在地里忙碌,这片不到1分地的小菜园,是他和妻子日常蔬菜的主要来源,洪水过后第三天,他就重新整理了土地,种下了新的种子,如今新的幼苗已经破土而出,和旁边地里倒伏的玉米遥遥相对。

8月14日,斋堂镇东胡林村,66岁的刘海柱正在重砌菜园里的石墙,洪水之中,这些小石墙几乎都被冲垮了。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在整个受灾的山区,不论是清理淤泥,还是整理土地,抑或是收拾家园,村庄里参加劳动的,大部分都是老人,除了参加救援的队伍、志愿者,村里的年轻人,少有长时间回村帮忙的。刘丰民的儿子,曾经想把刘丰民夫妻接到城里居住,但他们拒绝了,他们留在村里,和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同甘苦,儿子则回去上班了,那里也有许多工作等着他。
老年村庄,被灾难放大的困境
空心村,老年村,这些平常反复被人们讨论的乡村发展困境,在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面前,忽然被放大了,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过去关注乡村的老龄化,更多集中在老人缺乏照料、乡村发展缺乏劳动力等方面,但自然灾害来临后,给老龄化的乡村提出了新的问题,老年人如何防灾减灾?”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
自然灾害带来了严重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风险,如何应对风险,减少损失,可能将是这一次灾难之后,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
在梁家铺村,一位老人在转移之后,执意回到家里,想要拿遗落的手机,想要用手机和在外的孩子们联系,村干部们发现后,用绳子绑住他的腰,才从洪水中救出了他。
在雁翅镇淤白村,一位独居的老人,转移后房子被塌方的泥沙压塌,村支书承诺帮她清淤,但短时间内,她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家里。
在妙峰山镇桃园村,60岁的村支书曹振刚,失联后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镇政府通报村里消息。比曹振刚走得更久的,是雁翅镇珠窝村村支书李言生,1963年出生的他,在失联后走了4个多小时的山路,穿过洪水漫溢的山洞和铁路,走到镇政府通报消息……

8月2日,60岁的妙峰山镇桃园村支书曹振刚(左),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镇政府通报消息。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没有年轻人可派,村委会干部年纪都很大了。”曹振刚说。
“不论是救人,还是报信,抑或是灾后的恢复,缺乏年轻劳动力的乡村,都要面临许多难以想象的困境,”朱启臻说,“最直观的困难是,如果老人不愿意走或无法行动,协助他们转移避险,就是一个非常吃力且危险的工作。”
灾后重建,还会需要多少时间
洪水过后两三天,梁家铺村的村干部和包村干部们,几乎都没有睡觉。人员安置、餐饮保障、和外界打通消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庞大的工作量,都需要克服无数困难。
包村干部周利军和村支书梁怀军两个人开一辆四驱车,平时10多分钟的路程,两个人开了两个多小时,中途还弃车步行,才到达镇政府,即便如此,他们村也是第一个到达镇政府报告情况的村子。洪水退后的第二天,他们村里就通过后山的泉水,解决了吃水问题,也是清水镇第一个通水的村庄。
即便如此,村里的恢复和重建,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到8月13日,在有救援队伍帮助的情况下,村里的淤泥仍没有清理干净。村民们的家里,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张克浦的家里,淤泥已经清理结束,院子里晾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家具、电器,从柜子到桌子,从吹风机到电视机,“进水的屋子,这一冬天不能住人了。”他说。
从暴雨预警开始,周利军几乎都呆在村里,和村里所有的人一起,经历了转移、救援、安置、恢复的全过程,也经历了失联到复联的艰难历程。
在白虎头村,村委会倒塌的房屋,洪水留下的淤泥,也是最晚清理的,一直到8月14日,砸塌村委会的大石头,还留在院子里。
对62岁的宋福强来说,每一刻都有新的事情要做,都有新的问题出现。从2007年当选村支书,16年中,他和这个村里的老人们,把一个欠了几十万外债的凋敝小村,变成了远近知名的旅游村,村里的每一家民宿、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景观、每一块农田,都是他们一点点重新打造的。在灾难到来前,村庄正处在旅游的旺季,许多外地的游客都慕名而来,村里老人居多,无法承担过于沉重的劳动,但足以为游客提供良好的住宿和餐饮服务。
洪水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老人们放下毛巾和锅铲,拿起铁锹和镐头,清理淤泥,整理村庄、重新埋设管道……干起超出他们身体负荷的工作。
外部力量,是灾后重建的主力
随着道路的打通,更多的物资在不断进入受灾村庄,在梁家铺,每天都有至少一次外部的物资运送进村,在白虎头、东胡林等众多村庄同样如此。
尽管在救灾和恢复中,村民们一直在积极自救自助,但来自外部的帮助,仍然是应对灾难最主要的力量。
“在应对灾难时,村干部、包村干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周利军说,“村庄老龄化、空心化的同时,也意味着村庄体量的变小,老人多,但总人数并不多,因此包村干部和村干部的力量得以体现。”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受灾的村庄中,数百人的村庄,即可算作是大村,在深山区,人口稀少的小村庄占据绝大多数,最小的村庄,只有二三十个常住人口,“利用政府和村党支部的力量,弥补村庄老龄化的缺陷,是这次灾难中普遍展现出来的特点,”周利军说,“在这次灾难中,我们看到了基层党支部的强大力量,有村支书在洪水中救了一个小女孩,也有村支书带领村干部,打破院墙,救出了困在院子里的村民。”
村庄的灾后恢复同样如此,在村里,许多老年人参与劳动,排水清淤,但同时,外部的救援和支援力量,成为恢复村庄的主体。
“梁家铺在洪水后的第二天就接通了山泉水,这是我们村里自己动手解决的。同时,政府也在帮助修复自来水管道,到8月中旬左右,自来水就恢复了。”梁怀军介绍。
对于村庄的恢复和重建,周利军持乐观的态度,“灾后的恢复和重建,更多的力量来自全区乃至全市的力量,相信会在短时间内有比较明显的成效。”
来自外部的强力救援和帮助,缓解了村庄老龄化的困境,但这样的帮助是否可以持续,在灾难之后,引起了更多村民的思考和讨论,尤其是对村庄来说,漫长的恢复和重建,将严重考验自身的发展潜力。
村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历程
把一个一穷二白、欠着外债的村庄,发展成为远近知名的旅游村,白虎头村支书宋福强用了16年。16年中,他也从一个46岁的年轻村干部,变成了一个62岁的老人。
洪水之后,宋福强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几天,他忙于各种工作,几乎无暇休息,到后来,繁杂的恢复工作和村庄巨大的损失,总会让他恍惚失神,有时候到了晚上,清淤的工人们下班休息后,他还会久久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工地”上。村里的老人们会变得越来越老,而年轻人却不会增加,他不知道这个村庄还会不会有下一个16年。

8月13日,斋堂镇白虎头村村民王文革,在村里清理了一天淤泥后,正准备回家,洪水中,他带着12个人爬山避险,12人中有老人也有孩子。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在梁家铺村,村里集体种植的中药材,在洪水中受灾严重,而是否能恢复也仍未可知。
“老龄化的村庄,产业的发展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这可能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在遭遇罕见的灾难破坏后,恢复和重建可能会更难,这是政府力量很难解决的。”周利军说。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灾后,为什么年轻人回来的少?
“如果年轻人普遍参与,灾后的恢复和重建会更快,这是毫无疑问的,”朱启臻说,“但目前看,这不太现实。”
对外出多年的年轻人来说,村庄是老家,但并不是安身立命之所,他们和村庄的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薄弱,“城市化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使得年轻人离开村庄和土地。同时,乡村的发展中,农民的主体地位难以保障,也使得许多人不再认为自己是村庄发展的主导者。包括村庄的许多日常事务,如清洁、修路、建设等,都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实现的,村民对政府的依赖性正在变得更强,所以在灾难之后,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恢复和重建不是他们的事情,而是政府的工作。”朱启臻说,“其实最终还是落到了一个老问题上,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真正成为村庄的主人,在村庄的建设和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利益,让他们可以在村庄里安身立命,这才能让村庄有更强大的力量,面对和战胜自然灾害。”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