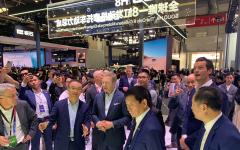2023年8月16日,尚珩站在长城上。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北京文化守护人尚珩,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长城专家,长期致力于长城研究、保护、宣传工作。过去20多年徒步考察北京、河北、天津、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长城,行程超过3000公里。他先后主持延庆柳沟长城遗址、延庆大庄科长城遗址等多项长城考古发掘工作,完成“中国历代长城研究”“明代蓟镇长城防御体系考古学研究”等研究项目。

8月16日,大雨过后,长城砖块上还残留着湿气。时隔半月,尚珩再次踏上延庆长城60-64号敌台及边墙考古现场。尚未保护修缮的长城墙体上的砖块残破无序,周围没有护栏,陡坡处的沙石砖块极易滑落,但尚珩走得飞快,步履稳健。他边走,边用双眼一一扫过每一个长城砖块,“青苔、小草都从缝隙中长出来了。”
尚珩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长期从事长城基础研究工作,不仅徒步考察过全国多地的明长城,还参与过全国长城资源调查暨山西长城资源调查项目,多次主持长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撰写有关长城的研究文章。
从7岁时第一次登上八达岭开始,尚珩便爱上了长城。他徒步考察了北京、河北、天津、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长城,行程超过3000公里,感受过长城的朝暮和四时,也见过了沙漠、海边、高山和平原之上的长城。在他眼里,长城就像一条巨龙,蜿蜒在中华大地上。
然而尚珩最爱的还是长城的田野考古现场。四百多年过去了,自然山脉没有太大的变化。当发现一个炕、一个棋盘、一粒花椒、一个因常年蹬爬而留下的凹陷处,尚珩宛如置身四百多年前,看到了边关战士的生活画卷,长城也在眼前活了起来。

2021年冬天,在延长城考古时,尚珩查看出土的石碑。受访者供图
长城与少年
尚珩仍然记得第一次登上长城的情景。
1991年,7岁的尚珩来到八达岭长城。城墙在山林间蜿蜒曲折,他一口气走到八达岭长城的北八楼,可放眼望去,仍然望不到尽头。正是此行,让尚珩对长城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祖父的带领下,陆续走完居庸关、司马台、黄花城、黄草梁等长城。
1999年,15岁的尚珩第一次抵达“野长城”。在景区以外的长城段,他从天亮走到天黑。在延绵不断的长城线路上,尚珩随家人从古北口走到金山岭,再走到司马台,整整走了三天,晚上就在附近的村民家借宿。
尚珩开始对长城的一砖一瓦产生好奇:这座建筑为什么建在这个位置?它为什么呈现这样的形状?它的用途是什么?从此以后,研究长城成了他的业余爱好,一有机会,他就从书籍和报纸上搜罗有关长城的各种信息。
2001年,尚珩从黄草梁长城回来之后,写了一篇游记打算发上网,却无意间发现了“长城小站”,一个由志愿者自发组建并运营的公益性网站,虽然网站还保留着20世纪末的页面风格,但里面大量关于长城的图文资料吸引了尚珩。
在“长城小站”,尚珩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虽然他们中大部分人是理工科背景,但是共同的爱好将大家聚集在一起,一群人沿着长城走走停停,途经残破砖墙、碎石土堆,每一程都让尚珩流连忘返。
至今,尚珩都没有停下探索长城沿线的脚步,即便工作繁忙,每个月他仍会抽时间和朋友们相约去徒步长城。如今,他已徒步考察了北京、河北、天津、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长城,行程超过3000公里。
“我特别喜欢和外专业的同学一起爬长城,大家从各自专业的视角解读长城,彼此交流碰撞,思维更加发散。”尚珩记得,比如长城里是否含有糯米浆的问题,化学系的同学就曾提出质疑,“万里长城那么长,需要耗费多少糯米浆呢,当时的物资保障跟得上吗?”

2023年8月16日,北京,尚珩走在长城上。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走上长城
受家庭熏陶,尚珩自小便喜爱历史。他早已明确自己未来的方向,到了大学要学习考古专业。尚珩想通过实物,去真正体会文献中寥寥几笔带过的历史。
也正是从大学时起,尚珩开始系统性阅读与长城有关的文献,也开始系统地徒步考察长城。
背着帐篷和睡袋,尚珩和朋友们一走就是一整天。太阳下山了,尚珩还眼巴巴地看着远方的长城,“就像追剧一样,总想往前多走一段。”由于交通不便,又没有攻略可以参考,只能趁节假日包车前往,扎营两晚后,就得下山寻找补给。到了2006年,尚珩和朋友们基本走完了河北东部到北京平谷一带的长城。
常年徒步行走野长城,尚珩的身上留下了不少伤痕,皮肤被尖锐的树枝划伤,多次摔跤留下疤痕。
他还曾遇到过危险。北京密云段长城山高林密,山路陡峭险峻,非常难走。2007年初冬的晚上,尚珩和朋友们徒步走下长城,由于天黑看不清山路,他从十米高的山崖上摔了下去,朋友们一转眼就看不到尚珩了,把他们吓坏了。幸而下方是一个铺满落叶的土坑,有了树叶的缓冲,尚珩才没有受伤。2009年,爬密云段长城时,尚珩还曾和两位朋友被困山上,夜晚天凉,三个人只能坐在一块石头上,互相紧抱着对方取暖,忍了一宿。
2007年,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开始启动。彼时,尚珩正在山西大学读研究生,他参与了山西长城的调查工作。
山西长城上,形态各异的烽火台让尚珩大开眼界,“有的呈圆形,周围有一圈围院,像个小院子。”在那里,烽火台的分布、烽火传递的路线,都可以精准地呈现在一张地图上,尚珩说,这得益于山西长城烽火台保存完好。而此前在北京考察明长城时,尚珩总是沿着长城的墙体徒步,觉得烽火台是长城的附属设施,于是经常忽视烽火台。
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跟着调查组走遍了山西省十几个县,途经800多座烽火台,逐渐熟悉了长城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更加关注长城的细节、设施。
尚珩也因此发现长城保护的不易。据他介绍,那次的长城资源调查,实际上是一个摸家底的管理行为,如若出现遗漏,日后的保护就非常困难。在当时的调查中,队员们曾漏掉一个烽火台。2009年当地修高速公路,施工人员看长城数据库里没有它,就将其拆掉。
“体量太大,分布太广了”,尚珩举例说,长城不像故宫,并非一个集中的院子,长城散落在中国各地,而且常年在户外经受风吹日晒,随着时间推移,有的已经成了残破城墙,甚至是土堆,沿线的老百姓不知道这是什么,很难产生保护的意识。

2023年8月16日,尚珩在察看长城。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让长城更有“温度”
2018年,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工作了八年之后,尚珩终于把“研究长城”的业余爱好变成了职业,开始专职从事长城的考古工作。
此后的五年里,尚珩先后主持了延庆岔道城遗址、大庄科长城遗址、怀柔箭扣长城遗址等多项长城考古发掘工作,完成“中国历代长城研究”“明代蓟镇长城防御体系考古学研究”“山西长城碑刻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等研究项目。
在尚珩看来,考古能让长城变得更有“温度”。
2018年,在延庆岔道城遗址1-6号烽火台及边墙遗址项目中,考古人员先是发现了一个土墩,顶高五六米,由砖石包砌。后来又找到了一块长条石头,顶部有两个钩子,中间有一段凹槽。之后,在张家口境内的长城,他们又发现了类似的石头,依旧是竖立在原始位置上。
有些人很不解,那段凹槽究竟如何产生?
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在文献中只有一句话,即“以绳梯上下”。尚珩恍然大悟,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戍边士兵接二连三地爬上石梯,双手紧扶麻绳,双脚用力前蹬,最终攀登到土墩顶部。长时间的踩踏后,石壁上渐渐形成了凹槽。
同年,考古队在怀柔箭扣长城发掘了五座敌台。其中四座敌台的顶部,都出现了火炕和灶址等生活设施遗迹。
考古挖掘后,长城的后期堆积物被清理干净。尚珩脚踩在明朝人垒砌长城城墙的石块上,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看到400多年前,士兵在此戍守、吃饭、爬上炕、睡觉……古代边疆社会的生活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未知的东西太多了,长城总是能给人惊喜。”尚珩有时感叹,做了长城考古之后,反而好像越来越不认识长城了,2022年,尚珩在延庆区庄科乡香屯村境内,主持大庄科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前期考古工作。考古队在一片黑色的碳化物中,发现了意料之物——黍、粟和一粒花椒。经过C14测年确认,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遗物。
“我既惊喜又好奇:古人如何把花椒用作调味料呢?然后联想到现在延庆长城沿线的美食‘火勺’,想象着古人在敌楼里吃着‘火勺’,里面夹着花椒碎末。这是多么富有生活气息的画面啊。”尚珩感叹。
“长城不是冰冷的建筑,而是有血有肉的。”尚珩说,他曾发现,有人提到长城时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因为觉得长城充满杀气。然而实际上,长期从事长城研究的尚珩知道,人们常去的长城,由于距离关口较远,战事并不多。在这里发生的更多场景,其实是戍边士兵拖家带口,在长城沿线安家,驻守着一片国土。
8月16日,尚珩又来到延庆长城60-64号敌台的考古现场。石雷在城墙边整齐摆放,沿着长城上凌乱的残砖往上走,还能看到数百年前人们睡觉的炕。
在前期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发掘出了300多枚石雷。如此大规模的石雷出土,尚珩还是首次看到。“1个石雷20-30斤重,100个石雷就能堆一面墙,我们以往从文献里知道有石雷,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也不知道放在哪里。这次300多个石雷,到底堆放在哪儿?”
数百年过去,石雷摆放的位置,变成了一个登山步道。尚珩笑道,“路过的人一定没想到脚下踩着这么多石雷。”

2023年8月16日,尚珩(右)和助手察看出土的石雷。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长城保护是所有人的事”
过去,长城被考古发掘后,往往要等上1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才能得到修缮。在这段“空当期”内,长城免不了要经受风吹日晒、狂风暴雨的洗礼。尚珩说,“考古发掘后,长城土层、植被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如若得不到及时修缮,可能面临坍塌的危险。”
而此次的延庆长城60-64号敌台考古项目,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施工空当期,实现了“前期考古”和“后期修缮”的无缝衔接。“我们赶在北京140年来最大的暴雨来临之前,完成了64号敌台的所有项目,保护了长城的安全。”这是尚珩参与的一种新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值得在以后的考古工作中大力推广。
在尚珩看来,长城研究和保护已经是一个多学科甚至全学科的范畴。如今,他与古建、材料、植物学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合作,以更加科学、专业的方法保护和修缮长城。
这些年的工作中,尚珩见证了长城保护修缮理念的更新和进步。
2022年启动的怀柔箭扣长城和延庆大庄科长城研究性修缮试点工程中,首次引入了考古发掘,向“慢慢修长城,边研究边修缮”的长城保护修缮新模式迈进。这是国家文物局首次批复的两个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之一,即在长城保护项目施工前先考古。
“我们以往只是在地面上观察长城。至于掩埋在地下的部分,只能依据工作经验来判断,这样往往不可靠。”尚珩说,“考古环节的纳入,对于长城被掩埋的部分、隐蔽的部位进行了勘察,找到了长城病害的根源,研究性修缮方案的制定更加全面、具体、科学。”
尚珩认为,在修缮中引入考古环节,修缮方案保护的对象也会更丰富。2022年,箭扣长城141-145号敌台的考古发掘项目中,他们就在敌台的顶部发现了火炕和灶址。“发现火炕后,我们的研究性修缮方案也做出了变更,要考虑如何将火炕保留下来。”尚珩说,“如果没有考古环节,这些火炕就被清理掉了。”
如今在尚珩眼中,长城仍然是新鲜的。
从山海关至北京的长城,尚珩即将走完第二遍了。一样的砖块道路,一样的沿线山林,然而早晨和傍晚,顺光和逆光,都呈现了不同的景象。长城像有魔力一般,吸引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探索。
“像巨龙一样,长城就这样蜿蜒在中华大地上,穿越漫漫戈壁,跨越崇山峻岭,蜿蜒入海……”由于长城跨度大、地理环境复杂、沿线人类活动复杂,尚珩越走,越担忧长城的保护问题。
“过冬”就是一个仍需解决的大难题。每到冬季,长城沿线冻融灾害频发。随着气温的升降,土层水分融化又冻结,反复多次后,长城墙体松散。“我们没法给长城扣罩子,也没法给长城安装暖气。”长城跨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多样,安装的难度非常大。尚珩举例说,箭扣长城地势起伏陡峭,地势险要,运输材料困难重重;到了沙漠地带的长城,材料、设备很可能被沙土掩埋。
尚珩说,受时间、精力、人员等客观条件的限制,长城保护的历史欠债很多。过去十多年,河北、山西等地的长城大都处于自然状态,保护措施基本缺位。十多年前,尚珩曾经走过的长城,部分已经塌陷、损毁了。一部分长城上的文物也遗失了。20年前,尚珩在爬长城时发现了一座石碑。5年前,他再次回到原先地点,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座石碑了,“可能被人偷走了。”
尚珩认为,要保护长城,需要的是所有人的力量。
除了考古工作之外,尚珩还一直在长城沿线奔波忙碌着,向沿线学校的孩子做宣讲,为基层的长城保护员做培训。长城保护员大多数是生活在长城沿线的普通村民,文化教育水平不高。村民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长城保护的知识,尚珩就给他们培训“充电”。如何巡查,发现破坏怎么办,他都会一一传授给村民。
“长城生病了,村民是第一个知道的。”尚珩深信,沿线村民能够成为长城保护的一线力量。有些村民不会拍照,尚珩就一步一步地教。“巡查时要拍三张照片:第一张,拍完整的长城;第二张,拍敌楼;第三张,拍长城的裂缝。”
尚珩发现,这些年来,在平谷、怀柔、密云、延庆等北京长城沿线地区,村民保护长城的热情高涨。
“长城保护员培训到位后,就是基层文保部门的眼睛和手。”尚珩期待着,有朝一日等长城点段开放得越来越多,村民们就地当起长城讲解员,带领游客游览长城原址,介绍石雷、火炕等考古发掘成果,带着人们走进数百年前人类在长城生活的画卷,“这是祖先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新京报记者 汪畅 实习生 邹冰倩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