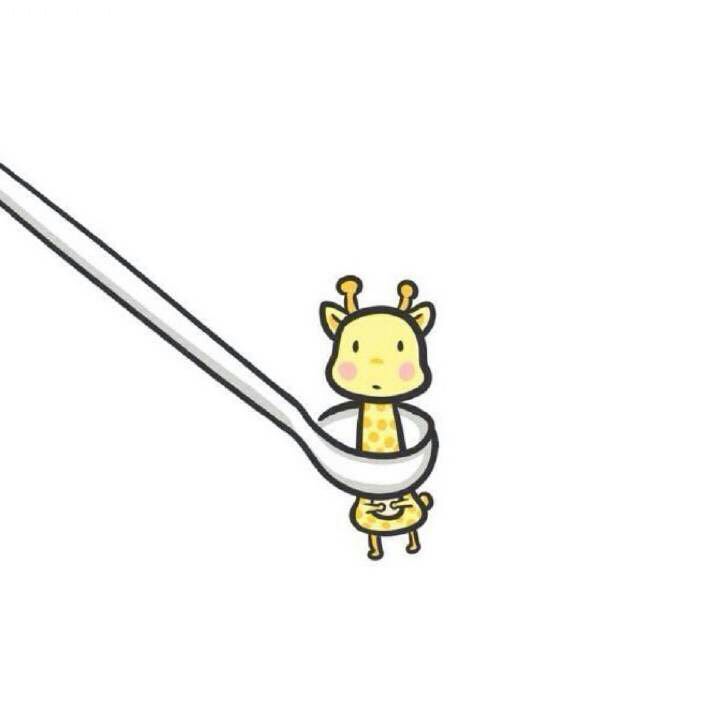Lisa作为一个演艺偶像,不仅是美丽、元气、自信的代表,也符合大家对新时代女性形象的期待:强大、独立、自信。她不仅以外国人身份在竞争激烈的韩国娱乐圈站稳脚跟,而且在国际上更是势不可挡,这完全是一个“大女主”故事。
与此同时,疯马秀却透露出过时的厌女,它是成立于1951年的法国艳舞团疯马俱乐部的表演节目,以裸舞秀著称。舞者在奇幻神秘的灯光和配乐下,以接近全裸或全裸状态出演。
当“大女主”之典范Lisa与性物化女性的“脱衣舞表演”交叠在一起,引发争议是一种必然。
Lisa的疯马秀:危险还是快乐?
一直以来,Lisa呈现形象都是韩国流行音乐(Kpop) 中Girl Crush(暂译,女孩的爱)世代的典范。“Girl Crush”被用于描述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风格或者才华的欣赏,这种欣赏无关浪漫。“Girl Crush偶像”是指那些能够激发女性粉丝的仰慕和欣赏的女性偶像。她们通常自信,强大,甚至有些“坏”,在舞台上展现帅气和自信,多维地打破了传统女性形象。
正是由于这样的形象,对于Lisa参演疯马秀,一部分女性感受到了冒犯和背刺。以“强势”“女性力量”著称的Lisa决定去物化女性的场所表演,她巨大的影响力——Instragram(社交媒体)上亿的关注,使其个人选择迅速演化为一场事件:获得如此成就的女偶像本该展现更强的女性力量,但她还是选择讨好男性凝视。长远来看,这将在象征层面加剧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剥削和性物化,这部分女性从Lisa的选择中嗅到了女性遭遇性剥削的危险。

图片音乐纪录片《#OUTNOW Unlimited: LISA》 剧照。
与之相反,另一部分女性则强调尊重个人的选择和权利,同时尊重女性之美与脱衣舞表演的艺术性。如果说女权主义的目标是为了让女性拥有更多自主权,肯定女性价值,扩大女性的行动空间,那么女权主义者理应尊重Lisa的选择。她们从事件中嗅到了女性自我决定性感的快乐。
矛盾的双方陷入日益激烈的交锋,她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指责对方“不够女权”,这么一来,理解成为一种奢望,大家甚至失去了对话的前提。

2019年的疯马秀演出,图源:ic photo
我们的女权主义发展在当下网络环境中所展现出的混乱与挣扎,其他国家早有前车之鉴。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内部产生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性论战”,该论战以1982年的“巴纳德会议”为节点,“色情问题”是该会议的焦点之一。在凯瑟琳·A·麦金农与安德里亚·德沃金共同撰写的《反色情制品的民权法案》(1980)中,色情被定义为“在图像或文字中,(包含)图例性且性露骨的女性屈从”。参与论战的双方分别是“性激进派女权主义”(sex radical feminism)与“反色情派支配论女权主义”(dominance feminism)。前者提倡性解放,认为这是女性自由和自主的体现,反对苛责那些享受性感和性爱的女性。后者则坚持性解放实际上在鼓励男性特权的扩张。

Pleasure and Danger,作者: Carole S. Vance,版本: Pandora Press,1993年1月。
巴纳德会议的文集《危险与快乐:迈向性政治》奠定了女权问题内“性激进派”和“反色情派”的争论框架,这些争论在我们当下的网络语境中反复呈现,却未得到整体的认知和反思。比如,在#MeToo运动中,“谈性色变”的文化环境,使女权主义对“性骚扰”问题的分析与界定的默认前提是“反色情派”立场。这造成了一种不允许对性骚扰的判定进行质疑和反思的环境。[1]还有在关于鉴定“擦边”、“媚男”、“正统女权”等造成割席的争论中,“反色情派”已然成为某种“监禁女权主义”(Carceral feminism),不由分说对展现性感的女性进行扑杀。
然而,与其纠结谁更女权,不如将注意力放在虽被双方忽视却可能实现的合作之上:女性能否通过参与某一传统上压迫女性(性剥削)的行当,从而颠覆这一行当,实现女性空间的扩大?这个问题无法简单作答。不过在面对Lisa疯马秀表演时,我们至少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脱衣舞表演是否使Lisa或女性整体处于屈从于男性的地位?二是脱衣舞表演是否会对“女性是什么”予以不良的影响?
厌女表演的意义能否改变?
现代意义上的脱衣舞表演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它“是一种通常带有性暗示、勾引与性刺激的舞蹈,舞者会在演出中逐渐褪下衣物”。大多数人会承认,“脱衣舞”引发的是肉欲横陈的想象:性感尤物与炽热的欲望。它和AV一样,虽然也存在服务于女性的AV,但两性受众不成比例的市场,使其很难不被看作是针对女性身体的剥削和物化。然而,在我们对脱衣舞进行一种本质主义式的定义之前,不如以开放的视角考察脱衣舞等色情产业的含义,它们注定厌女吗?其文化意义可能改变吗?若可能,需要什么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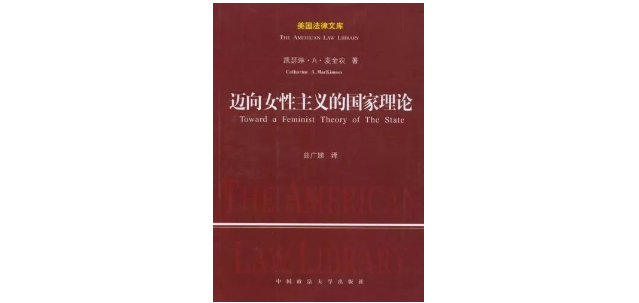
《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美]凯瑟琳·麦金农 著,曲广娣 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按照麦金农的说法,在色情制品对屈辱女性形象的生产、流通和再生产过程中,女性的自我表达失去了意义:她的“痛苦”被解读为“享受”,“不要”被解释为“要”。甚至有女性接受了这种自我物化,以满足男性的欲望为自己的欲望。结果就是女性失去了表达自我真实感受的可能性。但这一切都必然如此吗?

《日本AV影像史》,[日]藤木TDC 著,陈涤/阮航 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8月。
在《日本AV影像史》中记录了试图改革男性欲望结构的AV女优黑木香的事迹。黑木香在面对男优具有暴力虐待倾向的前戏时,呈现出一种疯狂的欲求方式,在她激烈和粗暴回应中,营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滑稽与疯狂混杂的气氛。书中写道:“对当时的男性而言,黑木香的反应是冲击性的,甚至令人恐惧。黑木香的口头表达能力也很了得,能坦然地用语言重现自己当时的反应。通过她的语言描述,大众理解到,她的这种性能力并非源自特殊的体质或野性的神秘,而是一个理性的人的谋生手段。”由此能看出,黑木香在AV表演中,不仅开创了一种源于女性的“令男人恐惧”且“去神秘化”的欲望表达方式,而且她对自己的表现具有充分的把握,能面对公众进行清晰生动的描述,并借此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么看来,即便不能说黑木香具有女性主义意识,她作为女性也展现了充分的自主意识。
另一个例子展现在讲述上海名妓如何影响“近代新女性形象形成”的《上海,爱》一书中。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从事娼妓行业的女性往往最早适应现代化的公共生活。妓女由于她们的边缘性,反而获得良家妇女所没有的“特权”——公然违抗和破坏传统的社会准则。没有道德包袱的上海名妓,不仅以女性身份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大胆涉猎时尚、金融等现代产品,而且借助大众文学、都市小报等媒体,提升自己曝光度。在此过程中,又与创作小说、小报的文人结盟,共同获得和经营社会文化资本。这一切都客观推进了社会中新女性意识的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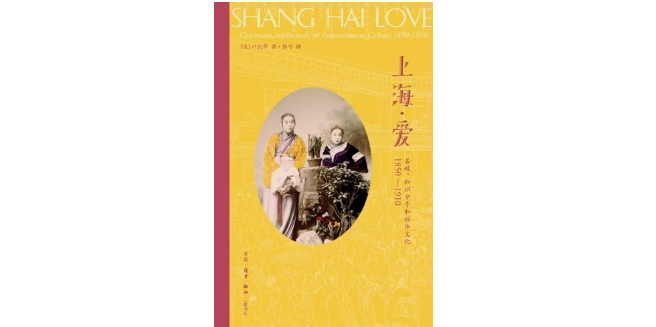
《上海,爱》,[美]叶凯蒂 著,杨可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1月。
然而这些“进步”雾霭沉沉。名妓的风光以其低微鄙夷的地位为前提,她们本人的行事作风也一定尾随着民众的期待,迎合着恩客的欲望。也就是说,名妓即便拥有部分的自主意识,也不太可能是内心自由行动无阻的新女性,这一局限阻碍了她们对社会中女性意识觉醒的推进。黑木香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她虽然清醒地开创了一种风格,但既然AV是她的“谋生手段”,那么她也无法单枪匹马地逃脱该产业的限制——她被类型化为“本番淫乱”,并被再次整合进入男性凝视的结构之中,作为宣泄欲望的商品。
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中对“情色资本”的质问同样适用于此:拥有情色资本的女性,真的能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身体吗?黑木香在AV中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欲望吗?上海名妓真的在公共空间中“自由”穿梭吗?女脱衣舞者真的能不受干扰地决定自己如何裸露,展现性感吗?
脱衣舞之变:女性自我表达之力
虽然像黑木香一样单纯依靠个体影响力,或像上海名妓一样依靠某个历史阶段所赋予的机遇,或像Lisa未经反思地选择脱衣舞表演进行自我取悦的表达,都无法对传统上的厌女的行当进行根本的解放和改革,但不能忽视她们带来的积极影响:扩张了女性的象征空间或者物理空间。进一步的反思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表达以打破刻板印象,强化女性的自主思想?
女性的自我表达,一方面包括女性对自我感受、经历和欲望的偏好性自发表达,另一方面则是女性有意识、讲策略地在公共领域内对女性视角进行自觉的构建。Lisa参与疯马秀的不合时宜之处是,她对公共场域中的自我表达缺乏反思。首先,她对自己所参与的脱衣舞表演本已具有的刻板印象缺乏把握;其次,她对自己参与脱衣舞表演的象征性缺乏反思。作为在全球范围的现象级女性偶像以及girl crush(暂译,女孩的爱)的代表,在对待与女性意识相关的事件时,她理应更敏锐。
Lisa或许能够通过脱衣舞展现她的自由和热爱,但仅凭舞蹈本身,无法颠覆脱衣舞对女性屈从形象的刻板印象。或许当Lisa在有厌女争议的领域内展现“女性力量”时,需要通过更多更深的表达来强化自己的表达。比如借助MV、影视作品等,甚至是公共媒体上的自我剖白,补充更多语境,来为女性表达生产新的诠释资源,也在公共语料库中扩充有关女性经验的丰富、精确的话语,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女性视角。

Neo-Burlesque,Lynn Sally 著,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21年1月。
林恩·萨莉(Lynn Sally)的作品《新派滑稽秀:脱衣舞之变》为我们提供了多种重构脱衣舞的文化刻板印象的方式。林恩·萨莉明确表达了,作为剥削女性之象征的脱衣舞,能够作为一种赋权工具,服务于女权主义。[2]通过滑稽秀的“戏仿”,性积极主义女权主义(sex positive feminism)对父权制进行模仿和嘲讽,这既巧妙地破坏了女性的被操控的形象——表演者主动挑战程式化性感化的女性形象,又颠覆了女性的被凝视位置——表演者能够控制自己的形象和观众的目光,观众无法进行侵略性的观看,观众是“被允许”观看。新派滑稽秀式的脱衣舞表演,将女性身体的展露强调为一个延伸的过程而非曝光的过程,她们在主动展露女性的世界。叙事弧线的张力使观众不断被吸入表演者的世界和故事之中。总之,滑稽秀式脱衣舞以更灵活有趣的方式,全方位地挑战了霸权叙事,不仅是父权制的霸权,也包含传统女权主义叙事的霸权。这些理论假设并非空中楼阁,实际上,疯马秀近年来就越来越重视女性受众,试图扭转自己的定位,强调其作为一种身体艺术的审美面向。这背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趋势,即将“为满足男性欲望而贩卖女性身体”的观念转变为“女性身体的解放和自我欣赏”。虽然这可能只是一种策略,也无法免除再度被父权制收编的风险,但这种转变的尝试仍有值得鼓励之处。
最后,希望“不要打着女权的旗号压迫女性”成为一种常识。Lisa疯马秀的争论至少能够提醒我们,女权主义内部本就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立场、判断、争论正是其批判的活力所在,争论虽可能造成女性主义内部的分化,但也可能带来新的启发。
值得关注的还有,这次的交战不再是“国蝻”与“女拳”这种敌意的、对立先于真诚立场的沟通情况,而是女性主义内部,不同立场的真诚交锋。那么,希望这次的争议能带领我们去构建交流与合作的义理之争,而非导致“姐妹情谊”破裂和女权立场固化的意气之争。女权主义期待的,本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多元世界,而不是生产出一组组新的对立,制造女性群体内部的相互割席。
本文注释:
[1]黄盈盈,张育智,女权主义的性论述,社会学评论,第6卷,第6期,2018年。
[2] Sally, Lynn. Neo-Burlesque: Striptease as Transformation, Ithaca, N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22
作者/陈明哲
编辑/走走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