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埃及博物馆是开罗埃及文物藏品的第五个家。首批文物展出于1835年,地点位于开罗市中心的阿兹巴基亚公园(Azbakiya Gardens)。随后,它们被重新安放在萨拉丁城堡(Saladin’s Citadel)的展厅内。1855年,埃及总督赛义德(Khedive Said Pasha)将这批馆藏作为礼物赠与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法国埃及学家奥古斯特·马里耶特在尼罗河岸边的布拉克(Bulaq)展出了第三批藏品。1878年,尼罗河洪水威胁到了布拉克的展馆和文物,它们又被搬迁至第四个地点,位于吉萨(Giza)的伊斯梅尔(Ismail)总督行宫的一座附属建筑内。
1902年11月15日,在总督阿拔斯·希尔米(Abbas Helmi)的统治时期,现在位于解放广场的博物馆在加斯东·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的指挥下竣工。最初博物馆的藏品数量约有50000件,目前馆内所藏文物已超过150000件。每一件文物都会被录入数据库,以确保馆员们能够保持记录更新,以及帮助学者们获取研究所需的信息。大多数通过发掘、购买和没收而获得的文物都会被运至埃及博物馆,在这里展出或者保存。如今,新出土的文物会就近保存在地方博物馆内,这样的博物馆目前全埃及有27家。
埃及博物馆拥有世界上最精美且丰富的古代埃及文物馆藏。这里有来自古王国时期的藏品,例如哈夫拉(Khafre)、孟卡拉(Menkaure)、拉霍特普(Rahotep)、诺夫瑞特(Nofret)、卡培尔(Ka-aper)等人的雕像,以及塞奈布(Seneb)与家人的雕像。此外,还有在胡夫(Khufu)的母亲海特夫瑞斯(Hetepheres)的墓中出土的文物,包括她的伞盖、床、凳子、轿椅以及棺椁,它们在博物馆一层的一间特别的展厅展出。
这里有来自中王国时期的藏品,例如孟图霍特普(Mentuhotep)的雕像,麦斯提(Mesehti)的模型,麦克特瑞(Meketre)的模型,塞努斯瑞特二世(Senusret II)和阿蒙奈姆赫特三世(Amenemhet III)的雕像,以及克努姆特(Khnumet)公主、斯特哈托尔(Sit-Hathor)、斯特哈托尔伊乌奈特(Sithathoriunet)、麦瑞瑞特(Mereret)、乌瑞特(Weret)、伊塔(Ita)、伊塔乌瑞特(Ita-Weret)、奈菲鲁普塔(Neferuptah)等人的饰品。
新王国时期的藏品有阿赫霍特普(Ahhotep)的饰品,哈特舍普苏特(Hatshepsut)、塞内穆特(Senenmut)、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和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的雕像,尤雅(Yuya)和图雅(Tuyu)的文物,哈普(Hapu)之子建筑师阿蒙霍特普、埃赫那吞(Akhenaten)和奈菲尔提提(Nefertiti)的雕像,以及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纳赫特敏(Nakhtmin)和其妻子的雕像。图坦卡蒙的珍宝在楼上东侧长廊、北侧室和三号厅内展出。关于古埃及晚期,博物馆有幸展出于1939—1940年出土自塔尼斯的珍宝。这批珍宝包括来自不同时期的珠宝首饰共计超过600件,目前安放在环境良好的展柜中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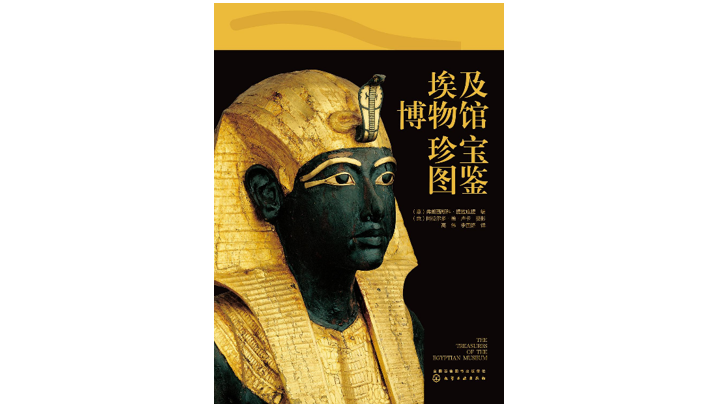
《埃及博物馆珍宝图鉴》,[意]弗朗西斯科·提拉底提 [意]阿拉尔多·德·卢卡 著,高伟 李国娇 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23年7月版。
拿破仑将尼罗河谷与法老文明重新带回到地中海文化圈
拿破仑远征埃及从军事角度来讲已被证明是彻底失败的,但至少还有一项功绩,它将尼罗河谷与法老文明重新带回到了地中海文化圈。外国列强在亚历山大和开罗的代表们在埃及任职期间被埃及艺术品所吸引,这些领事们搜罗了大量的文物然后将之运回欧洲各大城市。由此开启的繁盛的艺术品贸易使得欧洲人对埃及的一切东西都充满兴趣——从19世纪初期的家具风格和装饰艺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影响。
对埃及及其文物再次流行起来产生的兴趣促使许多欧洲贵族亲身来到尼罗河畔参观游览。装备着难以想象的豪华设施的船只在尼罗河上漫游。除了考察和绘制最重要的古迹之外,这时的参观者必会购得一些文物向家中的亲朋好友展示。这些19世纪的纪念品通常尺寸可观。木棺是最受欢迎的物品,木乃伊的订货数量同样庞大,尤其是仍然包裹着绷带的。木乃伊到达欧洲后,便开始组织表演,在拆开木乃伊绷带的时候,一些敏感的淑女会当场晕倒。除了木乃伊和木棺,王像与神像的生意同样兴旺,还有石碑、夏勃提(Shabit)像、纸莎草、家具、容器、护身符和圣甲虫等。带装饰和铭文的残破文物会被整个运走,而完整的物件则有可能面临被狂热的欧洲游客拆解的厄运。
即便是圣书体文字的破译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也无法抵抗塞提一世(Seti I)墓中彩绘壁画的精美,于是决定拆下一根门柱(如今在巴黎的卢浮宫展出)。商博良的托斯卡纳同事伊波利托·罗塞里尼(Ippolito Rosellini)如法炮制,将另一根门柱拆下运回了佛罗伦萨。最初,埃及人对于西方人如此热爱从地里冒出来的石头这件事感到迷惑。随后,石头下面有宝藏的谣言开始传开。
考古遗址附近的村民们开始洗劫墓葬、神庙和雕像以试图找到珠宝首饰和贵重物品,但都无功而返。不久之后,埃及人才意识到那些外国人是对石头本身感兴趣而不是其他可能掩藏的东西。尽管他们自己觉得这些被雕刻过的石头没有任何吸引力,但他们很快便成为了寻找和发现文物的专家。事实证明,缺少真品文物并不是问题,埃及人立刻便制作出了品相足以乱真的赝品,就连当时的埃及学家也难以分辨。
拿破仑远征之后的30年,埃及到处都是因各种原因从事文物贸易出口的人。地方当局的政策措施还促进了埃及文物流向海外。那时的埃及是在穆罕默德·阿里的(Muhammad Ali)统治下,穆罕默德·阿里被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任命为总督(viceroy)。拿破仑远征之后,穆罕默德·阿里实行了广泛地向西方世界开放的政策。外国人,尤其是大国的代表们,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他们可以轻易地获得在埃及发掘的许可。从与欧洲列强亲密的关系可能带来的经济和商业利益来看,发放“发掘许可”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穆罕默德·阿里在外国的援助下成功地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使得埃及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显著的改善,但是事实证明这并没有为贫困人口带来好处。
然而,他的计划同样导致不计其数的古代建筑遭到损毁。许多古迹被拆解,石块被填进石灰窑或被用于建造新的建筑。许多工厂甚至获得官方许可去购买木乃伊,把提取物用于工业制造。焚烧木乃伊可获得一种精细的炭,研磨后可用于糖的提纯和漂白。埃及作为甘蔗主要的生产国广泛地使用这项技术,并且将该原料大量出口到法国北部的制糖厂。这就是1828年商博良所面对的埃及,它的全部精力都关注于未来而对灿烂的历史置之不理。

《埃及博物馆珍宝图鉴》内页。
通过对比《埃及志》的图版,这位年轻的法国学者不禁发觉在这三十几年间不计其数的古迹遭受到了人为的毁坏。完整的神庙建筑群不留痕迹地凭空消失了。曾经屹立在神道两旁和庭院中的巨型雕像和普通尺寸雕像变为商博良眼前的一个个沙土地上的深坑。让商博良尤其感到惊讶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运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国家并没有意愿去管理流出埃及的文物。他特别担心珍贵的文物可能会被锁在欧洲富人的家中永不见天日。然而,他并不反对在官方授权下用于在博物馆或公共场所展出的文物被运出埃及。因此,他对保护埃及古迹有着相当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他批评个人可以轻易地获得“发掘许可”;另一方面,他却毫不犹豫地为卢浮宫搜罗藏品。他还计划将卢克索神庙第一塔门前面的两座方尖碑中的一座运走,这一计划最终于1836年完成。当时法国的领事弗朗索瓦·米莫(François Mimaut)是极为热情的支持者之一。然而,他又率先以官方身份提醒埃及政府应重视自身历史和文化遗产。由于对文物的热爱,米莫曾直接向穆罕默德·阿里提出严重抗议,反对拆除一座吉萨金字塔来作为建造尼罗河大坝的石料。
或许是米莫建议穆罕默德·阿里应当委托商博良撰写一份关于保护埃及古迹的报告,商博良在离开埃及前提交了这份报告。他在报告中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了古迹保护的重要性,并且还指出参观过尼罗河谷的所有欧洲的重要人物都应对文物古迹的损毁和流散深感遗憾。商博良还呼吁应加强对文物发掘和文物出口的管制,但并未提出任何具体的措施。然而,当报告提交给穆罕默德·阿里之后,并未有人愿意跟进商博良的建议。贩卖文物的人从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无论是埃及的文物商贩还是欧洲的富人顾客都不曾真正关心过文物的保护问题。
向公众开放了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埃及博物馆
时光飞逝,埃及人对本国文物古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曾在巴黎学习和生活过的埃及文化学者瑞法·塔赫塔维(Rifa’aal-Tahtawi)成为了保护埃及文化遗产的具体措施的推动者。他的理念促成了19世纪埃及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并唤醒了人们对历史以及与埃及过去的辉煌有关的一切的兴趣。塔赫塔维成功地提升了公众对于文物价值的关注度,并于1835年8月15日颁布了一项法令,首次对埃及文物贸易实行了管制。雕刻过的石块和文物禁止出境,文物在开罗的某地被集中保存和展示,这与当时欧洲的所有大城市相同。收集第一批文物并运至阿兹巴基亚花园展厅的工作交由一位长期居住在开罗的法国工程师和地理学家——利南·德·贝勒丰(Linantde Bellefonds)完成。
尽管出台了暂时性的措施,但1835年的法令被长期忽视。埃及文物的对外贸易和对古迹的毁坏仍在毫无节制地进行。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继任者们继续将新的文物藏品视为私有财产,在有需要时便抽取一件当作礼物赠送给贵宾。数年之后,这种做法导致馆藏不断减少,博物馆迁址。
萨拉丁城堡里教育部的一间大厅就足以放下尚未赠送出去的文物了。1855年,当阿拔斯总督将剩下的藏品作为礼物赠送给前来埃及正式访问的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时,首座埃及博物馆的故事就这样彻底结束了。卢浮宫的助理馆员奥古斯特·马里耶特为丰富巴黎科普特手稿收藏而来到开罗已经5年时间了。当他的任务宣告失败时(科普特长老禁止出售任何保存在教堂里的手稿),他决定去萨卡拉做发掘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在那里发现了塞拉皮斯墓(Serapeum)的入口。马里耶特继续在圣牛阿匹斯(Apis)的墓地工作了3年,直到他不得不返回法国。

《埃及博物馆珍宝图鉴》内页。
然而,沙漠中的经历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在那三年中必须应对的所有困难使他确信,埃及需要有效的机构来促进其古迹的保护。随后,他抓住了拿破仑二世(Napoleon II)计划游览尼罗河的机会,以为访问做准备为借口再次来到埃及。到达后,他开展了一系列发掘工作,并努力提高地方当局对古代文物的保护意识。
1858年,总督下令成立埃及文物管理局(Egyptian Antiquities Service),这是负责监管全国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实体机构。机构负责人的职位自然地落在了马里耶特的身上。上任后,他立刻启动了一连串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来自埃及全境的数量庞大的文物很快地便汇聚到了开罗。在文物管理局成立的初期阶段,马里耶特不得不面临各种难题,被迫与那些想继续从事文物生意的埃及人和欧洲人周旋。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859年,马里耶特的工人们在德拉阿布纳加(Dra Abuel-Naga)发现了阿赫霍特普的随葬品。但基纳(Qena)的市长没收了王后的木棺,他一心想讨好总督,打算把这件宝物送到开罗去。马里耶特派人拦截下运送文物的货船,成功地收回了珍贵的文物,并予以严厉的警告。1867年,阿赫霍特普的珍宝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即便在这种场合下,马里耶特也不得不回绝欧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企图得到这批珠宝的心意。

《埃及博物馆珍宝图鉴》内页。
尽管面临各种问题,埃及的经济仍处于困境,但马里耶特还是成功地于1863年利用过境管理局(Administrationdu Transit)的办公场所向公众开放了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埃及博物馆。这座可以俯瞰尼罗河的建筑位于布拉克区。随后,得益于马里耶特及其助手每年组织的考古发掘,博物馆随着藏品数量的增长而多次扩建。1864-1876年间,藏品手册出版发行,并重印了6次。
但是,布拉克的选址在尼罗河泛滥时暴露了严重的缺陷,1878年的那场洪水导致许多文物丢失。一直将布拉克建筑视为临时场所的马里耶特抓住了这次机会,坚持要政府为博物馆提供永久性场所,既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馆藏需求,又可以不受洪水侵扰。埃及政府之前已经批准了在杰济拉岛(Gezira)南端修建一座大型博物馆建筑的计划。然而,无论是马里耶特所提的要求还是政府发布的法令都没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此布拉克的博物馆又运行了10年。
层出不穷的新文物使得展厅的布置不断地变化
马里耶特去世后,博物馆的工作由与马里耶特共事近20年的路易吉·瓦萨里负责。继任的加斯东·马斯佩罗竭尽所能想把博物馆搬离布拉克区,但没有成功。在随后的欧仁·格雷博(Eugène Grébaut)任期内,布拉克馆藏的状况饱受批评。1889年,这座建筑的容量到达了它的极限:展厅和库房内无一处闲置空间,当时发掘出土的文物不得不在上埃及的货船上搁置了许久。
这种严峻的情况迫使总督伊斯梅尔将自己在吉萨的行宫贡献出来(现为动物园)作为博物馆的新址。在1889年的夏天至年底期间,藏品被从布拉克搬迁到了吉萨。1890年1月,新博物馆准备向公众开放。几年之后,建造新博物馆的计划通过审批。在竞标的73份方案中,法国建筑师马塞尔·杜尔尼翁(Marcel Dourgnon)的方案最终脱颖而出。他的设计在当时相当前卫。首先,它是世界上第一座专门作为博物馆而设计和建造的建筑物。其次,建筑物整体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使用的是当时刚刚发现的一种相对新颖的材料。许多竞标设计方案的灵感都来自古代埃及建筑模型,而杜尔尼翁设计的博物馆则有着古典的样式和外观。只有平面布局的部分巧妙地与古埃及晚期神庙的格局相融合。例如,大长廊与建筑主体相垂直的部分让人联想到埃及神庙的塔门,而宽阔的中央大厅与周围侧室的布局如今依旧可以在艾德福(Edfu)神庙内见到。
杜尔尼翁将博物馆内部设计成一个开放的空间,不同区域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可以让游客漫步其间,感受古代埃及恢宏的气势。然而,杜尔尼翁的中标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对为新馆的资金筹措尽心尽力的意大利社群而言,法国人的胜利代表了意大利人的失败,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也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博物馆的承建方是来自意大利的格罗佐·扎法拉尼(Garozzoe Zaffarani)公司。新馆于1897年1月启动建造,地点位于驻扎在开罗的英军营房旁边的空地上。
奠基仪式于同年4月1日举行,王子阿拔斯·希尔米和马斯佩罗出席仪式。马斯佩罗接替了格雷博的工作,再次担任了文物管理局的负责人。1901年11月,文物管理局聘用了意大利建筑师亚历桑德罗·巴桑提(Alessandro Barsanti),从1902年3月9日开始将吉萨行宫的藏品运至新馆。运输期间约5000个木箱被使用。另有两辆专列火车在两地往返了19次,用以运送大型文物。

《埃及博物馆珍宝图鉴》内页。
第一次运送的48具石棺总重量超过1000吨。搬家工作在匆忙和慌乱中完成了。当所有文物被运抵新馆后,文物局的官员突然发现一尊法老霍尔(Hor)的精美木制雕像不见了。悬案随后被破,这尊珍贵的雕像在地下库房的角落被找到了。在搬运期间,工人们由于担心受罚,一些文物受到损坏后却并没有被及时上报。1902年7月13日,马里耶特的墓迁至新馆标志着新馆的搬迁工作完成。依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将与他用毕生精力所收集的文物藏品永不分离。同年11月15日,开罗博物馆正式开馆。
新馆内的布展设计遵循了19世纪末埃及的文化观念。展厅按照时间顺序安排,文物的展陈首先考虑美学标准。出于结构上的原因,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文物被安放在一层,而二层按照年代顺序展出墓葬中的随葬品。生活中的日常物品按照类别被放置在不同的展厅内。1908年大长廊两端的天窗需要重建,这项工作由一家法国公司用时一年完成。或许是在此时修建了楼梯四周的小阳台,以用于安放在戴尔巴哈里所谓“第二隐蔽墓葬”(Second Cache)内出土的许多底比斯祭司的木棺。随着馆藏的丰富,该建筑不断被改造,位于一层的一些房间变成了商店。为了扩大书店的面积,为其他服务提供空间,原本展示古迹石膏模型的门廊也关闭了。
层出不穷的新文物使得展厅的布置不断地变化。例如,在泰勒阿玛尔纳(Tellel-Amarna)的发掘工作,以及随后这一艺术风格的流行,使得博物馆被开辟出了一个专门用于展览该遗址出土文物的展厅。图坦卡蒙的珍宝也需要一个合适的地方保存和展示。1923年,当图坦卡蒙珍宝入馆时,人们对二层展厅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整。为了给这位小法老所有的随葬品腾出足够的空间,戴尔巴哈里王室隐蔽墓葬内的棺椁不得不被移到了博物馆的其他地方。
虽然博物馆的外观没有重大的改动,但它所处的环境已与之前设想的截然不同。曾经的英国军营如今已变成尼罗河希尔顿酒店。矗立在博物馆后方的是拉美西斯希尔顿酒店,而前面则是开罗的心脏广场——解放广场。在博物馆和解放广场之间是一座被铁艺栅栏围起来的花园。花园的中央有一座喷泉,四周都是古代雕像。马里耶特的墓原本计划安放在博物馆内(一层展出阿玛尔纳时期文物的地方),而现在位于花园的西侧。奥古斯特·马里耶特,这位为建立埃及博物馆奉献一生的人,至今仍长眠于一座古王国风格的石棺内。
本文选自《埃及博物馆珍宝图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意]弗朗西斯科·提拉底提 [意]阿拉尔多·德·卢卡
摘编/何也
编辑/何安安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