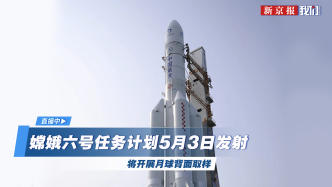《土豆帝国》,[英]丽贝卡·厄尔 著,刘媺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版。
法国人是如何开始接受土豆的?
“好几年来,报纸上几乎只讨论土豆。”1782年,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让—巴蒂斯特·勒格兰德·奥西如是说。医生们分析它们的特性,作家们推崇它们的优点,君主们鼓励食用它们——勒格兰德·奥西宣称,土豆已经成为启蒙运动的宠儿。
有两个特点特别吸引18世纪土豆热衷者的想象力。首先,他们坚持认为土豆是一种健康且营养丰富的食物,每个人都可以愉快地食用。一本法国烹饪书宣称,土豆有三重优势,即“健康、美味、经济”,由此,它无疑是神圣的天意所赐。其次,土豆赞美者(一家报纸这样称呼他们)也提出,这种块根给普通人带来了特殊的好处。“对于拥有一大家子的穷人来说,一头奶牛和一片土豆菜园,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啊!”著名的苏格兰医师威廉·巴肯如此赞颂道。
在整个欧洲,医生、政治家、牧师和文学界的成员都一致认为,土豆对穷人来说是一种额外的资源,可以把他们从饥饿和贫困中解放出来。在土豆显著优点的鼓舞下,欧洲大陆许多地方的君主颁布法令,鼓励种植土豆,无数组织也提出了增加土豆消费的方案。勒格兰德·奥西说18世纪的公共领域被启蒙运动的土豆言论所占领也许有些夸张,但它确实在半个世纪里成了一个跨越欧洲大陆的强大主题。
土豆从受人鄙视的怪植物转变为今天的主食,这个现象被一家受人尊敬的学术团体归功于18世纪的宣传。如我所指出的,这种转变的主力军据称是有远见的统治者和慈善家。一位食物历史学家声称:“莱茵河两岸的人们都倾向于认为吃土豆会导致麻风病。”他解释说,在路易十六亲自资助了一场巧妙的促销计划之后,法国人才开始接受土豆。
这项计划据说是由法国科学家、土豆推广者安托万·奥古斯丁·帕蒙蒂埃设计的,他安排在王室土地上招摇显眼地种植这种块茎作物。帕蒙蒂埃的合作者朱利安—约瑟夫·维雷在他的朋友及同事离世后出版的传记中描述道,当这些植物成熟时:帕蒙蒂埃安排了宪兵进行守卫——但都是在白天。他的目的是让它们在夜里被偷走,老百姓确实也帮了忙。每天早晨他都被告以夜间的盗窃行为,他十分高兴,并慷慨地酬谢告密者,而告密者却对他那让人费解的喜悦感到吃惊。但公众舆论被征服了,从那一刻起,法国因一种持久的资源而富起来。

《土豆的神话》(2021)海报。
据说在欧洲其他地方,要想征服公众的舆论也需要采取几乎相同的计策。在希腊,19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依昂尼斯·卡波迪思特里亚斯,据说是以极其相似的策略,说服了持怀疑态度的希腊人接受土豆。卡波迪思特里亚斯命令把土豆倒在纳普良的码头上并加以看管。谣言开始散布,说既然土豆得到那么好的保护,它们一定很贵重。不久就有人想偷这些“值钱的”土豆。由于守卫们被告知不要理会偷窃行为,因此没过多久整批货就消失了。土豆至今仍然是希腊菜肴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故事在欧洲流行文化中广为流传。我与许多人交谈过,他们讲述了在学校学到的这些土豆英雄和他们克服顽固阻力的事迹。这些营养方面的慈善举措,通常是在饥荒或粮食短缺的特殊时刻典型呈现的应急响应。在普鲁士,据说是18世纪40年代反复发生的饥荒,促使腓特烈大帝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土豆种植的法令。支撑这些故事的假设是,政府推广一种受欢迎的粮食,是特定短缺时期的自然反应。
可以肯定的是,18世纪的粮食短缺,将富人的注意力引向饥饿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和政治后果。在1750年到1815年的半个多世纪里,几乎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给粮食供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过,这样的事件,应该被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招募和装备庞大军队的需要、对粮食贸易自由化影响的调查、有用农业知识的传播导致的当地社会的形成、对农民和劳工酒精消费的束手无策、减少婴儿死亡率的计划,以及土豆推广,共同成为粮食与国家富强之间关系的更大的重组概念的一部分。以这种角度观察18世纪对土豆的着迷,就会发现个人饮食与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和有效治国等新观点之间的联系。
认识到这些联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粮食短缺与政府反应之间的历史关系。饥荒曾长期困扰着欧洲,“饥荒”解释了18世纪对土豆的巨大兴趣,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只有在18世纪,政府才开始通过推广特定的粮食来应对短缺。从饥荒有时夺走多达40%当地人口的17世纪,到18世纪,所发生改变的,并不是饥荒的发生率和严重性的增加——学者告诉我们,饥荒的频率实际上降低了。发生改变的是塑造健康人口的新治国模式的重要性。
启蒙运动对土豆的着迷,反映的不是新食物的出现或新的饥饿程度的呈现,而是人口的健康和活力与国家富强之间关系的新观念。正是这一点,才将土豆的地位从农舍菜园和船舱货物的默默无闻,抬升到启蒙运动的论著之中。因此,土豆的小历史,揭示的是更大的历史变化,这些变化使得政府和它的理论家们关注到了普通人的日常习惯。
启蒙时期人们对土豆的讨论与“人口”分不开
启蒙时期的人们对土豆的讨论,与18世纪关于“人口”的辩论是分不开的。在整个18世纪,哲学家、经济学家、官员和文学界的成员,都致力于长期研究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和其财富之间的关系。他们尤其思考的是,人口多是否是贸易和商业成功的根本动力,人口增长本身是否表明一个国家管理良好,以及人口是否有可能对于一个特定地区而言太过于庞大。这些问题都引起了激烈的争端和讨论。

《土豆侠》(第一季,2014)海报。
自16世纪晚期开始,讨论好政府的论著开始提出,国家通常会从庞大的人口中获益。更多的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工农业劳动力和更多的军队后备。它们反过来又会增加君主的权力。这种对人口规模与国家权力之间联系的兴趣,推动了19世纪数学领域,如测算人口增长所需的概率和统计等学科的发展。在18世纪,治国理论家们开始认为,人口不仅是君主的个人财产,而且是国家财富和权力的基石。这种政治信念,推动了越来越多的计划的制订,它们的目的是通过排干沼泽、管理医院,以及采取其他公共卫生措施来保护人口免于疾病和死亡。这种勇敢尝试的倡导者们,不仅强调推动他们努力的强大人道主义,而且还强调维持人口的政治重要性。
英国1750年出台了《穷人预防注射诊疗所计划》,启动这项计划的依据是:“由于国家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居民数量是成比例的,因此每一次通过保护生命而增加人口的尝试,都会被认为是爱国和人道的。”到18世纪中叶,这些观点在欧洲许多地方已经司空见惯。西班牙政治家确信“人口是万物的基础”,因为没有人民,“就没有农业、工业、商业、艺术、权力和财富”。
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数学家佩尔·沃占廷赞同的是:“一个公民社会的最强实力由大量的好公民构成,这是一种现在几乎无人怀疑的说法。”庞大且(在理想情况下)密集定居的人口具有优势,这种信念贯穿了整个18世纪。当然,人口多也可能是不利因素的理论同样存在,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导致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人口庞大。举例来说,重农主义,是强调土地和农业在创造财富中的中心地位的新经济理论,其倡导者们认为,人口增长是经济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赞同,它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是经济健康的象征。
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里,反对的声音开始抬头。一些作家认为,无限制的增长最终可能适得其反,会削弱而不是增强政体。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成为这种观点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尽管如此,主流观点仍然强调人口众多的优点。1795年,即马尔萨斯出版《人口论》的三年前,由农学家亚瑟·杨主编的一家有影响力的英国杂志《农业年鉴》刊登了一篇记者文章,它确信地论述说,“国家的富裕,无可争议地与它的居民数量成比例”。
晚至19世纪20年代,詹姆斯·穆勒等作家,面对人口众多必然有益的执着观念,还在耐心地试图解释马尔萨斯的观点。正如米歇尔·福柯几十年前所言,这些人口问题的辩论标志着一种权力行使的新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强调了让国家政策与更大的力量保持一致的重要性,而这些力量本身塑造了一个地区居民的活力、规模和生产力。
新的治国科学,不是简单的确保服从或施加权力的问题。它需要对资源进行管理,并为开发资源建立有效的制度。“人口”,换句话说,远不止是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个体的集合体,它是必不可少的资源。论述人口问题的作者们不断强调,对这个至关重要资源的成功管理,是政府效力的基本晴雨表。法国人口学家让—巴蒂斯特·莫霍在一篇论述人口的文章中指出,居民数量的增加,既是整体公众福祉的表现,也是它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由于这个原因,人口的增长或不增长,“证明了政府的好或坏”。
然而,仅人口多是不够的。有一篇关于如何重振西班牙疲软经济的论著,对需要更多地做些什么进行了详细说明。“任何经济体制的最基本要素,”它阐明,“都是确保人们得到有效就业。”这篇论著的爱尔兰作者伯纳多·沃德,曾受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六世委托,对西班牙的农业、商业和工业进行研究,为此他走遍了伊比利亚半岛。沃德后来担任西班牙皇家铸币厂厂长,有许多年一直在思考让西班牙人得到有效就业的最佳途径。他早先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打算将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安置在一个机构里,让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工作。
沃德对流浪者的关注表明,如果不积极从事生产劳动,庞大的人口也是无用的。在为费迪南德六世撰写的报告中,沃德建议对西班牙在欧洲和新世界领土的管理进行改革。他强调,西班牙人口的劳动潜力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资源,而良好的治理恰恰在于释放这种潜力。人口可以通过个体数量的增加而“物理”地增加,但这并不是发展有效人口的唯一或最好的方法。将“一个不工作、对国家没有任何有用贡献的人”转变为一个勤奋的劳动者,才是更大的成就,因为这构成了人口的“政治”增长。
沃德认为,“当人们说,一个君主的财富由他的臣民的数量构成,他们的意思是‘有用’的臣民,因为上百万的流浪者和职业乞丐不仅没有用处,反而是国家的障碍。没有他们,国家会更好更富裕。”沃德对发展勤劳人口的重要性的评判,得到了广泛的赞同。1731年,瑞典作家、政治家爱德华·卡尔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没有在农业或制造业中得到有效的就业,它就“如同埋在地下的死宝藏”。

纪录片《舌尖上的马铃薯》(2015)剧照。
勤劳的居民,而不仅仅是普通大众,才是国家伟大和成功的核心。民众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勤劳工作,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繁荣昌盛。而民众健康所需的不仅是预防接种计划、沼泽排水方案,还必须包括充足的粮食供应。如土豆推广者帕蒙蒂埃所提出的那样,“食物的种类和选择极大地影响着人口,因此要确保人们吃得够,就不可能采取太多的防范措施”。这些观点,并不仅仅是特定短缺时刻的反应,而是基于一种日益增强的信念,即强大的人口可以极大地增加一个国家的权力和财富。当然,战争和短缺的特别压力,会将官员的注意力集中在粮食供应上。1796年,数学家、官僚主义者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设计了“营养微积分”,用于估算新法兰西共和国的食物需求。他的动机既包括对理论的好奇,也包括实际的担忧。
确保有足够的、适合劳动者的粮食种类供应是至关重要的
从1792年到1815年,全球战争共动用超过700万兵力。从法国大革命爆发到滑铁卢战役的余波,这场战争将欧洲的实力消耗殆尽。再加上反复歉收,许多国家的粮食供应出现紧张状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战争年代,对劳动人民饮食的兴趣,也不仅仅是这些连续不断状况的反映。作家们一直强调确保“下层人民”得到充分营养的重要性,因为这样的观念在治国的讨论中已是司空见惯。
从17世纪晚期开始,政治理论家们开始将粮食视为建立强大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学的德国外交官、政治理论家约翰·约阿希姆·贝歇耳将公民社会定义为“人口众多、营养丰富的社区”。英国律师威廉·培提特写过许多论述政府治理的著作,他也提出了同样的粮食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
由于发展规模庞大而活跃的人口对理解政治和经济福祉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确保人口吃好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也更加受到关注。18世纪30年代,法国律师、政治哲学家让—弗朗索瓦·梅隆将粮食供应纳入他的国际贸易分析中。梅隆在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思维实验,以说明塑造商业交换的力量。他对三个假想岛国之间贸易关系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其拥有“尽可能多的粮食”密切相关。在解释国家如何变得强大的更大的理论框架中,粮食是一个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确保有足够的、适合劳动者的粮食种类供应是至关重要的。当作家们谈到要保证人口的精力和勤劳时,他们内心所想的是劳动人民的精力和勤劳。英国慈善家乔纳斯·汉威曾明确表示:“财富和权力的真正基础是穷人劳动者的数量。”因此,国家的力量与财富所需要的,用诸多讨论该问题的小册子之一的话来说,是劳动人民要“吃得饱,吃得便宜”。劳动人民的身体与国家实力和繁荣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促使人们对劳动者的饮食习惯产生了新的兴趣。将劳动者的饮食与国家政体相联系时,这些作者借鉴了在不同的写作体裁——健康手册中日益普遍的观点。
在17世纪,这类致力于介绍良好生活原理的各国的指南,出版的数量日益增多。饮食建议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到,好身体从根本上取决于吃合适的食物。这些书籍除了强调选择符合个人体质和气色的饮食的重要性外,还经常将特定地区的饮食与当地人口的特点联系起来。不同的饮食习惯,有助于说明诸如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民族差异,以及欧洲人对自己和非欧洲人之间差异的理解。一位西班牙医生说,美洲印第安人在身体和性格上与西班牙人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吃的食物不同”。
当地的历史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也试图对一个地区的特色进行解释。威尔特郡居民忧郁的性格,格拉摩根郡人精力充沛、和蔼可亲的性格,都被归因于当地的饮食。
个人饮食习惯塑造了地区和民族性格
个人的饮食习惯就这样塑造了地区和民族性格。这些概念,使得个人饮食习惯和整体人口特征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18世纪的政治思想家正是对它们加以了利用。一个国家福祉的许多方面,据说都会受到劳动人民饮食习惯的影响。观察人士认为,工业生产率是一个明显与之关联的领域。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一般来说,人在吃得差的时候工作强过吃得好的时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营养不良的劳动者不会养育精力充沛的孩子来从事制造业和农业劳动,人们也不能依靠营养不良的士兵来保卫国家。这两者——贫困儿童的健康和军队的强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关的。小说家亨利·菲尔丁想象着喝杜松子酒的母亲生下的病弱婴儿,担心“这些可怜的婴儿”成为“我们未来的水兵、士兵”的后果。他预言,如果英国依靠这些羸弱的人来保卫自己的领土、发展商业和农业,后果将十分可怕。欧洲各地的作家与菲尔丁一样,担心贫穷儿童的死亡或衰弱会造成“国家的政治损失”。在考虑该问题的众多文章中,有一篇认为,确保婴儿成长为健康而有活力的劳动者,对国家的“荣耀与繁荣”至关重要。
论述该主题的书籍在它们的书名中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关联。有一部西班牙的此类著作的标题是:《弃婴夭亡的具体原因:对这种严重不幸的补救方法,以及使他们成为有用的基督徒公民以使西班牙的人口、力量和财富显著增长的方法》。它的作者是潘普洛纳综合医院的一名牧师和托管人。他明确表示,为国家救活这些命运不幸的婴儿,将会增加士兵和劳动人口:“将会有多少——我们现在缺乏的人——从事公共工作!有多少劳动者!多少诚实的士兵啊!”
潘普洛纳的医院,是旨在通过照顾弃婴来增加诚实士兵和劳动者人口的众多机构之一。在这些工作中,食物是核心问题。喂养弃儿的难度很大。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奶妈,孤儿院的死亡率有时接近100%。正因为强壮而多产的劳动人口依靠的是它自身的再生能力,因此婴儿喂养与婴儿死亡率的关联引起了欧洲许多地方作家的关注。关于最佳人工配方奶粉,以及婴儿总体喂养的特别重要性之类的论著,被大量撰写出来,其中一些直接写给统治君王。这种情况说明,它们的作者们认识到了贫困儿童的营养与国家事务之间的关联。

《收获的天空下》(2013)剧照。
对国家安全、营养食品和劳动人口的关注,在海军补给需求中是最紧密交织的。英国政府供养皇家海军的工作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关系。由于人们认为这种“帝国赖以生存的人的身体”需要高营养的饮食,皇家海军的水兵所享受的口粮供应量远远超过商船上的水手。对它的保障并非易事。尽管供养任何一支军队都需要先进的组织,但船上生活造成的特殊障碍,却需要更复杂的基础建设。
在不列颠群岛,供养海军的艰巨任务,是由1683年成立的食品储备局承担的,它负责监督所有与海军供应有关的事务。它的数百万英镑的预算,反映了英国政府对这项事业的重视。它的条例强调了对高质量食品的需求,1760年的条例规定:“牛必须是最肥的,土豆、洋葱和饲料必须是能买到的最好的。”
公务表中规定了水兵有权获得的供应品,同样也是为了确保劳动力的健康和工作能力。储备局一丝不苟的记录显示,条例最轻微的变更都可能招致审计,一方面是因为它可能意味着有欺骗财政部的企图,另一方面也因为不符合标准的口粮会削弱海军的战斗力。其他国家虽然缺乏粮食储备局的强力制度,但也同样相信,水兵的饮食对于国家治理有直接的重要性。西班牙医生、西班牙加的斯皇家外科医学院教授佩德罗·马利亚·冈萨雷斯坚称,让水兵们因饮食不良和医疗不当而患病,对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损失,而对敌人却极为有利。
其他地方的医生也同样强调为水兵提供营养食物的政治重要性。当医师安托万·普瓦索尼耶·德斯佩里埃向法国海军提议一种激进的素食饮食方案时,他将它置于一种明确的政治背景下。普瓦索尼耶·德斯佩里埃是第戎科学院的成员、殖民医学早期文章的作者。他对海军补给中典型的对咸肉的依赖提出了批评,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指责它是坏血病的罪魁祸首,这种病是对水兵个人和海军整体的严重威胁。他提出将以大米和豆类为基础、用姜和腌洋葱调味的口粮作为替代。他承认,这种新饮食可能会让水兵不悦,但他坚持认为,它会让海军更健康、更有活力。由于它旨在保护“国家珍贵人群”的健康,因此他认为他的计划是一项“爱国和经济方案”。简而言之,考虑劳动人口的饮食问题,对关心政治的人而言是正当事业。
以上内容节选自《土豆帝国》,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英]丽贝卡·厄尔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