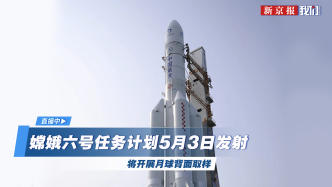在童年,人会更亲近自己的本能,而人的本能则与动物的野性有相通之处。在童诗国度中,有位诗人就尤其看重这份野性。他对动物和幻想着迷,书写鲸鱼、驯鹿,还有月亮上的幻想动物……他就是英国桂冠诗人、儿童文学作家特德·休斯。

特德·休斯(Ted Hughes,1930—1998)。
对于休斯来说,诗歌也具有其动物性,他在《诗的锻造:休斯写作教学手册》中曾这样说道:“我觉得诗在某种程度上仿佛一种动物,也拥有自己的生命。”
在本期“孩子与诗”系列专栏中,作者闫超华分享赏析了特德·休斯的童诗作品。正如文中所说:“休斯的童诗重建人与自然的神秘关系,虽然这其中充满了残忍、野性、讽刺与荒诞,但本质上,休斯是为了表达对自然之中生命的尊重与赞颂。”
诗是动物,拥有自己野性的生命
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在《诗的锻造:休斯写作教学手册》中曾这样说道:“我觉得诗在某种程度上仿佛一种动物,也拥有自己的生命。”(杨铁军 译)。我们看它、听它、抚摸它、感受它,慢慢变成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场景,一个由词语组成的方形、圆形甚至迷宫形的小小生物,它们组成了一个“奇趣动物园”。于是,当我们读休斯童诗的时候,似乎它们都在动,一点一点靠近你。许多动物奔跑在诗行中,留下各种各样的脚印,跑累了,它们就在你心中的洞穴里住了下来。

《写给你的诗,孩子》,[英]特德·休斯 著,[英]雷蒙德·布里格斯 绘,潘岳 译,禹田文化传媒出品,晨光出版社,2019年4月。
下面我们可以从休斯的诗集《写给你的诗,孩子》入手,在这本诗集中,休斯从海洋写到陆地,进而又写到极地和月球中想象的生物。其中,海洋生物及水怪约三十首;北极星下的生物约三十首;月亮中的生物约五十首;陆地及其他生物约一百首。无数事物通过拼接、组装,混合在一起,变成新的物种,语言包裹着它们。整本诗集就像个稀奇古怪马戏团,诗人指挥着那些生物不断登场,一行行句子像是围栏,读者时而大笑,时而悲伤,时而惊恐,时而流泪,直到看完最后的表演——也就是一首诗的最后一行,他们才缓缓离场:
月亮橡树
作者:[英]特德·休斯
翻译:潘岳
月亮橡树
是一种植物鹰鹫。
他的爪子拎着地球
因为那是他的肉。
他将手臂伸进星空
那是他的伟大飞行
很久以前就已开始——
他朝着太阳飞去
因为那是他的老巢。
他将在那里歇脚
并向他的伴侣发出问候,
她的爪子拎着地球。
然后地球和月亮将消散
在他们的火焰雏鸟中间。
何为“月亮橡树”?诗人说那是一种“植物鹰鹫”,很明显,这是植物与动物的融合体,诗人制造了它,并赋予它以生命。这让我想起希尔弗斯坦的诗句“身上长出棵树/总让人觉得恐怖/我现在只有枝和刺,浑身上下光秃秃/可到了春天你再瞧/一定把你吓一跳。”(《头疼》,叶硕 译)
事实上,休斯不光要吓你一跳,它还要让你目睹动物的天性与野性。一个场景浮现了:鹰鹫的爪子拎起地球,向星空飞去。语言开始变形,夸大其词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危险”,因为连诗人自身也成了这种鹰鹫的猎物。对此,诗人在《栖息的猎鹰》中也有所暗示:“我坐在树顶,闭上眼睛/一动不动,没有虚假的梦/在我钩状的头和钩形的爪子之间/或于梦中操演完美的捕杀和进食。”(曾静 译)原始的气息弥漫在休斯的心灵,这源于他对自然世界的迷恋。

《诗的锻造》,[英]特德·休斯 著,杨铁军 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
沿幻象之梯,攀向月亮
一枚纸月亮在休斯的诗集中升起,当它消失时,落在诗里的光像花蕾一样不断生长,而这些都是诗。用休斯在《月球生物》一文中的话来说:“真的月亮在天上滚动,这让我们很安心,但是,同样多的证据表明,存在一个梦的月亮,因为它在我们的头脑内部……”(杨铁军 译)。一旦诗意与梦连接在一起,幻觉就会产生,仿佛诗人吃了一朵“月亮上的蘑菇”:
月亮上的蘑菇
作者:[英]特德·休斯
翻译:潘岳
月亮上的蘑菇很美味。
可那些吃过的人都变成了鸟类、兽类或鱼类。
太空鱼,太空兽,太空鸟。
他们迷失在太空,一群群,一队队,一条条。
一开始,他们兴奋又狂喜,
但突然感觉到上上下下围绕着太空,他们惊恐不已。
然后,目瞪口呆的太空鱼成对逃窜,
太空兽在无尽的迁徙中四处疏散,
太空鸟在无尽的骚动中从太空的一端猛冲到另一端
在星座中间。
可太空太浩瀚,他们迷了路,瞎得可以。
他们寻找着丢在身后的人类躯体
就在那小小小小的月亮上,如此之小,小得像尘埃
一颗
他们永远无望再次飞落。
没错,“月亮上的蘑菇”也许是魔法蘑菇,吃了以后就会变身,比如变成鸟类、鱼类、兽类……但很快,他们迷失在太空中,而且永远无法再次飞落。绝望如梦魇般笼罩,没有人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休斯的诗中有一种巨大的能量,它驱赶着那些生物走入人们的视野,吸引孩子的目光。植物行走,动物生根,星空飞行其中,生命在此闪耀。用休斯的妻子——诗人普拉斯的诗来说,便是“沿幻象之梯攀向月亮”。(《公主与小精灵》冯冬 译)一条光的梯子垂下,诗人爬了上去,他发现上面有:月亮风、月亮百合、月亮蜗牛、月亮时钟、月亮女巫……很显然,诗人加大了诗歌的难度和强度,夸张、离奇、变形、荒诞,甚至充满了残忍的狂欢,休斯营造出一场恶作剧般的世界,因为在休斯这里,童诗将重新被定义和命名:
鲸鱼
作者:[英]特德·休斯
翻译:潘岳
哦听听鲸鱼的
巨人之歌!
比女高音的舌头
更灵活,
像弹拨竖琴的
一只手那样狂烈,
在她歌唱的所有
海洋中穿梭。
鲸鱼的歌声远胜于人类,那是“巨人之歌”,波浪如同竖琴之弦,狂烈激荡,声音似乎可以穿梭到海水的任何地方,“月亮鲸”与之合奏:“它们在月亮上挺近/就在地表之下/拱起月亮的表皮。”(潘岳 译),一种重金属般的音乐贯穿我们的心扉,通过动物的语言,休斯点燃了他的诗歌星辰,他是一个魔法师:
海星
作者:[英]特德·休斯
翻译:潘岳
一只海星凝望
繁星满天
从天空的深处涌出
无边无岸。
她指尖交叠
哭诉道:
“如果我哭得够多,
也许会
冲洗掉
我眼里的盐
那些明亮的星星
就会有一颗是我!”
童诗的鳗鱼,词语的电流,语言的光波。海星与天星如何相互转化——用足够多的泪水洗掉海星眼里的盐。休斯深入海星的梦境中,将它的梦拼接在一起,倾听海星的自言自语。但谁又能说这样的世界是假的呢?
与动物共用一个狂野的心脏
事实上,动物并非没有语言;相反,它们始终而且从总体上就是语言。”(阿甘本《幼年与历史》,尹星译)休斯与动物共用一个狂野的心脏,语言让动物成为它自己,唯一的自己:
牡羊
作者:[英]特德·休斯
翻译:潘岳
牡羊睡不着的晚上
他不数羊。
他眨呀眨呀眨眼睛,
他想啊想啊想事情。
“究竟是怎么搞的
我就成了唯一的我?
“我是唯一,唯一,唯一
因为我起初就是羔羊一只。
“可我从哪儿来呢,在那之前?”
然后他就轻轻打起鼾
还听见,在沉沉梦乡
有千万只、千万只羊
每一只都在咩咩叫:“为什么
我是唯一的我?”
从月亮到海洋,进又爬到陆地,休斯笔下的“语言动物”四处游走,即使在模糊不清的梦乡。我们数羊,睡眠笼罩我们的身体。然而疑问将我们弄醒:“可我从哪儿来呢?在那之前?”不得而知,仿佛我们在一只羊的梦里做着梦,听见它们之间的谈话,那温柔的眼神眨呀眨,像是水晶。这让我想起聂鲁达在《疑问集》第六十三首诗歌中的诗句:
将他们的语言
翻译成鸟语会如何?
我要如何告诉乌龟
我的动作比他还迟缓?
我要如何向跳蚤
索取它显赫的战绩表?
或者告诉康乃馨
我感谢她们的芬芳?
人和动物的语言如同两只翅膀,它们向前飞的样子让人想起生命。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动物也是休斯的引路者。从处女诗集《雨中鹰》开始,动物就成了他诗学中的重要的光束,不停闪烁。

《雨中鹰》,[英]特德·休斯 著,雷武铃 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
这一切和休斯的童年有关,休斯出生于英国一个偏远而荒凉的小镇,那里质朴、原始的原野风景,在他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迹。据说,休斯自小就对动物感兴趣,三岁时从市场买回来很多铅制的动物模型,也经常用橡皮泥捏动物,建造自己的“动物园”。后来在哥哥的带领下,他学会了捕鱼、制作陷阱和使用猎枪狩猎:“他带我去,把我当猎犬差使,我跑来跑去,收他打下的喜鹊、猫头鹰、兔子、鼬鼠、老鼠、杓鹬。”(杨铁军 译)
十五岁时他停止捕捉动物,转而开始阅读和写诗:“多年后的一天深夜,下着大雪……几分钟后写了下面这首诗——我的第一首‘动物诗’:《思想里的狐狸》。”这只狐狸在雪地留下了足迹:“突然,它释放一股强烈的/狐狸热臭,冲入大脑的黑洞/窗外依旧星星全无;钟表/滴答作响,白纸印满痕迹。”(杨铁军 译)。在休斯眼中,诗歌就是在词语的丛林里狩猎,动物的生存法则和生命秘密都是诗意的存在。

《写给你的诗,孩子》内页。
事实上,动物主题也一直延伸到他的那部《很久很久以前》童话寓言故事集中。比如在这部童话中有一只在魔鬼身上采蜜的蜜蜂,休斯也试图在动物的脑袋里采蜜。后来他发现了与动物相处的方式——语言。接着,北极熊、豹子、乌龟、猫咪、驴子、野兔、大象都来了,各种奇特的动物纷纷登场,童话的芬芳花粉一样扩散。

《很久很久以前》,[英] 特德·休斯 著,[英]乔治·亚当森 绘,邓雪球 译,禹田文化传媒出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3月。
诗人这部作品与他的诗歌融为一体,动物的宇宙在我们心中开始运转。这和刘易斯·卡罗尔的《猎鲨记》有许多相似之处:
海狸从丰富的物质中
拿出纸张、文件夹、钢笔和墨水:
用一双充满惊奇的眼睛注视着
那些奇怪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物”
从洞穴中倾巢而出
——《猎鲨记》(李珊珊 译 )
休斯描述动物的角度和语言永远都充满活力,像野生动物一样奔腾不息,带着原始之力。童诗本身就是“跳舞的句子”,那些由动物组成的乐园,解放了我们对童诗的认知——人类与动物的转化:
我什么也没说——没有一句话
关于我们的简。你难道没听说过她?
她是一只鸟,一只鸟,一只鸟。
哦,永远不要让人知道
我妹妹其实是只大号乌鸦。
——《我妹妹简》节选
我姥姥是只章鱼
生活在海底,
每次来赴宴
都要带上一家子。
——《我姥姥》节选
诗人深陷两个世界,人与动物的界限变得模糊,任何动物都可以成为诗人想象中的家族,一切皆是语言的狂欢,这样的闹剧也符合孩子的天性。正如休斯所说:“每一个初生的孩子的天性都是改正成人错误的一个机会。”(潘岳 译)
休斯的童诗重建人与自然的神秘关系,虽然这其中充满了残忍、野性、讽刺与荒诞,但本质上,休斯是为了表达对自然之中生命的尊重与赞颂。野性的呼吸也是语言的呼吸,看吧,那些形形色色的动物从休斯的诗句中走来,又一点点消失在纸张的尽头……
撰文/闫超华
编辑/王铭博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