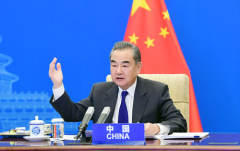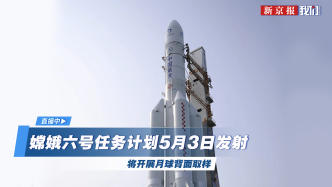当下全球各处似乎都有一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互混杂的趋势,回首世纪初“同住地球村”的未来畅想,恍惚如一场梦幻。一般而言,学界常常将欧洲视为“民族主义”概念及其实践的重要起源地。“民族主义”的学理性阐释及其概念可追溯到18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赫尔德,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概念的创制是非常晚近之事。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与《传统的发明》,以及欧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基本上都将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广泛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民族意识的形成同工业化社会、更迅速的信息传递以及国家主导的“记忆塑造”密切相关。从整体上来说,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及其衍生出的“人民主权论”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成熟的标志。特别是自19世纪以来,对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的反应催了德意志浪漫主义,再加上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社会重构,更强化了欧洲作为“民族主义”诞生地的地位。
许多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都会特别关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的一系列战争、冲突与动荡,使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贯穿了整个19世纪的思想知识界,而随着19世纪中后期德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的统一建立,以及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帝国主义,最终催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个民族主义的幽灵一直徘徊在欧洲上空,并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扩展到了全球其他地方。不过,这种现代主义建构的考察始终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在许多历史语境中难以妥善自洽。比如,在19世纪以来屡遭挫折的中国学者更坚持“民族主义,古已有之”的观念。一代大儒章太炎就说“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倡导“三民主义”的孙中山也认为“盖民族主义,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烁者也”。即使我们仅仅将目光重新投向欧亚大陆西端,我们也能看到在十几个世纪之前的人们似乎就已经拥有了强烈而完整的民族意识,有着不亚于现代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瑞士]卡斯帕·赫希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10月。
中世纪的普世主义势力:帝国与教会
在《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从古罗马到现代早期德意志的另一种历史》的作者卡斯帕·赫希看来,民族多极化的话语体系是欧洲在政治和文化上发展的独特内在动力。这种多极化的出现是普世主义的帝国与教会走向失败的产物。赫希认为,罗马帝国为欧洲文明提供了关于自我认知和民族认同的基本话语。即使罗马帝国衰亡后分裂为数个政体,政治版图在广阔地理范围中呈现出权力多极化的景象,但这个区域中的精英在思想上仍然高度同质化且维系着密切的交流。各方势力在政权林立中角逐霸主地位,同时也会为了对抗最强霸权而形成暂时的同盟。对政治权威的争夺,会演变扩展为文化上和道德上的竞争,塑造出了一种帝国主义的原始冲动。特别是在罗马帝国无远弗届的大一统观念下,原先因民族大迁徙而变得支离破碎的领土遗产,在查理曼手中开始重新被整合,后来又演化为具有竞争性的多极领土。对于古代晚期到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而言,罗马天主教会不仅象征着大一统的普世主义,同时也是支离破碎的领土结构的具体表现。

神圣罗马帝国的创始人“红胡子”巴巴罗萨。
我一直认可一种观念,亦即中世纪欧洲时期逐渐塑造出来的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用中国史家雷海宗的精辟评价,可称为“外表希罗而内质全新”。罗马帝国的遗产从西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就一直以各种形式不断地在欧洲再现,前有查理曼的加冕,后有加洛林的分国,到奥托大帝再度确立帝国法统。腓特烈·巴巴罗萨将自己的政权冠名为“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时,就是试图将遥远的罗马帝国权威和神圣的罗马天主教会权威全都收入囊中。
正如卡斯帕·赫希所说,在中世纪时期两股最为强劲的普世势力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在这部作品中,赫希反复回到的主题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普世性帝国主义政治文化是与支离破碎的领土结构并存的,而这种特征也同样存在于罗马天主教会当中。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不仅享有教宗国的主权和领土,更有对遍布整个拉丁欧洲的主教区、修道院以及无穷无尽的天主教友在各个层面的管辖权。种族各异的基督徒构成了一个极为多样化又在教义层面上平等的集体,造就了西欧的“天主教多民族世界”。由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思想所统摄,同时又无休无止地处于领土上四分五裂状态的巨大文化实体,具象化于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信仰。作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第一位诗人”的但丁,就对大一统情有独钟。在《论世界帝国》中,但丁指出要在尘世建立全人类的和平与统一,甚至类似于“将天国建立在此世”,除了建立罗马帝国这样“一统天下”的局面别无他途。

但丁《神曲·炼狱篇》插图。作者:古斯塔夫·多雷。
然而,在中世纪晚期,这两股势力的衰落为民族国家发展提供了历史空间,也就使欧洲的诸多王国向着法律上的独立和平等地位迈进。从历史角度来看,多民族的大帝国其实都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以他们为核心而运作的帝国,迫使周边过于弱小而无法拥有自己独立国家的民族共同体依附于这个帝国。从这个角度来说,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大一统”主义衰微的结果。换而言之,民族主义的起源可以归结于源自罗马帝国遗产、挥之不去且强而有力的“大一统”思想。就在这种循环往复之中,民族主义开始蜕变成型。
民族的“虚荣”
《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一书中,5到7章的内容最为丰富,这也与赫希此前的著作《民族的竞争:中世纪与现代之交德意志荣誉共同体的构建》(Wettkampf der Nationen: Konstruktionen einer deutschen Ehrgemeinschaft an der Wende vom Mittelalter zur Neuzeit, Wallstein Verlag, 2005)紧密契合。在这一部分,赫希非常精彩地论证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亦即人文主义者在创制关于民族话语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有学者在评论本书的时候,认为赫希将立论点着落在与现代主义者的方法论辩驳上,从而使本书遗憾地未能充分发挥其渊博学识和敏锐性所应该带来的冲击力。平心而论,在这样一部“观点先行、先破后立”的作品中,几乎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在一些片段性的思考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赫希的视野所在。在他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可以被看作这场复古主义运动的顶峰以及最深刻的转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将带有多极化平等竞争思想的自治民族概念引入之后,宗教改革迅速重建了两极化和不平等的体制,将信众与异教徒和无信仰者、被救赎的人与受诅咒者分开。
民族的形成需要外界的刺激,以便将自己界定为一个语言和政治上的整体,德意志人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由意大利人对他们的不屑、调侃而逐渐“发明”出来的。为了应对意大利人的嘲讽,德国人则构想出亚当是德意志人,而罗马城的创立者罗慕鲁斯是娼妇之子的。在一些极端新教人士的想象中,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罗马人所创造的堕落的秩序将被完全地消灭,天主教会则是首当其冲要被彻底摧毁的。世界将会回归其原初状态,也就是一个讲德语且日耳曼人说了算的世界。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徒对罗马天主教的一切感到厌弃。有趣的是,他们厌弃带有浓厚拉丁文化色彩的天主教,厌恶犹太人,却没有放弃基督信仰,反而自视为信仰的代言人。在他们的认知或者说是“想象”中, 德语“比希伯来语的文辞更加丰富、比希腊语的结构更加灵活、比拉丁语的意义更加重大、比西班牙语的发音更加绚丽、比法语的风范更加优雅。”基于马丁·路德学说的新教主义摒弃了大公教会所代表的普世传统,更将罗马帝国的尊威弃置一旁,他们独立地在基督教传统中创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德意志根脉”。

马丁·路德在沃姆斯会议上受审。
法国人也将拉丁语视为一种外来语言要将之驱逐,甚至认为更为古老的“希腊字母表是高卢人的发明”。在英格兰的情况也是如此,但他们更为明确地将自己的国王当作最高宗教领袖,将自己偏处一隅的民族视为“上帝的选民”。通过英文译本的《圣经》的剪裁,在强烈排斥天主教徒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同质的宗教兼民族身份,进而成为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角度,阿德里安·黑斯廷斯 (Adrian Hastings)在《民族性建构:种族、宗教和民族主义》中将宗教视为国家和民族主义创建的核心,而英国亦成为这一进路的典范。他认为早在七国时代,阿尔弗雷德大帝就将圣经部分翻译为古英语,并借以激励英格兰人击退北方的入侵者。英格兰民族主义强力兴起的诱因则源于14世纪80年代威克里夫圈子中将整部《圣经》译为英文。当然,这一解读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特别是某些具体词汇的延续,实质上并不意味着其含义的延续,文献中的延续性终归不能取代现实历史中的断裂性。事实上,英国和法国是欧洲近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两个民族国家,它们的民族国家构建历程也对后来的民族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英法民族国家有着共同的大背景,那就是与具有普世主义特征的罗马天主教教权和神圣罗马帝国帝权相抗衡,以“民族”的外衣掩护君主的集中王权。
对于欧洲来说,民族主义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似乎确实比其他区域更为明显。这就尤其体现在语言方面。中世纪时期,无论是在罗马教廷还是大学课堂中,拉丁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核心地位,也是各国外交往来和知识分子之间通信的主要渠道。许多学者都认为,拉丁语权威地位的衰落标志着近代欧洲民族意识的觉醒。如同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描绘的,印刷品的广泛出现与宗教改革运动相结合,在欧洲迅速催生出一个人数众多的非拉丁语阅读团体。这些人在阅读和思考中由于使用本地语言,进一步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共同体想象。这个观点当然非常具有洞见,但从方言作品的传播来看,此类文本的首次爆发期至少可以追溯到12世纪。那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传奇骑士文学,包括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亚瑟王传奇系列”以及强调德意志与罗马帝国血脉关系的《皇帝编年史》等。除了在欧洲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德法英之外,北方的挪威、瑞典、丹麦等王国也在12、13世纪开始以流行传奇文学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民族认同与家国情怀。
在绝对主义国家中,官方的行政语言是推动近代欧洲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独立因素”。比如,瑞士就是一个多语言和多民族的国家,但是在其1848年成为一个拥有联邦宪法的民族国家时,各个区域之间的划分并没有使用语言或者民族作为政治标准。然而,在几乎同一时期建立国家的比利时,则一直到19世纪末才承认弗莱芒语(荷兰语)在本国的官方语言地位。在语言上的争夺一直持续到20世纪,比利时的行政划分乃至大学都是按照语言来定义其自治地位,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数荷兰语鲁汶大学和法语鲁汶大学的分立。
民族主义的未来
如果我们采取科泽勒克之概念史的标准,早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生成之前,民族意识的相关思想已经具备了长期演进的“时间化”、被广泛民众接受的“民主化”、融入社会活动的“政治化”以及被凝练为信条的“意识形态化”。当然,这种表现与18世纪,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民族主义有极大的差异,更属于民族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的范畴,正是这项研究更关注古代的象征、神话以及价值传统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的持续影响。

亚瑟王与石中剑的传说。
这些古老文献中对自身“民族”或所从属集体的“荣誉感”“自豪感”的表述,以及与其他任何团体的竞争意识,是否都能被恰切地称为“民族主义”?从19世纪以来的回溯性研究中,当代人带着放大镜在古代文献中找寻、阐释和解读先人的民族意识难免有“时代错乱”之误。如果说康斯坦茨会议是各个国家政权在罗马天主教的“普世主义”牌坊下的一次宣布自身政治权力的舞台,那许多学者的演说也许只能被认作一种情感,而非能称为现代政治学说意义上“起源”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也许在赫希所讨论的漫长时间和广阔地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和民族主义有紧密联系的要素,比如国家的肇建、中央集权、部族的传统或家族王朝的竞争乃至种族化的自我中心主义,但这些要素混杂在了一起,是否就可以说民族主义就业已出现了呢?然而,赫希本人也曾经回应过,对于那些“文艺复兴”或者“中世纪”人文主义等词汇,不也从未在当时人的笔下出现过吗?中世纪的人从来不知道他们身处于“中世纪”时期,而在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词汇对于学者们来说却并非“时代错乱”,因为其已经在学术传承中奠定了超过两个世纪的传统。由此观之,为什么就不能将“民族主义”的概念应用于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历史解释呢?
更进一步而言,“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事实上未必就是历史的最终归宿。根据研究,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的181个国家当中,只有十几个可以被称为在种族上同质的民族国家,但在半个多世纪的迅猛全球化之后,这个数字可能还在不断减少。一些在中东、非洲乃至中亚地区的国家,其内部存在着多重的人为边界和复杂的民族构成,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民族认同基础事实上非常薄弱。这种“脆弱国家的政治边界和民族边界之间的不匹配”是当代不稳定的根源。历史社会学家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就认为,在当下全球化的环境中,对民族国家的定义不再需要包括原先那些必不可少的要素,特别是“共同的血缘、血统观念”以及“共通而独特的文化”,而是要强调在同一个国家内,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进行统一统治,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且国家是以民族共同体名义进行治理的。
霍布斯鲍姆曾经预言,随着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勃兴,人类社会真正走向“平等的全球化”之后,民族主义或许会走向式微。但以21世纪头二十年的经验来看,民族主义仍然保持着极度旺盛的生命力,且总是以排外主义——被许多学者视为“当今世界散布最广的群众意识形态”——的面貌出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斯鲍姆清晰地认识到,民族主义从根本上效忠的对象是“经过改写版本的”国家,也就是由意识形态所建构出来的国家。卡斯帕·赫希的这部《欧洲民族主义起源》从德意志民族及其国家构建着手,向我们揭示了另外一个可能的维度,民族主义的出现恰恰是普世主义衰微的产物。各方势力的争夺,从许多方面来看,似乎仍然没有跳出十几个世纪之前的心态。
撰文/李腾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