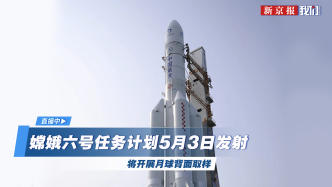近日,番茄文化客厅“《繁花》——小说与叙事艺术的胜利”主题座谈会在上海举办。电视剧《繁花》联合导演程亮、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作家、艺术评论人btr,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张屏瑾四位嘉宾,共同就《繁花》的热播,探讨了作品在文学与影视两种不同路径下的魅力。

1月28日,“《繁花》——小说与叙事艺术的胜利”主题座谈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在电视剧《繁花》热播以前,小说《繁花》在文学界早已掀起过很大的讨论。此次借助剧集《繁花》的播出,金宇澄的作品再度进入到大家的视线范围之内。《繁花》首次发表于2012年,并于2013年推出单行本。书中的故事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少年旧梦,辐射广泛,处处人间烟火的斑斓记忆;九十年代的声色犬马,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水席。叙事在两个时空里频繁交替,传奇迭生,延伸了关于上海的“不一致”和错综复杂的局面,小心翼翼的嘲讽,咄咄逼人的漫画,暗藏上海的时尚与流行。
一部电视剧对书的带动是无法估量的
作为《繁花》的出版方,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表示:“一部电视剧对一部书的带动,是无法估量的。在《繁花》剧集上线后短短不到20天的时间,就带动了将近30多万册销售。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地往前奔涌。”同时,《繁花》这部作品在数字阅读领域的增长也非常明显。

《繁花》,金宇澄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
在李伟长看来,小说《繁花》的写作到出版像奇迹一样,“金宇澄在论坛上开始写的时候,他的ID名就叫‘独上阁楼’。因为带着上海话的方式去写,刚写了一两段,就有人开始回复。”一开始,作为一名作家的金宇澄并不算很有名,但读者的反馈对他来说极为重要,“他认为这是他当初能够写下去最重要的一点。”
李伟长说,“有的段落读者反映没那么好,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做调整……直到最终出版,总共写了30多万字——这是非常网络小说的写作方法。”李伟长介绍,金宇澄在网上写了大约10万字以后,突然意识到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他后来花了很多时间把发布在论坛网的部分重新结构化、人物化,把事件、时间做了调整,“我们会看到,在他的故事里,两条时间线一直在穿插,呈现一章叠一章的结构。”
“当时我们其实都意识到,有一本非常独特的小说诞生了,但是它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还不是很知道。”李伟长说,“这个故事讲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漫长时间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识别者,包括像编辑,老的评论家、小说家,还有无以计数的读者给到《繁花》的激励,给到《繁花》的肯定,让他这个东西变得无比的强大……如果说小说是屠龙刀的话,那么剧集可能是倚天剑,倚天剑和屠龙刀合二为一,才会有现在《繁花》的江湖。”

《繁花》(2023)剧照。
时间是作品中呈现得最为复杂的部分,也是座谈中嘉宾们反复提及的词汇。显然,无论原作还是剧集,《繁花》都成功地复现出属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记忆中的那段时光。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东西是很稳定的,时代的烙印、世界的形象都是稳定的。90年代正好是一个各种元素杂陈的时间段,非常复杂。90年代的画面,在时光沉淀下来以后,会呈现出更奇妙的冲突感。”据程亮回忆,王家卫导演在拍摄的过程中花了大量心思去还原当年的场景。“比如‘外滩27号’的办公室。我觉得自己没有见过这么精细的景,这个景里面所有的图章,所有东西的复刻,几乎完全是当时外滩金融机构里能够有的一切。”
程亮表示,王家卫导演的工作非常细致,不仅请来当年“外滩27号”的五朵金花中的几位——“现在都已经是中年人了”,还在现场请了许多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职工作为顾问。为了一个痰盂的木柄,可以停下拍摄,让木工师傅现场复刻,“确实有那个长长柄的气息是不同于别的影视剧的,它这个精致程度,这种呼吸、这种质感是不一样的。”
在海派文学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作为一个上海人,这个片子触动了很多我们对1990年代的记忆。(上世纪)90年代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候,很多东西如果不说、不写、不被影视记录下来,可能我们早就忘记了。”btr表示,书与剧集,通过不同的方式将人带回到了过去。“整个生活场景,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
在btr看来,《繁花》里面最出彩的是对沪语这种方言的灵活应用,“这种灵活应用不是说把上海话作为某种声音,用一些拟声词写到这个沪语里面去。而是它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非常微妙,他把它巧妙地像在更新一种语言那样去使用上海话,我觉得上海话成为这本书里面一种风格的锚点。对于王家卫来说也是同样的,看《繁花》这部剧,能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他的这种影像风格之间的强烈程度,跟以前他的电影是一以贯之的。”

《繁花》(2023)剧照。
张屏瑾则从那一时间段社会变化的角度分析了作品。她认为,从阿宝到宝总的变化,将那几年上海的都市文明与我们整个社会转轨的节奏体现了出来——恰恰在那几年,社会呈现井喷式的发展,各种东西都在进入、各种记忆都在复活、各种梦都开始放飞……《繁花》提供了那个时代新出现的一些征候,这部作品里既有从至真园的三楼看下去的人,又有从三楼往上眺的,还有从底层往上仰视的,各种各样阶层人物形象都已出现,供我们去回忆、去想象、去感受那样一个时代。
《繁花》自小说问世以来,就有非常多的学者和评论家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解读它。那么,它在上海海派文学中又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呢?
张屏瑾认为,近代海派文学中最有名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海上花列传》,原版中韩邦庆完全是用苏州话来写作的。而经过张爱玲注释的《海上花开》《海上花落》,把这部书的阅读——包括在语言上的传播和更广义的中文阅读世界人群的接受,都做了非常大的推进。对比《繁花》跟《海上花列传》,金宇澄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把海派文化的核心的质地,在当代再次重现出来。从这个意义而言,张屏瑾表示,小说版和剧集版的《繁花》就像是两个平行宇宙,既开创出了自身独特的美学,同时又跟整个海派文化这样一种文学艺术的源流上都有接壤,而且有更独特的推进,“把我们上海城市文化这样的一种氛围再一次地推动了起来。”
记者/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柳宝庆